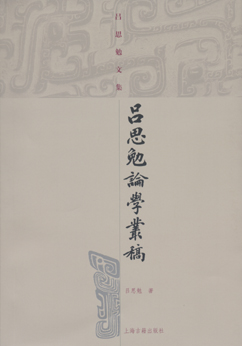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农历八月十六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起就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三年以后,因家道中落而无力延师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导教学。此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毕生关注国计民生,学习新文化,吸取新思想,与时俱进,至老弥笃。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农历八月十六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起就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三年以后,因家道中落而无力延师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导教学。此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毕生关注国计民生,学习新文化,吸取新思想,与时俱进,至老弥笃。吕先生长期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五年起开始任教,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一九七年)、常州府中学堂(一九七年至一九九年)、南通国文专修科(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学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其后,又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沪江大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其中,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最久,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该校任教授兼历史系系主任,并一度担任该校代校长。一九五一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先生是教学与研究相互推动的模范,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写下大量的论著,计有通史两部:《白话本国史》(一九二三年)、《吕着中国通史》(上册一九四年、下册一九四四年);断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汉史》(一九四七年)、《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吕着中国近代史》(一九九七年);专著若干种: 《经子解题》(一九二六年)、《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年)、《宋代文学》(一九三一年)、《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年)、《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中国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学四种》(一九八五年)、《吕着史学与史籍》(二二年);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的汇编三部:《吕思勉读史札记》(包括《燕石札记》、《燕石续札》,一九八二年)、《论学集林》(一九八七年)、《吕思勉遗文集》(一九九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十多种,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他的这些著作,声名广播,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在港台、国外仍有多种翻印熬和重印本。吕先生晚年体衰多病,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録,可惜未能完稿,是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吕思勉论学丛稿》收辑各类文章共一二篇,大体分为“史学”、“哲学”、“社会经济文化”、“文学文献文字”和“书信序跋自述”等五组,内部又按写作和发表年代的先后加以编排。 “史学”和“哲学”二组收录的是吕先生在一九一至一九五年间的部分学术文章,其中《古史纪年考》、《蒙古种族考》、《秦汉移民论》、《汉人訾产杂论》、《道家起原杂考》等,都是吕先生早年的重要论文,曾刊于《大中华》、《齐鲁学报》等学刊及《古史辨》第七册中。《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的《东方杂志》,反驳当时梁启超主张阴阳五行起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而由邹衍首先传播的说法,认为梁氏此说“颇伤武断”,而“其误在于信经而疑传”。《中国文化东南早于西北说》、《古代人性论十家五派》、《西汉哲学思想》、《魏晋玄谈》等篇,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吕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的教学讲稿。《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和《古代印度与佛教》最初都发表在二十年代初期的《渖阳高师周刊》上,也是因教学的需要而撰写。《古代印度与佛教》是先生少数几篇专门论述外国史的文章,文中对人种分布、民族迁移、东西方交通往还、印度宗教的兴衰和传播等叙述,颇为简明而扼要,对了解古代中印之间和东西方关系,很有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