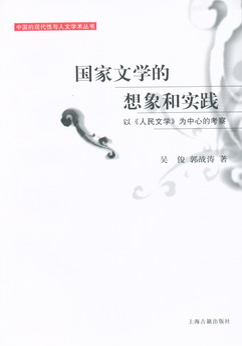 “国家文学”释义 “国家文学”释义从政治角度考察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的时限,传统上界定为1949-1976年,或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至七八十年代之交。但在具体的行文中,一般又可适度上溯和下延。特别是“当代”的时间下限,迄今也是模糊的。本书无意讨论文学史的分期概念,基本上是在狭义的时限内使用“当代”概念。我把它“命名”为国家文学。何谓国家文学?我的基本定义是,由国家权利全面支配的文学谓之国家文学。换言之,当文学(在国家范畴内)受到国家权利的全面支配时,这种文学就是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是国家权利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方式),或者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直接产物,它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同时,国家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家权利的代表或代言者之一,它为国家权利服务。国家权利是国家文学最高也是最终的利益目标,这也就决定了国家文学基本的(或根本的)价值观。 国家是个政治概念。它首先是一种统治机构,是一种权力系统或工具。最高的统治机构或权力系统,也就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行使其维护自身利益的职能。这种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按照经典著作的解释,国家所包含的统治权力及其利益内涵,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显然,国家意识形态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它是国家权力必须建立并维护的一种最根本的观念和价值系统。而所谓价值多元化及其程度,往往或完全取决于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实际权利地位,或其能够承受、容忍的底线。 将当代中国文学视为国家文学,理由之一不仅是指当代中国文学系由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所全面建构,是自觉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也是指当代中国文学系由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所全面支配,是被完全改造、整合、纳入到国家权利范畴之中的意识形态。除了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其他可能的文学“支配”因素,或者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表现为逐渐丧失其支配性影响(地位)的过程。由此,当代中国文学成为由国家权利全面支配的一种文学(形态),即国家文学。理由之二是指当代中国文学不仅被完全赋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或代言的职能与使命,而且它还充分自觉地履行了这种表现或代言的职能与使命,即它是充分自觉地服务于国家权利目标的。由此,当代中国文学在其基本表达方式或形态方面,特别是在其价值诉求和价值归属上,也不能不属于国家文学的性质或范畴。 当代中国文学之为国家文学,还依赖于一种特定的理由,即其具备着一种特定的解释。那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象征、标志或事实。而这一切的实现,并且能够对此提供保障的惟一可能性,就是必须依靠并服从新的国家权力。新的国家权力是作为民族复兴的惟一政治前提而出现的,因此它也理所当然地承担了重建并复兴民族文化的政治和历史责任。建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复兴民族文化,在(国家)政治层面上,两者合而为一。或者,只有将民族文化的复兴寄托在新的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前者的实现才有可能。在此意义上,民族文化的想象、设计与实践,也就必须依附于国家政治(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想象、设计与实践。换言之,在文学领域,建立和建设国家文学(包括其主流或权威地位与形象),也就是重建或复兴民族文学,至少也是其前提与保证。在更广大的范畴上,国家文化也就是民族文化。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特定政治性,也就是其特定的价值依据和规范性。在这种政治文化的逻辑中,当代中国文学之为国家文学,显然也就获得了多重合理性的解释。概言之,文学和文化的合理性,乃至其合法性,必须首先厘清并确认其政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国家文学”形成的一般或宏观过程 国家文学的形成依赖于国家权力(政权)及其相应的制度、意识形态等等的规范(建立与完备)和操作。在当代中国,国家文学伴生于新的国家权利的出现,因此,两者在宏观上几乎呈现为同步发展状态。 首先,国家文学的形成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其制度化的过程。如果说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统治地位为国家文学提供的是基本的思想观念资源及其(政治)规范,那么,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设计和安排,则为国家文学(包括所有的文学形态)提供的是法理依据和规定。所以,在当代中国,政权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组织制度建设等,既成为国家文学形成的政治基础,也与之充分互动,互为验证。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利与国家文学的范畴及价值内涵与时俱变,指向的则是同一的目标。参见本书《〈人民文学〉:与新中国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政治变局的文学见证》等文。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