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汉语中父亲称谓系列的多角度考察*
郭熙 提要:汉语社会中对父亲的称谓复杂多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使用的形式有所不同。主要有“父、爷、爸、大、伯”等类别。“父”是汉语中对父亲的最早的也是一直得以延续的称谓。“父”以外的称谓则经历了“(爸)—爷—爹—爸”的过程,“爸”以弱势地位伴随其中,最终在竞争中获胜。从对父亲称谓的沿革和相关形式在方言中的分布的梳理中我们得到了不少启示。 关键词:父亲 称谓系列 考察
A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s of Chinese addressing forms for “father”
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address father in Chinese. It differs with the times, places and users. Those forms of address mainly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eries : “fù”, “yé”, “bà”, “dà” and “bó”. “fù” is the earliest form and is preserved till today. The other forms experience the changes from “bà” to “yé” to “diē” and finally to “bà”. During this process, “bà” had once been in unfavourable position, but stood out of the competition in the end. We can be highly inspired when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dressing forms for “fath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ome relevant forms in Chinese dialects. Key words: father; series of addressing forms; observations 一、问题的提出 二、 汉语社会中对父亲的称谓复杂多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使用的形式有所不同,但目前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爸爸”化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就在上个世纪30年代,“爸爸”还不为社会所认可,以致于国语的积极推行者们想方设法来证明它的“古雅”。1933年,黎锦熙在北京《国语周刊》第98期发表《“爸爸”考》一文,他在引言中说: 近来小学国语课本大都依北京语改“父亲”为“爸爸”;有些人不赞成,以为非对称时,北京语也常说“父亲”。这是语言习惯和修辞上的问题。其实“爸爸”比“父亲”古雅得多,特从《中国大辞典长编》稿中,抽出此词,比次成文,发而表之,以资参考。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一贯尚古的中国社会,古雅的“爸爸”为什么到了国语运动以后还需要正名?它今天为什么又成了中国社会中争相采用的称谓?探讨它如何从千百年的传统中一跃而成为“黑马”,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采用语言传播的分析模式,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三、汉语社会对父亲的称谓的沿革 对父亲的称谓是最基本的称谓形式之一。古往今来,对汉语中称谓问题进行研究的论著很多,其中不乏对父亲称谓的研究,但近年来胡士云(1994,2002,2003)等的相关研究颇值得注意。这些学者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的搜索,同时注意搜集、整理和利用近年来方言研究的大量成果,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尤其是语言接触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从共时、历时等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少令人信服的结论。 胡士云(2002)从汉语方言的角度把父亲的称谓分为6类(每类他称之为某系)。本文从讨论方便出发,对胡文各类顺序和内容进行少量的调整,结果如下:(1)“父”类,包括父、父亲;(2)“爸”类,包括爸、爸爸、阿爸、老爸等;(3)“爷”类,包括爷、爷爷、阿爷、老爷子等;(4)“爹”类,包括爹、阿爹、老爹;(5)“大”类,包括达、大大、达达等;(6)“伯”类,包括伯、伯伯、老伯、阿伯等。除了以上六类外,还有以“叔”称父亲的,如河南一些地方;有以“相”称父的,如安徽歙县;有以“官”称父的,如福建福清;更有以“哥哥”称父亲的,如浙江武义。还有很多,不一而足。因为这些对父的称谓数量相对较少,本文暂不讨论。此外,还有人把 “令尊”“家严”等也看作对父亲的称谓①,我们觉得这种称谓实际上是一种代称,与我们的讨论无关。 另一方面,胡士云(2002)虽然对汉语方言中对父亲的称谓进行了分类,但他意在梳理爸类,并未对其它各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他的另一篇论文(胡士云,1994)曾涉及“爷”类和“爹”类,但他基本是围绕着“爷”和“爹”称父称祖问题进行的。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依据已有的语料,对汉语父亲称谓问题进一步进行探讨。 (一)“父”类 “父”类是中国社会中历史最悠久、最稳定、也最有地位的称谓。汉语文献中看到对“父亲”的最早称谓是“父”。胡士云(2003)引用王绍新的看法, 说“父”在甲骨文时代已经指称父亲了②。王的说法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后来的字书、辞书一直没有改变。直到今天,“父”类仍然是称呼父亲的重要方式。只是它一般是用来作背称。 按“古无轻唇,‘鱼’‘模’转‘麻’,故‘父’为‘爸’”的说法, “爸”实即“父”之本音。(黎锦熙,1933)这个说法在今天的方言和外语的对音中还可以找到旁证:福建一些方言保留“父”的词中,“父”的声母都念[p](冯爱珍,1993);雷州话中虽然是以“阿”“尼阿”称父,但在含“父”的词中,“父”也读[pe]。此外,轻唇音非组声母的文读为[h],白读则是[p]组,如飞、分、放、孵、父、吠、饭等和蜂、芳、缝等(李新魁,1994))。朝鲜语和汉语的对音关系是非常严整的,“父”所在的唇齿音今天仍读b,例如《韩国汉字读音表》对下列汉字的注音就是bu:夫扶父富部付符府腐妇否浮讣釜附负副簿肤赴赋。③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中古以后,就开始有两个称父的词,一个是与口语相异的“父”(广韵:扶雨切),一个是记录口语的“爸”(集韵:必驾切)。但现有的文献似乎又表明后者始终并没有取得正统的地位。 (二)“爸”类 “爸”最早见于三国魏张揖所著《广雅》一书。按照《广雅》的解释:爸,父也。其后《玉篇》、《广韵》、《集韵》,直到《康熙字典》等均收录该字,释义一般也相同。奇怪的是,自《广雅》始,逢字书必有“爸”字,而在我们查阅的文献中,却很难找到直接用“爸”的语料;在一些涉及“爸”的使用情况的文献中,“爸”的地位似乎也不高。我们来看看关于“爸”的一些记载: 《集韵》去声四十禡:“必驾切。吴人呼父曰爸。” 《龙龛手鉴·卷四》:爸 蒲可反,楚人呼父也。 《巵林·卷七》(明 周婴):单家呼父谓之爸。广雅曰:步可反,父也。 《广东通志,卷五十一》:广州谓父曰爸,亦曰爹。 要么是方言,要么是某个什么人家。均不是常规称谓。可见“爸”不在“正式语言”之中。 只是到了清代情况才有所改观。胡士云(2003)指出清代许多白话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文学作品开始使用“爸爸”这一称谓,其后的文学作品用例更多。这和我们的考察是一致的,但我们发现他提到的一系列作品中的“爸爸”的出现数量仍然不及他类称谓。“爸”的真正崛起,是在“国语”运动以后。这是后话。 (三)“爷”类 “爷”类用来称父亲的时间不详。按照胡士云(1994)的研究,称父的 “爷” 唐宋以前就存在了,而“爷”这个词三国以后才被记录下来。和“爸”不同,对于“爷”我们既可以求诸辞书,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实际用例。例如《玉篇》有“爺,俗为父爺字”之说,而南朝《木兰诗》中“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更是广为人知的名句。 “爷”称父的兴起的确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至此,我们有必要再回到 “爸”的问题上。因为 “父”在语音上已经变得脱离口语,我们的先辈于是另造一形声字“爸”来保留其古音,然而,“父”却经世不衰,足见文人的顽强。现在的问题是,“爷”既为俗字,它又是如何获取“爸”所不能获取的地位的?对于“爷”来说,若只谈其产生问题似乎还好解释,例如可以说它是语言接触带来的,也可能因为本来就是方言。当然,前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因为“爷”有好几种写法,而有的写法与汉字的构造传统并不相符,更使人想到它只是起到记音的作用。但是,一个俗字能进入主流汉语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或许我们永远无法还原那段历史,但我们似乎还可以听到语言竞争中这个“俗字”与保持了“父”的古音的“爸”的厮杀声。毫无疑问,到了唐代,“爷”作为胜利者的地位已经奠定,它进入唐诗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例如杜甫《兵车行》中就有“车遴遴,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称父的“爷”能入诗,说明它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问题在于,无论是来自外语还是来自方言,它要进入主流汉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能有的解释是:(1)原来使用“爸”的人移走了,这一移动使得另外的地方有了“爸”(如上所说“吴人呼父曰爸”、“爸,楚人呼父也”④);(2)“爷”原来的使用者成了新的主人,取得了优越的地位;(3)大唐盛世对语言表现出自己的宽容,换句话说,那个时代对语言项目的各种变异形式都是认可的,而且语言项目的胜利要靠自身的力量。 历史的发展似乎充满着嘲弄。强势的“爷”最终也有走向下坡的时候。“爷”后来又被“爹”逐步取代。今天,“爷”称父仅在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客家话等一些方言中得到了保留,我们还可以在苏州话、上海话、金华话等方言中找到具体的例子。在有的地方,作为词来称父已经不复存在,但在相关的语素中还有所保留,例如温州话的“晚爷”(继父)。然而,今天的西北方言中我们没有找到用“爷”呼父的。中原也很少见,仅在山东找到一处。那么,这么广大的北方地区的“爷”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假设同样是:(1)使用这种称谓的人移走了;(2)使用这种称谓的发生了称谓更替;(3)这里有了新的主人。 尽管广大的北方包括中原地区已经不用“爷”称父,但它的痕迹还是在这个地方的语言中得到了保留。例如称父子俩为“爷儿俩”,我小时候还经常听到“还是爷娘亲”的儿歌。 (四)“爹”类 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成是一种有机体。语言项目有时也和这个社会一样,弱者可以变成强者,而强者也可能再被别的所战胜。“爹”战胜“爷”可以说是又一个重要例证。 在已经看到的文献中,最早记载“爹”的是《广雅》⑤。就字形看,这是个形声字。早期的“爹”显然也是“偏宫”,例如: 《南史·卷五十二》:是冬,诏征以本号还朝。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荆土方言谓父为爹,故云。徙我反。 《广韵·麻韵》:爹,羌人呼父,徒可切。 《广韵·哿韵》:北方人呼父曰爹。 《六书故·卷十五》:岷俗呼父曰爹。 《册府元龟·卷六百六十三》:唯仰食于阿爹,国政悉不敢问也,回鹘谓父为爹。 《天中记·卷十七》:荆土方言谓父为爹,呉人谓父曰爸,回纥呼父曰阿多。 显然,这些“爹”非同时同地之“爹”,但它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观察语言项目更替的又一实例。胡士云(1994)曾经详细地探讨了“爷”和“爹”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认为“爹”并非羌语。他从几个方面论证说“爷”有可能是外来词,而且可能和“爹”同源。但他同时也非常谨慎地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觉得,无论“爷”“爹”是否同源,称父的“爹”如何战胜了称父的“爷”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陈燕(2003)认为,“爹”字的两个反切(徒可切、陟邪切)反映了源于不同地域而又一先一后出现的不同读音。前者出自北方人对父亲的称呼,后者源自羌人对父亲的称呼。 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区分是否正确,但若说“爹”是外来的应该是有道理的。我们考察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发现了大量的证据。例如,维吾尔语喀什话:父亲:A-tA。《委兀儿译语》:父,“阿坛”;《高昌馆译书·人事门》:父,阿答。这些都是可以印证的。另,“父亲”在其它突厥语系的语言中也可以印证:哈萨克语:Qke ata-nFN 塔塔尔语:Qtij 柯尔柯孜语: AtA 乌孜别克语:ÃtQ 撒拉语:aba 裕固语:adZa 图瓦语:adZa(资料来源:程适良,1997) 在中国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布依:po 白语:ati, ate, abo 阿昌语: te/,aph(陇川);tiE(潞西);AphA(梁河) 仓洛门巴语:apa 藏语:papa (分别见喻翠容,1980;徐琳等,1984;戴庆夏等,1986;张济川,1986; 金鹏 ,1983) 就我们的观察,唐代总体是“爷”称父,北宋仍然是“爷”占主导,北宋年间的《太平广记》仍然用“爷”;但到了南宋和元以后,“爹”逐渐扩大地盘,变为强势,而“爷”开始偏居一隅。 (五)“大”类 与“爷”和“爹”相比,“大”类没有那么幸运。一是我们很难在书面文献中找到它的记载,二是它似乎从来没有进入主流汉语,而这两个方面总是紧密相连的。所幸的是,这一称谓类型在今天的方言中得以保留下来,使我们有机会再品评一番。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大类”和“爹”类本来就是一家,或许它也可以说自己曾经荣耀过。但习惯于汉字为中心的我等民族,若干年后大概还是会把“大类”忘掉的,因为它毕竟没有像“爷”和“爹”那样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载⑥。 就目前看到的资料,“大”类和“爹”类似乎应该是同一来源。胡士云(1994)指出,“大”是“爹”(徒可切)的俗字,一般辞书中“大”都没有用作亲属称谓的义项。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学作品中“大”类呼父出现的情况很少。“大”类还有其他一些写法,如“达”、“答”之类,应该都是记音上的缘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大”是外来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今天的方言中,“大”类的称谓仍然广泛地存在。我们不应该把今天的“大类”看作是“爹类”的“异形词”。因为不同地区、不同家族可能会用不同的称谓。而就我的家庭而论,“爹”和“大”还有顺序的差异(郭熙,1999)。今天用“大类”的地区集中在西北,呈片状。 (六)“伯”类 最不幸运的应该是“伯”类。尽管我们的文化中某些方面“伯”的序列居首,也尽管汉语社会中也不乏以“伯”称父者,但这一称谓却似乎从来无缘进入通语。 “伯”的出现应该是很早的。李鼎超(1988:199)指出,“伯”“霸”古音同。今呼伯、叔为“爸爸”,即“伯”或“父”之转。他的证据是“五霸”亦作“五伯”。 我们认为,不能把“伯”看成是“爸”。“伯”“霸”上古同音,但到中古以后的“伯”是入声字,“爸”则是去声。和其它系列相比,伯系的使用范围要小得多。梁章矩《称谓录·方言称父》说“吴语称父为阿伯。”今天的汉语方言中还可以找到很多以“伯”称父的例证。河北沧州、保定,河南郑州、南阳、许昌,贵州毕节,湖北襄樊、宜昌、红安,安徽安庆、合肥,浙江宁波、温州、金华,都有该系列的称谓。 胡士云(2002)指出,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可以用“庞杂纷繁”来概括。对父亲的称谓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北齐书·卷十二》:南阳王绰传云:绰兄弟呼父为兄,兄后主乃俨兄,不知何亦同此称。 《老学庵笔记·卷一》:予在南郑见西陲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葢尊之以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东京,羣盗降附者百余万皆谓汝霖曰宗爷爷,盖此比也。 《通雅·卷十九》:吴下称父多曰老相,自江北至北方曰老子,其曰爷曰爹者,通称也。(熙案:称父为“相”今天看到的方言资料中只有歙县。其它都是爹或爷。可见爷爹进军速度之快。)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八》:爹,徒可反,吴人谓父为奢,却后复收入陟邪反,云巴人呼父为爹。今吴人实称爹不称奢也。按唐中宗称窦从一为国奢则京师人称乳媪父实为奢耳。岂吴音前后殊耶? 《日知录·卷二十四》:哥,唐时人称父为哥。唐时宫中称父称兄皆曰哥。 《山西通志·卷四十六》:称父曰老子,呼小儿曰娃。 我们无法一一证实这些记载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据此来说明汉语对父称谓变化的频繁,方向的趋同,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四、现代汉语社会对父亲各种称谓的分布 在现代汉语社会里,对父亲的称谓有了新的变化。“爸类”的称谓已经相当普遍。我们搜集(包括调查)了161个县城以上的方言点对父亲的称谓,搜集的资料包括《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和《现代汉语方言词典》的全部相关资料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方言志或调查报告。这些方言资料的调查时间不一,记音方式有差异,调查原则也未必相同,与实际情况可能也会有些出入,还有口语和书面语、背称和面称等差异;但我们认为总体上还可以反映出汉语中对父亲称谓分布的面貌。希望熟悉相关点语言情况的同仁协助补正相关资料。 (一)“父”类(53处): 北京、张家口、阳原、唐山、邯郸、太原、大同、离石、隰县、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临河、沈阳、丹东、锦州、白城、哈尔滨、佳木斯、黑河、崇明、南京、南通、苏州、徐州、连云港、涟水、扬州、安庆、阜阳、福州、原阳、洛阳、许昌、方城、社旗、唐河、武汉、宜昌、襄樊、天门、红安、雷州、柳州、吉首、成都、南充、自贡、西昌、汉源、昆明、汉中、宝鸡、白河、兰州、银川、乌鲁木齐 (二)“爸”类(111处) 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张家口、阳原、唐山、沧州、太原、大同、长治、长子、平顺、阳城、陵川、高平、离石、石楼、临汾、霍州、汾西、隰县、万荣、呼和浩特、集宁、赤峰、临河、海拉尔、二连浩特、沈阳、大连、丹东、锦州、长春、通化、白城、黑河、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南京、南通、丹阳、徐州、连云港、扬州、溧水、杭州、宁波、温州、安庆、阜阳、芜湖、歙县、福州、厦门、建瓯、福清、南昌、于都、萍乡、青岛、诸城、济南、济宁、牟平、博山、郑州、商丘、原阳、洛阳、社旗、信阳、武汉、宜昌、襄樊、红安、钟祥、天门、吉首、江永、广州、东莞、梅县、南宁、柳州、桂林、海口、重庆、成都、南充、达县、汉源、西昌、自贡、贵阳、遵义、毕节、昆明、昭通、蒙自、西安、宝鸡、绥德、白河、汉中、兰州、敦煌、天水、银川、乌鲁木齐 (三)“爷”类(20处) 运城、晋城、上海、崇明、苏州、涟水、杭州、金华、合肥、歙县、建瓯、南昌、萍乡、黎川、于都、诸城、钟祥、天门、娄底、江永 (四)“爹”类(89处) 天津、石家庄、平山、张家口、阳原、唐山、沧州、邯郸、清徐、忻州、代县、五台、朔州、大同、天镇、广灵、太谷、长治、平顺、离石、文水、临县、吉县、运城、闻喜、万荣、新绛、永济、沈阳、丹东、锦州、长春、通化、白城、哈尔滨、上海、崇明、南京、苏州、丹阳、扬州、溧水、宁波、金华、阜阳、萍乡、黎平、建瓯、济南、青岛、烟台、利津、牟平、博山、郑州、洛阳、商丘、林县、原阳、灵宝、许昌、方城、社旗、唐河、宜昌、钟祥、武汉、常德、吉首、娄底、江永、广州、柳州、贵阳、遵义、海口、昆明、大理、昭通、达县、汉源、自贡、宝鸡、白河、兰州、敦煌、银川、西宁、乌鲁木齐 (五)“大”类(44处) 太原、娄烦、忻州、五寨、山阴、大同、天镇、和顺、太谷、沁县、陵川、平定、阳城、文水、汾阳、孝义、岚县、呼和浩特、临河、集宁、二连浩特、徐州、连云港、安庆、阜阳、芜湖、歙县、济南、济宁、诸城、商丘、郑州、灵宝、社旗、钟祥、天门、江永、自贡、西安、天水、敦煌、西宁、乌鲁木齐、哈密 (六)“伯”类(14处) 沧州、宁波、温州、金华、合肥、安庆、福清、郑州、社旗、襄樊、红安、自贡、毕节、昭通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父”类总体上是背称,但也有用作面称的。黎锦熙(1933)说方言中未闻呼父为fu的,我们发现今江苏南通话中仍普遍用“父”作面称。 (七)其他 有11处称“老子”:离石、太原、临河、呼和浩特、绥德、武汉、扬州、南宁、南昌、清徐、东莞。 另外,广州、台山、东莞称“老豆”,海口称“阿兄”、“阿官”,福清称“阿叔、阿哥、阿官”、柳州、社旗称“叔”、歙县称“相”、雷州称“阿、尼阿”等。 上面的称谓分布有几点值得注意: (1)“爹”类的使用仍然占绝对优势。如果按照前面所说,把“爹”类和“大”类归并,则总数超过了“爸”类。对此我们起初感到意外,但认真分析后觉得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一是“爹”类在白话小说中的使用数量大,对社会的影响力大;二是现代小说中仍然大量使用,许多现代熟语也都是用“爹”的,它们自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直到近几十年这种情况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例如,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爹”就大量使用。 (2)文献记载中历史上的称谓基本上都可以在今天的方言中找到。 (3)“爷”类呈点状分布,“大”类呈片状分布。 对父称谓的这种状况显然与历史上人口移动有关。例如,西北地区“爹”“达”交互或并行,南京话和西安话中回民都把爷爷叫“把把”,大概就是民族迁移造成的。在西昌的方言调查报告中,没有“爹”,这显然是新的移民形成的普通话社区形成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接触和普通话的推广,同一地区语言也有自己的变化。例如,海口有“阿爹”“阿官”“阿兄”,新派是“阿爸”;而另一些地方以前的报告中无“爸”,现在也大量出现了。 五、“爸”的崛起和“父”的“永恒” 如上所说,清代是“爸爸”崛起的重要时期。但它也经历了和“爹”抗衡阶段。下表列出的是清代一些文学作品中“爸”和“爹”的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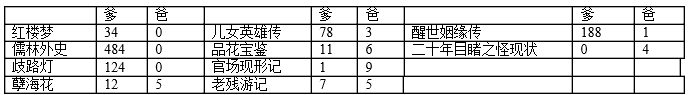 胡士云(2003)认为“爸”是外来的,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就目前的文献看,胡的分析是可信的。但是,胡文没有分析“爸”何以在这个时期才进入汉语社会成为对父亲的主流称谓。在我们看来,“爸”在此时复兴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满人在语言上已经被汉语同化,满人对父亲的称谓实际上也就成了汉语社会的称谓;(2)由于满人的特殊地位,“爸爸”成了一种社会的强势称谓;(3)文人开始对“爸”逐步接受,并找回了久违的“爸”字作为书面用字。但上面的数据已经表明,即使是这个时期,“爸”在书面上的出现仍然是有限的。这可能与文人“天生”的保守有关。直到“爸爸”已经在口语中风行的时候,人们还不愿意在书面上使用,以致将教材上的“父亲”改为“爸爸”的时候还引来非议(黎锦熙,1933)。其实,这种情况不乏其例,黎锦熙(1933)就谈到了《老残游记》的石印本将“爸爸”改为“老子”的例子。 但再往后,人们则开始把“爸”看成是北京话的标志了。胡明扬(1987)说: 旧白话文用“爹”、“娘”、“俺”、“啥”等等,现代白话文改用“爸爸”、“妈妈”、“我”“什么”等等,而“俺”和“啥”成了典型的方言词。为什么? 就因为北京话和一般北方话不同,不说“爹”、“娘”、“俺”、“啥”而说“爸爸”(更常见的是“爸”)、“妈妈”(更常见的是“妈”)、“我”、“什么”等等,这些正是北京话和一般北方话的不同之处。 显然,胡先生说的应该是后来的事。事实上,北京原来也曾用“爹”,即使是用“爸”以后,“爹”也仍然存在。例如《儿女英雄传》三十九回: 只是他自己想了想,既不好按着官话尊声“义父”,又不肯依着乡风叫声“干爹”,也不好通套些儿称作“老人家”,那么大个个儿了,再要“爸爸”长、“爸爸”短,那可就合“唱曲儿的改字儿——没甚么大分别”了。 现代文学作品也反映了“爸爸”发展的进程。根据我们的调查,鲁迅《阿Q正传》没有“爸爸”一词:要么用“父亲”,要么用“爹爹”。老舍的《茶馆》“爸爸”31见,“父亲”4见,未见用“爹”。就整体而论,用“爸爸”是自由的,用“父亲”则是有条件的。 我们对《读书》杂志1979到1998共20年的全部文本进行了统计,共 2246条、2038句使用“父亲”一词。而“爸爸”只有 255条、242句,其中《爸爸爸》是书名,反复出现35次,故应排除,这样,“爸爸”的实际出现就只有120条,不及“父亲”的十分之一,可见“父亲”的顽强。 台湾《当代国语大辞典》(百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对“爸爸”的解释还是:俗语呼父亲。 由此可见,“父亲”处于称父的最正宗的地位这一点还是很难改变的。至于“爸爸”,尽管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似乎也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称谓”。正在“爸爸”成为全国通用称谓的时候,“爸”的变异形式也正在出现。在城市里,“老爸”在青少年中的使用已经有所扩大,这也反映了对称谓方式多样化的追求;另一方面,“爹地”也在南方一些城市中的一些家庭中作为亲昵的称谓(与“妈咪”相应)。它是否还会像以往那样逐步替代原有的称谓,进入主流? 六、结语 语言项目的更替在语言发展中是一种正常现象。称谓当然也是如此。 汉语对父亲的称谓有几点值得注意:(1)始终有通语和方言的差别;(2)始终有雅俗之别;(3)始终呈现出多样性;(4)“父”类始终处于非常稳定的地位。 汉语对父亲的称谓在历史上经历的过程可以表述为:作为背称和正式称谓的“父”类一直得到了延续,口语主流称谓则经历了“爸—爷—爹—爸”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人口移动、文化和语言接触以及各种力量的交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父”是汉语中对父亲的最早的也是一直得以延续的称谓。在它的发展中,规范的力量一直在其作用,但这种规范是限定在一定的领域里边的,尽管它一直被汉语社会赋予正宗的地位,但它却无法阻止口头称谓的变化——“爷”“爹”虽说出自“偏宫”,但是却由于某种现在还不完全清楚的力量,得到了文人的青睐,并通过文人得以传播。 ——虽说称谓是基本词汇,但它的稳定性并非很强,社会因素会直接影响到称谓的变异和变化;如果真的如我们推想的那样,“爷”“爹”“爸”都是外来的,那么就更说明,语言接触中的借用成分完全可以融入到我们的语言中,不必谈“外”色变。 ——“爸爸”的重新崛起并走向全国反映了语言规划的成功,也反映了社会高层语言对一般民众语言的影响力。 ——“父、爸、爷、爹”的演变史是语言接触、民族接触、人口移动的历史。社会语言学的方法不只适合共时的研究,也适合历时的研究。 附注: *本文曾在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2004)上宣读。 ①例如清·梁章钜《称谓录》,页35。 ②王绍新《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见《先秦汉语研究》,程湘清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 ③此表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文美振提供的。 ④再往后,“广东谓父曰爸”,以致于黎锦熙先生(1933)发出疑问:“今吴人方言却鲜闻以‘爸’呼父者,北宋之时吴人殆已入广乎? ⑤“爹”有不同的字形。胡士云(1994)称为同源字,本文主要讨论称谓的更替,故不再考虑“爹”的不同形态。 ⑥留下文字记录的近代小说大概只有《金瓶梅》。 主要参考文献: 陈燕 2003 《“爹”字二音考》,《辞书研究》第3期。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 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 程适良 1997 《突厥比较语言学》,新疆人民出版社。 戴庆夏、崔志超 1986《阿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冯爱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郭熙 1999 《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侯精一等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胡明扬 1987《北京话初探》,《普通话和北京话》商务印书馆。 胡士云 1994《说“爷”和“爹”》,《语言研究》第1期。 ——— 2002《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会议(北京)论文。 ——— 2003《爸爸疏正》,第二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会议暨中国社会语言学成立大会(澳门)论文。 黄雪贞 1993《江永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金鹏 1983《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黎锦熙 1933《“爸爸”考》,《国语周刊》第98期 李鼎超 1988《陇右方言》(刻印本),李鼎文校点,兰州大学出版社。 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词典》系列(共41本),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新魁 1994《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 梁章钜 1988 《称谓录》,天津古籍出版社。 钱曾怡 1993《博山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徐琳, 赵衍荪1984 《白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喻翠容 1980 《布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张济川 1986 《仓洛门巴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正文中已经注明出处的文献从略。文中方言材料涉及的各种方言词典、方言志和方言调查报告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注出,谨此志谢。 (修改稿载《中国语文》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