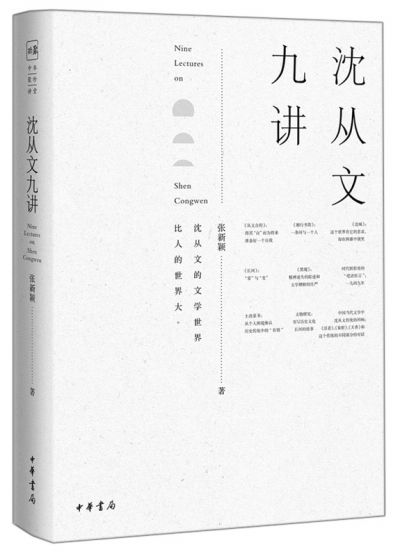陈河,20世纪80年代浩浩荡荡的文学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在离开祖国十几年之后,他的名字被重新擦亮。他的中篇陆续在《人民文学》、《收获》发表,获得国内郁达夫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这在当年,也许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一位旅居加拿大的温州生意人,什么原因使他重拾疏离了十几年的文学创作,又是什么原因使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一跃成为文坛瞩目的重要作家? 6月底,陈河新书《红白黑》推出。此前,这部作品以《致命的远行》为题在《收获》发表,引起文学界的重视。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所说,陈河的作品中有两种东西非常珍贵:一种是从80年代而来的中国文学的遗产,即带着人向何处去的终极思考,带着某种先锋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是他对文本的敬畏之心。陈河的小说不是依据情节讲以吸引人为目的的故事,而是通过小说表现探索性思考,使作品呈现故事之外的深度,这是陈河非常鲜明而可贵的特点,也是今天的文学所欠缺的一种品质。 读书报:80年代,你从部队转业回到温州,在汽车运输公司担任干部,同时是温州市作协的副主席,在社会上、文学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为什么选择了阿尔巴尼亚? 陈河:80年代文学青年很多,那时我也写过短篇、中篇,在浙江有一定影响。但是我觉得再待下去也写不出更好的作品。海明威说:一个菜鸟去学写作,假如学习五年一点成就都没有,那你就不要写了。 我的志向不在官场,也不在金钱,我也想不到志向在哪里,总觉得在温州一眼能看到头。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温州走不了很远,顶多是出国访问。我有一个亲戚,先到匈牙利,又到阿尔巴尼亚做生意,他告诉我说那个地方很好,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时阿尔巴尼亚刚刚开放,有很好的商机。我就动心了。1994年5月,我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做生意,边做生意边学英语。 读书报:在阿尔巴尼亚生活怎样?《被绑架者说》就是你的遭遇吗? 陈河: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比如《脚印》、《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所以到了阿尔巴尼亚总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1998年我被绑架,那时已经在阿尔巴尼亚做了好几年生意,正准备去加拿大移民。一个周末,突然有人打电话说要过来买大批药,我回来后就发现上当了,那个年轻人拿出手枪来绑架我,叫了好多当地人,头上都蒙面,拿着冲锋枪,就把我绑走,关在地下室里一个礼拜。那是一段非常苦难的日子,整天被绑着,头上蒙着胶布,生死未卜。有一天我感觉到防空洞里好像有一点空气流进来,好像有一点青草的味道,又听到外面小鸟的叫声,就想,自己可能离生命不是太远。如果我能自由,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在《收获》上发表。 这很奇怪,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居然还能想到写作。可见写作在我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后来我被警察救出来了,这些经历都成为写作素材。 读书报:重新动笔写作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吗?什么样的机缘重新开始写作? 陈河:究竟在哪里可以安家,埃及、土耳其,我们动过很多脑筋,因为加拿大有移民政策,后来就选择了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很多,中文报纸多,文学团体多,有这种语言环境以后,慢慢会动心;另一个原因,在阿尔巴尼亚是拼命的状态,到加拿大后生意做得不错,生活安定下来了,环境好了,文学的爱好慢慢会回来。 2003年,我在加拿大做进口生意,经常飞上海宁波,到上海后换火车去宁波,有时会买本杂志。有一次在《上海文学》上看到须一瓜的《地瓜一样的大海》,就觉得那时的文学和当年不一样了。那两年,因为母亲发现癌症,我在温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接触到王手、程绍国、哲贵等老朋友,他们也劝我回到写作。后来我在想,也许是母亲临走前给我的一种暗示,让我把步子慢下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开始找书来看,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年选,了解国内的创作情况,看了以后,开始觉得挺不错,后来看来看去,感觉中国文学还是原地踏步,甚至有些还不如80年代的水平,我还可以写。 读书报:在国外十多年的时间,一个字没写吗?重新拿起笔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陈河:十多年虽然没写,但积累了好多,包括经历。2005年正式开始写,先写了《被绑架者说》,当时叫《走出阿尔巴尼亚》,完全纪实,写好后我给温州一些朋友看,程绍国推荐给当时在《当代》的编辑吴玄,杨新岚给改了题目,发表后引起一些注意,麦家看了觉得文字有味道,从《当代》问到我的邮箱,给我发来邮件。当时我刚好完成中篇《女孩和三文鱼》,麦家马上推荐给《收获》,后来的《西尼罗症》也是他帮我推荐的,在《人民文学》作为头条刊出。 读书报:和出国前的陈河比较,你觉得出国后的陈河,在写作上有怎样的变化? 陈河:出国前比较扎实地阅读了西方经典作家的作品,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包括欧美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对中国古典文学有过系统的学习。有一些文学的准备和基础,再加上丰富的经历,年纪大了后思考比年轻时老道一点。 读书报:你怎么评价当下的中国文学? 陈河:中国经济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也有很多毛病,有生存的问题、次序的问题、道德的问题,食品的问题,这些不是偶然的,是中国道德水平的原因。对于中国文学,不管业内业外大家不是很满意。在国内,一部优秀的作品假如不和评论家有直接利益,他们不会去关心。作为评判的体系,已经出问题了。中国整体的文学功利心太强,小说是靠细节不是靠情节,可是很多从剧本改编来的小说,居然也能卖,这很奇怪。我还有一点不满意,中国阅读的趣味不太对,很多人喜欢看官场小说,假如兴趣在那里,好的作品出来得更慢。 现在小说不景气,也不必要求太高,整个世界当代小说中也没有特别好的作品,美国《纽约客》上的短篇也很一般,好不到哪里去。不要对文学指望太高,土耳其那么多年,也就只有一个帕慕克。所谓经典,也是历经百年筛选出来的。 读书报:回到《红白黑》,小说中的主人公杨虹身上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结,你是怎么塑造这个人物的? 陈河:一部小说写到最后,一定会表现作家内心的想法。杨虹是非常理想化的人物。通常来说,特别理想化的人物,会和现实有一种冲突。写的时候我比较节制。一个人物写得好不好,不一定以笔墨多少为标准,关键是几个节点写好了。《日瓦格医生》中拉拉的笔墨不是很多,但她变成世界文学里的经典,想起来心里就有温柔的感觉。 读书报:很多年轻的作家,认为自己的经验不够丰富,阻碍了自己的写作。但是你有一个观点,认为经验并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 陈河:这话我是说给自己的,我是在提醒自己,如果把经历当作自己写作的主要资源,是蛮危险的,总是写传奇的东西,会很快枯竭。但是如果根据经历反映大的事情,反映人生终极的目标,无论写生死或爱情,提升到哲学层面,你的经历对自己就是有好处的。我也是得益于经历。人的经历不是你想经历就经历,经历重要不是决定性的东西,等着经历也不现实。真正好的作家总归能找到好的方式表达,写作最终还是靠想象力。 经验是蛮重要的事情,我是这样想。经验一旦写完,就没办法再写了。记忆里好的材料,本来液体似的流动,一旦用过,等于是固化了,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再重新使用的话自己也会有疲劳的感觉。一个作家,即使经历丰富,单靠经历写作也很危险,因为把经历写完,就没有可写。打个比方,靠经历写作的人很多,同样是靠经历写作,杰克·伦敦经历丰富,但跟福克纳相比,他的作品精神方面开掘不够。有些作家的写作依赖经历,有些没有太多经历。博尔赫思总是待在图书馆里,他照样是世界受尊敬的作家。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01日 11 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8月01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