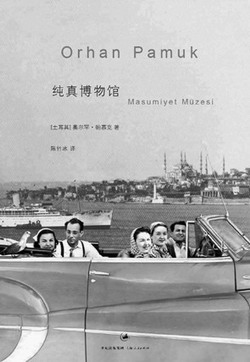 《纯真博物馆》[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陈竹冰译 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 “凯末尔是你吗?”奥尔罕·帕慕克开心地讲述《纯真博物馆》的许多女读者对他的提问,“从广义上说,当然是的,所有堕入爱河的人都会这么干。女人们这样问我时,我觉得她们温柔的微笑仿佛在告诉我,她们深为自己拥有能让男人沉于爱而不能自拔的力量感到幸福。” 自然,帕慕克的创作野心并不仅仅囿于“爱情”二字,尽管爱情是这部小说最显要的外表,但作家对伊斯坦布尔这座城的深情却渗透在故事的每一处缝隙、每一个枝节之间。 《纯真博物馆》中的情爱缠绵悱恻,达到一种极致,可用“癖”来形容。富家子凯末尔在与未婚妻订婚前,遇到多年未见的远房贫寒亲戚芙颂,不可遏抑地爱上她。两人炽热的爱恋过后,凯末尔最终与未婚妻解除了婚约,却发现芙颂早已离他而去。他开始寻找芙颂触碰过的一切,“悉数收集起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将它们放入了自己的博物馆。” 我们可以视这种习惯为恋物,而帕慕克说自己是小说家,不是医生,凯末尔的举动人人皆有,不过在这里形诸文字而已。我想,这其中的潜台词或许是,对一个城市、一种文明的依恋每个人都有,但真正能精妙地表述出来却不是人人做得到的。 我们的精神自由无垠,而身体却总是需要一个现实的区域去容纳,于是有了城与人、一种文明与一个民族之间的交织关系。帕慕克身处伊斯坦布尔,一座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城,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二十世纪七〇年代,正是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穷街陋巷与奢华别墅并存的时期,帕慕克虽非完全的叛逆者,但亦有青年人的躁动不安。数十年后回首,他亟亟瞩目于时间、激情、欲望与占有,记录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百态与如许风云往事。 帕慕克的记录是温情的,他自己也说对众生显示出最大的耐心与敬意。其时,伊斯坦布尔社会的传统与现代,不同阶层之间均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帕慕克笔下的人物不乏离经叛道的行为,但其作品的基调并不是愤怒、乖张的,而是于叛逆中渗透出委婉的温情,显见出时代的变化并未摧毁一个城市、一种文明,当多年后返首回忆时,虽一切不可逆,但终究一切皆可记,因为那是自己的“城”。 自己的“城”埋藏着自己的爱恋,其来有自,却没有承诺与未来的支撑,以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痴迷,默默地等待,悄悄地收集,不说耳坠、发卡、手帕等,仅烟头就有四千二百一十三个,因为那经过了爱恋的人嘴唇的润泽,自然弥足珍贵。有这许多琐细感怀的收藏物进入纯真博物馆,换一个角度来看,岂不是也在收藏着一个日常的“我城”——伊斯坦布尔。 一个城市的倾覆,往往也意味着一种文明的倾覆。反之,一种文明的历久弥新,其承载体——一座古老的城市在岁月的流逝中并未被荡涤一清,而是因身处其间者的温情和敬意吸纳着适足的丰富细节——有形的和无形的。帕慕克显然做得足够多,他创作的人物“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别无他求。 有论者将《纯真博物馆》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洛丽塔》”,自有古怪之处。但如果着眼于对一种文化的迷恋(《洛丽塔》时被解读为暴发户的美国文化对欧洲文化的一种微妙暧昧的觊觎),也不乏卓见。中国古代也早有“香草美人”式的借男女情爱隐喻更宏大主题的传统,代不乏人。帕慕克声言《纯真博物馆》是其“最柔情的小说”,联系2006年瑞典皇家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颁奖词中有“帕慕克在对故乡忧郁的城市灵魂的探求中发现了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新符号”等语句,这“柔情”的情就不可做狭义的理解了。回溯帕慕克以前的作品,这一点能看得更清楚。 帕慕克实实在在地写男女情爱,专注且痴迷,而于是中悄无声息地透出伊斯坦布尔的气息和脉动,润物无声,尤令我们惊讶。或许帕慕克对他的“城”已爱到了骨子里,谈星辰,谈微尘,却实在都可见到这座“城”。于是,故事以“色欲沉迷开始”,终以“幸福与感动”完结。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5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