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幅卡夫卡的照片都让人感到他的眼神无法禁闭,这种眼神和他的文字像梦境里的昆虫爬行而出,大卫·林奇也有表达的欲求,他借助影像和声音虚构出梦境,这可以让他在白日里幻视幻听,在黑夜里内心深处得到自我的歇斯底里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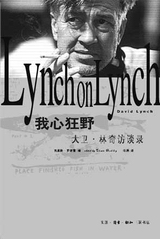 梦醒时分,我们有一种抑止不住的欲望,要把梦和我们的未来联系起来,梦已然成为了我们现实的一部分,一种历史的烙印和命运的征兆。这是弗洛伊德的遗产,这个遗产并不在乎你是不是直接读过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思想和思路以及那些误解、篡改、庸俗化他的思想和思路一起构成了一面镜子,我们不经意地就会在这个镜子里打量自己,盘算别人。睿智的英国已故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调侃过精神分析者在一个拄杖而行的男性形象前的思维,这种调侃自然是对精神分析的所谓“泛性问题的嘲讽,但也无疑是一个沉溺于“理性”光辉的智者在过度清醒或者理性后对“精神分析”的某种失察。
梦醒时分,我们有一种抑止不住的欲望,要把梦和我们的未来联系起来,梦已然成为了我们现实的一部分,一种历史的烙印和命运的征兆。这是弗洛伊德的遗产,这个遗产并不在乎你是不是直接读过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思想和思路以及那些误解、篡改、庸俗化他的思想和思路一起构成了一面镜子,我们不经意地就会在这个镜子里打量自己,盘算别人。睿智的英国已故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调侃过精神分析者在一个拄杖而行的男性形象前的思维,这种调侃自然是对精神分析的所谓“泛性问题的嘲讽,但也无疑是一个沉溺于“理性”光辉的智者在过度清醒或者理性后对“精神分析”的某种失察。
基于拉康立场的精神分析所强调的“创伤”和“恐惧”成为一种“自我”形成的需要,一种不是真的见鬼而是心中有鬼的心理机制,不是真的“创伤经验”和“恐惧经历”,而是对“创伤”和“恐惧”的需求,这种需求是通过对“他者”的确立和升华来获得“自我”的心安理得和快感体验的通道。在这个层面上,精神分析理论持有者对美国著名导演大卫·林奇和他的作品的高度兴趣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完全成立,尽管大卫·林奇宣称自己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毫无联系,以及他的密友可以做出证明等等。 1946年1月20日出生在美国蒙大拿州密苏拉市的大卫·林奇,是美国艺术圈里的多面手,在电影、电视、绘画、摄影和音乐等领域内都确定了自己的声望。大卫·林奇把自己的传记曾经浓缩成三个词:鹰牌童子军、密苏里、蒙大拿,这个浓缩是他对自己的童年的总结。他的童年成长在一个健康、健全的家庭,父母对他的关爱一直延续到他成年之后,父亲虽然不明白他的电影创作,但是一直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但是在大卫·林奇的电影作品中却经常构置了诡异和不安的家庭关系。在这点上,大卫·林奇和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大卫·林奇对于这位老前辈极为钦佩,他曾说过:“我亲眼目睹的最糟糕的事就是在戛纳电影节观众们对费里尼的一部片子嘘声一片。那是《我心狂野》(1990)上映前一天晚上的事,他们竟然嘘费里尼的片子。”费里尼和大卫·林奇同月同日出生,他的作品几乎全是直接的记录自己的梦境,如他自己所说“梦是我唯一的现实”。费里尼的作品很多元素都是来自对童年记忆的梦境化,或者直接就是童年的梦境。费里尼的伟大正在于对现代人的内心世俗欲念极为直率地暴露,完全没有对这种欲念的什么深刻自省和分析。费里尼是一个在现实中记录梦境的人,费里尼说荣格是我老大哥。而在这一点,林奇却完全相反,他断言自己和弗洛伊德毫无关联,但是却又在现实中睁着大眼虚构自己的梦境,因为他需要这种想象或者梦境来完成“自我”的定义。林奇的作品不是像费里尼那样的我梦到了,于是我拍我的梦,而是感觉到有个东西很有意思,我可以把它做成梦一样的东西。比如他看到了一对夫妻不断收到录像带的故事,于是他编制了梦境一样的《迷失高速公路》(1997)。 大卫·林奇是一个对现实有着不确定感的人,这是他睁着眼睛造梦的心理基础。而这种不确定感是身处现代社会的敏感者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如何被演化成作品里梦境一样的氛围,在这个渗透不安和诡异的氛围中呈现出林奇自己称作“迷失于黑暗和混乱中”的那种状态?或者直接地说林奇如何编造自己的梦境来表述自己的不安,满足自己对诡异和恐惧的需求?他如何获得快感体验? 克里斯·罗德雷在给《我心狂野:大卫·林奇访谈录》撰写的序言中敏锐地提及:“大城市的兴起也是产生诡异感的一个原因。”我所要强调的正是林奇通过对空间的破碎处理,让空间碎片成为虚构的“记忆的碎片”,成为当代爱森斯坦式的蒙太奇装配原理的另一种演示,这种碎片符号的组合不再是传递确定的思想,而是构成思想的迷宫、记忆的迷宫,一种类似梦境的氛围。罗德雷的精辟论述清晰地说明其中精神病学的基础:“当人们开始感到已经与自然和历史隔绝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种与疾病和心理骚乱相联系的现代焦虑症———特别是表现为一种空间性的恐惧(广场恐惧症和幽闭恐惧症)。”《迷失高速公路》一方面是主人公被空虚的空间所包围,一方面又用幽暗黑夜中被火柴光亮瞬间照亮这种类似方式,让空间呈现为瞬间碎片,于是人的不确定感和不能自拔的状况得以传递。林奇所用的方式是构成梦境一样的画面,然后用摄影机去将梦境图景“复制”下来,这点和安东尼奥尼直接用摄影机在秩序的、逻辑的、理性的空间中进行截取,然后再重组为不确定的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上安东尼奥尼是电影化的电影导演,而林奇是绘画式的电影导演。 大卫·林奇遗忘在机场的行李箱中有老鼠和苍蝇,他遗忘在房东冰箱里有12只老鼠,他是一个蚂蚁牧人,经常使用老鼠、苍蝇与蚂蚁这样的东西构成绘画作品,这是因为他需要把物质世界本身梦境化,这点他和费里尼是类似的,费里尼也是一个不在摄影棚中做出梦境就不能拍摄的导演。林奇的虚构梦境的方式除了对物质空间梦境化之外也包含着有意模糊叙事的清晰度,这种方式在《穆赫兰道》(2001)中就集中展现出来。但是这种打碎叙事线的完整性并不是林奇最有贡献的地方,真正的贡献反而是他和安吉洛·巴德拉门蒂合作创作的电影音乐,这个贡献一方面是给电影的梦境配乐,同时在现代音乐领域也是独立的优秀作品。 大卫·林奇是在拍摄《蓝丝绒》(1986)期间,经人介绍才认识了作曲家巴德拉门蒂,现在他已经成了林奇创作班底不可或缺的成员。正是由于巴德拉门蒂,林奇才发现自己和音乐的距离如此之近,发挥出他在旋律上的天赋,而这音乐也成为林奇电影风格的一部分。这对搭档的合作成就了朱丽·克鲁斯的两张唱片,《工业交响曲1号》的演出,而《蓝丝绒》的电影原声音乐也成为现代音乐的一个经典。我们与其说林奇是通过电影结识了巴德拉门蒂,结识了音乐,不如说是林奇因为虚构梦境的欲望而需要巴德拉门蒂和音乐,这样他找寻到满足虚构梦境的欲望的新路径。 梦对于我来说是无声的。对于无声的梦境,林奇的音乐或者说音效是如同春雨入夜一样,静静地入梦。林奇-巴德拉门蒂的音乐完成了对梦境的有声化想象,这种音乐使得演员的嗓音也梦境化了,林奇-巴德拉门蒂对音乐的音效化的处理,让音乐成为音效和气氛,让旋律成为对白,而演员唇齿间的对白成为旋律的一部分。他们在布拉格为《迷失高速公路》的音乐录音时,布拉格交响乐团的那些古典乐器发出的声音被装在篮子里、铁管里的话筒拾取,经过数字处理成无声梦境的声音。这种对音乐的变形是对无声之梦的声音虚构,是睁眼做梦同时的竖耳听梦。 大卫·林奇说:“卡夫卡是一位令我觉得亲如手足的艺术家。”这位导演外表文静、衣着整洁。他刚出道的时候,制片人无法把这位将最上面的一颗衣扣都要扣紧的年轻人和《橡皮头》(1976)联系起来。我想卡夫卡也是一个把敏感的心禁闭在整洁衣着里面、禁闭在干净面孔的背后的人。但是每一幅卡夫卡的照片都让人感到他的眼神无法禁闭,这种眼神和他的文字像梦境里的昆虫爬行而出,大卫·林奇也有表达的欲求,他借助影像和声音虚构出梦境,这可以让他在白日里幻视幻听,在黑夜里内心深处得到自我的歇斯底里快感。 (《我心狂野:大卫·林奇访谈录》克里斯·罗德雷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