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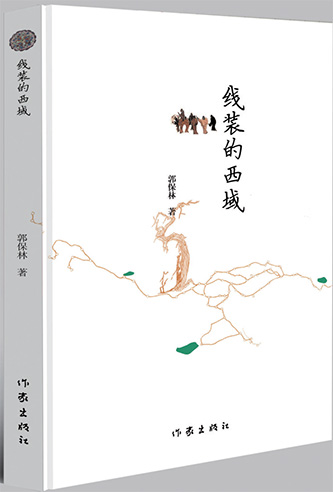
我对西部情有独钟。青少年时期,面对着地图上那片广袤的棕红色高地,常常产生辽阔的想象和深沉的向往。这是片神秘而又神圣的土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了西部之旅,从1991年到2004年,十几年间,我年年走进大西北,有时一年两次去西部采风,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内蒙古草原、塔克拉玛干大漠、柴达木盆地,还有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山山麓都留下我匆匆的履痕;戈壁、大漠、冰川、圣湖、草原、林莽这些巨大的符号,都震撼过我的心灵。我一生重要的几部著作都是写大西北的。
大西北是一部古老的书卷,是用羊皮纸书写的史诗,虽然我十几年去西部采风,实际上我连部巨著的目录都未读完,太丰厚了,一生都不会读出个门道。
我觉得只有大西北的旷野、戈壁、大漠和内蒙古草原的大境界、大空间,才能容得下我一颗骚动的灵魂,铺得开我成吨成吨的情感。1991年之夏,应内蒙古《草原》杂志主编丁茂、吴佩灿先生(令人悲痛的是他们已归道山)之邀,我在草原上进行了几十天的采访和体验,我相继来到乌兰察布草原、巴彦淖尔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与锡林郭勒大草原。文联和《草原》杂志经济并不富裕,丁茂、吴佩灿,还有尊敬的许淇先生安排包头国棉厂出车,每天带着地图旅行,让我饱赏了草原无限风光。
草原,一幅绿色的谜语,我永远猜不透它的真谛;草原,永恒的史诗,我永远读不懂它的内涵。草原是美丽的。我当时曾想,草原倘若能折叠,我会扛起一卷带回我的故城;草原的阳光是纯净的,倘若能剪裁,我会裁一方挂在我的窗前。
后来,我在作品中写道:“我喜欢草原,草原的辽阔,草原的舒朗,草原的纯净,草原的漫漶。那飞翔的云,那潇洒的风,那奔腾的马,那如云卷般的羊群,那山岭跳跃的线条,那河流动荡的旋律,都透露着一种生机勃勃而坦然自信的心态!再浮躁的人、再浅薄的人走进草原,也会变得雄沉和宁静。”
我写草原的散文陆续发表后,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先生立即撰文并给予高度评价,文章以书信形式发表在《文汇报》上,引起较大关注。结集为《一半是蓝一半是绿》,著名评论家冯牧先生热情称赞:“这就是这位诗人气质的作家笔下的草原夜色。”
当散文集《一半是蓝一半是绿》的样书刚寄达济南,我从邮局取回,还未来得及分赠朋友们,接到上面通知,派我去西藏采访“党员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真是天赐良机,我对西藏早已心驰神往,那片神山圣水曾经使我产生几多迷离的梦幻。第二天我便随记者采访团飞往拉萨。
我们先是飞到成都,飞机到双流机场已是黄昏,在机场宾馆休息一夜,黎明时分起飞,经过两个多小时,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时间仍是黎明,好像时间停滞了,成了一个概念,当太阳在西部高原升起时,那真是绮丽璀璨动人的景观,我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令我咋舌的是高原的太阳,那光芒简直是用纯金锻造的,黄澄澄、金铮铮、亮晶晶,明丽、鲜艳、纯贞。我还未见过世上有如此美丽动人的阳光,没有污染、不掺任何杂质的阳光!还有天空是那样蓝,蓝得令人难以置信,蓝得像走进真理的终极。”
我们采访时间有限,满打满算只有8天,孔繁森事迹特别突出,他三次援藏,常年在高原缺氧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除召开座谈会听取他的事迹,我们还要到他生前工作的地方采访。我们乘车到墨竹工卡、贡嘎县、日喀则,墨竹工卡当时还是一个荒凉的小县城,没有楼房,一两条街道,像个大村庄。接着我又去贡嘎县采访,进牧家,进帐篷,还沿着雅鲁藏布江,在喜马拉雅山大峡谷里穿行,道路崎岖,险崖巉岩,雄势滔滔的岩石,宣示着庄严的沉默、肃穆的喧嚣;斑驳的色块弥漫着恐怖氛围,令人感到一种悲怆、苍凉。雅鲁藏布江在深山峡谷中咆哮奔腾,苍鹰在空中盘旋,岩羊在山腰间跳跃。深褐色的岩石缝间长着骆驼草、索索柴,已至冬天还有星星点点的野花。天空湛蓝,大块的白云静静地伏在天幕上。旷达、寥廓、苍茫,那云彩多么高傲,独占着广阔的天宇!
我们去过海拔4600米的岗巴,在那里更是荒凉、荒芜、荒蛮,好像走在另一个星球上,没有树、没有草、没有绿色,只有风在呼啸、不时发出尖厉的吼叫,像亿万匹雄狮在峡谷中咆哮。阳光汹涌澎湃,恣情纵横,气势磅礴。高原的阳光成了一曲震天撼地的《英雄》乐章。
经过三个月的奋笔疾书,我写就了31万字的《高原雪魂——孔繁森》,书一出版立即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新华社发了通稿,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新闻联播做报道,全国各大媒体陆续发表评论,选载、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虹云和方明配乐播送全文,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还译成藏文播放。
《高原雪魂——孔繁森》出版不久,也就是1996年,我又有机会去西部采访,此次去新疆塔里木采访石油天然气开发公司,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漠,我要完成一部反映石油工人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石油、天然气,对我而言是极其生疏的领域,无疑是一次新的挑战。我满怀信心地西去塔里木。
这是我生命册上最难忘的一章。塔里木盆地56万平方公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35万平方公里,沙山、沙丘、沙沟,起伏跌宕,涌涌荡荡,无边无涯,人称“死亡之海”。这里气候干燥,每年6月至9月,地表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空气温度50多摄氏度,更可怕的是风暴,从3月到10月,是风季,沙尘暴刮起来,天昏地暗,沙丘流动,一切重新洗牌,沙凹变成金字塔的沙山,沙山削为平地。没有绿色,没有飞鸟,更无走兽,一片死亡的沉寂。
早在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骑着骆驼在维吾尔族人的引导下横穿千百年来无人涉足的大沙漠,差一点葬身沙海。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政府组织地质队员在大漠勘探石油天然气,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才发现油矿和油气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从全国各大油田调来6万石油大军在这里进行开发和开采。我去采访时,已开采了9年。这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我对石油、地质勘探,无点滴知识,指挥部给送来一沓《中国石油报》和《塔里木石油报》合订本,我日夜翻阅,从中获得了地质勘探和钻井采油等基本常识。我开始采访,到天山脚下采访地质队员,他们顶风冒沙,在戈壁滩上“拉线”,荒山野岭,连片树荫也没有,烈日当空,晒得人头晕,而沙石又热得烫人,环境艰苦,超出想象,夜晚又寒气逼人,住在小小的帐篷里,既不挡风,又不避寒,后半夜往往冻醒,风大时连帐篷都刮得无影无踪。我采访了数以百计的物探队员、钻井工人,采访了参加塔里木石油会战的许多干部、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我带回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和近百万字的相关资料。我的采访本夹杂着大漠的飞沙,天山、昆仑山的烟尘,戈壁滩焦干的气息,还有黑色石油浓郁的芳馨……当我铺开稿纸,书写这些为共和国寻找太阳的人时,我常常激动不已,墨到淋漓、情到热烈时,那简直是在燃烧,笔飞墨舞,我一口气完成了37万字,展示了一代石油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风貌。
《塔克拉玛干:红黄黑》出版后,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各大媒体都给予报道并纷纷发表书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虹云、方明全文配乐播送,时过两年北京出版社又再版此书。此书也获得多种奖项。
后来应百花文艺出版社之约,我去宁夏采风,受到宁夏文联热情接待,在地方史专家张树林先生的陪伴下,我走遍宁夏大地,黄土高原的序篇就写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母亲河裂地而来,呼啸而去,北有贺兰(山),南有六盘(山),腾格里沙漠伸出长长的舌头,舔噬着这方山野,黄河擦肩而过,古长城纵横盘桓,人称宁夏是“长城博物馆”,烽燧、垛堞毗连,贺兰山的岩画、戈壁滩上的西夏王陵,西海固的干旱,沙坡头绿涛翻腾,这斑驳陆离的色块,这多种文化的融汇(伊斯兰文化、西夏文化、边塞文化、黄河文化),闪烁着宁夏大地绚丽灿烂的文明之光。
我曾经说过:“西部是诗,是苦难铸就的史诗。西部是一片壮美而丰富、苍凉而又浑厚的土地。西部是曾经拥有辉煌而又失辉煌的土地。”一踏上这片粗糙、粗狂、粗粝的土地,我心中的诗情和诗意便蒸腾而出,看到那赤裸裸的大山、苍莽的荒原、起伏跌宕的沟壑,心里便产生一种亲切感、一种敬畏感,这是一片充满梦幻,也充满期待的大地啊!
感谢西部,感谢生活。风从西部吹来,把我的日子吹乱,也清醒了我的精神。使我深知如何增加生命的深度与厚度。当我的肉体化为泥土时,但愿这片土地能留下我血肉模糊的证词——那就是我的写作;风沙弥漫中留下我注满汗水和艰辛的足迹,不管是趔趄的还是坚实的。
(《线装的西域》,郭保林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