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眼睛》的故事与人物关系,都在师傅与徒弟之间生发和蔓延。刘建东在四个工厂师徒故事里试图安放的是一些更大的词、更具超越性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如何“顺从内心”又如何被外部声音所塑造,一个时代正反两面的荒诞与真切以及对自由与责任的追问等等。
刘建东所选择的叙事声音与他的文学观念、写作方式相呼应,内含着对经验的规避和抗拒。写小说的过程,是他与自己创造的人物故事间的角力和砥砺,有时候那些先在的观念被印证、被落实,有时候则被挑战、被质疑——而作者此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品质,是诚恳地面对生活真实与文本真实,还是不管不顾地强行推进情节、将观念进行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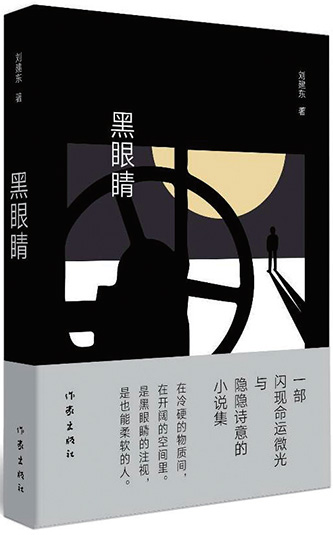
刘建东的小说集《黑眼睛》中容纳了《阅读与欣赏》《卡斯特罗》《完美的焊缝》《黑眼睛》四个中篇。四篇小说在叙事逻辑和情节设置上彼此独立而自洽,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部小说来通读——虽然四篇作品中的人物面目各异,情节上也似乎全无显在关联,但这四个故事都发生在一家名为“八方炼油厂”的国企,之间参差镶嵌闪烁着的都是铆钉、铁锈、红色的安全帽、管道或钢板……每个故事的展开和演绎、每一段人生命运的起伏中都分布着高高低低的装置塔、密密麻麻的管线、进进出出的油罐车……
打开这本书,就走进了一座上世纪老牌国企的60、70、80年代,生产与设备运转的间隙里,厂房与车间的各个角落里每一天都发生或酝酿着不同的情感和故事,除了出产数以百万吨计的汽油、煤油、液化气,还生发出许多理想与幻灭、忠贞与背叛、爱与恨、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蜿蜒曲折、荒谬又真切的缠绕和交锋。
有意思的是,尽管刘建东在文本中刻意地随手布下那些铆钉、螺丝、阀门,那些管线间、蒸馏塔——是的,“刻意”的“随手”,我断言作者在这些貌似不起眼的背景和细节处其实是很花了心思的,他想要通过这些为自己的叙事安顿好一个妥帖的、极具实感的工厂经验背景。但其实这四篇以工厂为背景、以工人为主要人物的作品,又并非我们印象中的工厂小说,刘建东着意处理的并非历史与当下工厂生活中的表层经验,更不是当代文学传统中工业题材关于工厂与改革,工人与国家、与工业化等问题,甚至也不是时代中工人的际遇和人生起伏。刘建东的小说志向似乎并不在于此。
这部集子里,每一篇小说的主要故事与核心人物关系,都在师傅与徒弟之间生发和蔓延。作为当代工业生产和工厂生活中一种独特的关系,师徒既是一种官方认可的工作安排,同时又混杂着民间伦理中复杂的人际、人情。刘建东正是从这个角度进入工厂和工人的生活,在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里缓缓展开自己的关照和审美偏好,他在四个工厂师徒故事里试图安放的是一些更大的词、更具超越性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如何地“顺从内心”又如何被外部声音所塑造,一个时代正反两面的荒诞与真切以及对自由与责任的追问等等。但他的小说并不紧密地附着在这些经验上,他的写作属于观念性很明显的那种。所谓“观念性”,在我这里并不具备褒贬意味,我用它来形容一种创作动机和写作状态。刘建东对面前的这个世界有自己比较坚持的理解、认知和观念,当他开始写作一部小说,与其说是源于心里的故事冲动、情感冲动,不如说是观念冲动,他想要经由一些故事和人物去释放和分享自己对于世事人心的某种看法。而精心剪裁素材、塑造人物和铺展情节的过程,其实是作者为自己想要表达的观念赋形的过程。
这一点,刘建东和同为河北“四侠”的李浩有点像,他们似乎都特别受不了自己的小说被经验的毛茸感和生活的汁液感轻易覆盖,受不了鲜明的主题与深刻的思想被所谓“现实感”的情节细节所淹没。其实,任何自觉的写作都是观念先行的写作,关键是如何平衡好文本内部经验铺陈、人物塑造与观念的关系,坐实小说叙事的说服力和可信度、经验的可信度与观念的说服力。
刘建东写小说的过程,大概是自己与他创造的人物故事之间的相互角力和砥砺,有时候那些先在的观念被印证、被落实,有时候则被挑战、被质疑——无论人物和故事自在的生活逻辑还是内在的文本逻辑,它们当然都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作者此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品质,是诚恳地面对生活真实与文本真实,还是不管不顾地强行推进情节、将观念进行到底?在这部集子里,《阅读与欣赏》的文本质感与惊艳,《黑眼睛》稍欠说服力的叙事效果,皆源于此。
四篇小说中都回响着一个强大的叙述人的声音,一个介于读者与故事之间的声音,它在文本中不仅是一个功能性的语言介质,更是小说内容的重要部分。有时甚至人物语言都是被刻意怠慢的,叙事语言被放大,人物语言被淡化。这是刘建东刻意、自觉地操持着的小说语言,一个即使故作轻松其实却总保持着紧张感的声音,它直接参与到小说的“阴谋”之中,力图引导读者在小说阅读中了然什么、忽略什么。有时候这声音甚至在阅读时能让你感受到故事传达给你的强大压力,它有效地实现了一种阅读时的间离感:刘建东讲故事给我们听,但同时不允许我们听的太全神贯注,他要时不时地跳出来阻止读者“听评书落泪、为古人担忧”的投入。刘建东所选择的叙事声音与他的文学观念、写作方式是相呼应的,内含着对于经验的规避和抗拒。
这四个中篇里,最具意味的是《阅读与欣赏》。这是一个操持着两重叙事层次的故事,关于命运、人生,也关于写作。“那一年,我师傅冯茎衣30岁”,小说开篇,女主角冯茎衣不掩饰、不隐晦的恣意人生便被和盘托出,她“风姿绰约”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沉浸在情欲的暖流之中”放荡不羁,随心所欲。小说中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事人又是参与故事的人物,在“我”的观察和讲述中,冯茎衣波折的人生经历依次呈现分明,她经历着丈夫的意外死亡和自己的性情大变,经历着劳模的风光和意外的牢狱之灾……作为师傅信任、亲近的徒弟,“我”是师傅冯茎衣跌宕人生的见证者和讲述者,而讲述的过程,恰也是阅读和欣赏人生这本厚重之书的过程,更是一个小说写作者修炼自己去理解他人的真理、把握一个人的内部与外部世界的过程——这是小说的另外一个叙事层次,“我”在工厂工作之余,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小说写作者,在与师傅相处的时间里,在旁观其人生选择与命运际遇的过程里,“我”也在渐渐学会感受“真正的生活”,慢慢领悟写作的真正要义。
这两重层次的叙事不是水平并行的,而是拧麻花般缠绕在一起的,叙事的遮蔽和打开的分寸感把握得很精准,对应着这个世界本身整体性的复杂丰富。其实这恰是写作实践中深思熟虑的观念与诚恳的经验取舍之间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其首发刊物《人民文学》的卷首语中赞其“叙事的褶皱及铺展手法、叙述的声色及其张力控制等等方面”“足可作为写作课堂研读的文本”。直到小说结尾,无论是对作品中的“我”还是作者刘建东来说,冯茎衣“美丽而带刺的生活”,大概始终都是一个未解之谜。关于冯茎衣的讲述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不断了解着别人的生活、理解着写作的要义,最后实现了对自己日常人生与文学生活的双重检阅。小说双层次的叙事结构里更暗含着一种关于人生与写作的双重提醒:也许我们始终无法真正地理解他人的真理,而只能努力地让自己心怀包容和善意;也许小说永远无力呈现所谓的本质与真相,而只是努力地让我们看到对真相的寻找过程。
刘建东的写作一直被贴着明晰的“先锋”标签,而小说集《黑眼睛》中的作品因其“开始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被一些评价认为是“从先锋叙事中撤退”。之前的写作中,刘建东的确充分展示过自己对于20世纪西方现代派和中国80年代先锋写作经典作品的致敬,展现过自己对于文体形式、叙事技巧的兴致盎然,特别是多篇作品中对于“荒诞感”这种表现手法更呈现出一种依赖和迷恋。不过,在批评家那里,“先锋”是一种文学修辞,是一种评论话语套路,往往形容其写作的惯有形式、手法,与80年代中后期以形式革命为核心特征的那一批小说的相像;更是文学批评的偷懒——用一种轻易的笼统概念来省却文本精读、有效阐释。用“先锋”来定义刘建东,其实远不及李敬泽评价他时那句“轻逸而古怪”来得及物和精准。
而关于“先锋”,刘建东自己曾有过表述:“先锋的意义可能并不是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而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对文学有什么样的解释”。我觉得,这才是先锋文学的正解,也是刘建东对小说集《黑眼睛》最好的自我注释与阐释。
■创作谈
写下去,并写得更好
□刘建东

1989年大学毕业后,我在炼油厂工作生活了整整十年。作为宣传部的记者、编辑,我几乎每天都要到装置间、车间里去采访,了解生产进度,报道先进事迹与人物。在我最好的10年青春岁月中,在我从学校课堂向社会课堂转变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那些生产一线的工人师傅们,他们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有着无私奉献与默默求索的精神品质,他们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影响着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从工厂出来将近20年的时间,那些鲜活的记忆、生动的个体,时时在呼唤着我。而当我真正地开始思考他们、书写他们时,我发现,我仍然生活在那里,与他们在装置间、管线间相谈甚欢;我依然能够看清他们的面庞,能够抵达他们的内心世界。我相信一点,只有最细微的所在才是真正的现实,只有被遮蔽的地方才是时代的脉搏,只有最容易忽视的身旁才是历史的起点。
最初写作时,我写得比较多的是思想上的“父亲”,比如长篇小说《全家福》。“师傅”一词,是我想要开拓自己写作路径与天地时,所要寻找的一个有着特别意象的词语,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师傅”,不是尊与卑,不是简单的传承与发扬,它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你前行的道路上、在你成长的历程中,你与强大的传统、优秀的品质、美好的梦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既是《阅读与欣赏》中那个敢爱敢恨、追求自我价值的女师傅冯茎衣,是《卡斯特罗》里那个在现实的困境中挣扎的师傅老庄,是《完美的焊缝》中那个认不清自己的师傅,又是《黑眼睛》中那个被时代所裹挟的骆北风。他们影响着你、鼓舞着你、激励着你,同样也束缚着你、羁绊着你。你与他们情感相联、思想互通,却又在时代的某个路口犹疑与徘徊。
我在工厂工作的10年间,正是中国工业发展最迅速的10年,而伴随着速度的成长,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个链条——工人的思想追求也变得多元而丰富。所以当我去书写这一特定的群体时,我没有去写他们在工业发展中被同化的那些元素,而是想找到他们别于他们的前辈的异质,就是他们有在这一进程中独特的个性的张扬与散发。他们的个性与坚硬的装置和设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与那些在管线里穿梭的油气一样,是有温度的;他们又和那些装置设备上的零部件一样,是千差万别的。
从小说的外观上看,似乎这部集子里的小说,与我之前所坚持的先锋写作不一样了,与《一座塔》这样在形式的探索上走得更远的小说相比,面貌可能更加可亲可敬了。但一直以来,我对小说的划分始终有足够的警惕,我对于“现实主义”、“先锋写作”这样的词不以为然,我觉得小说家的写作显然不是为了这些词语而存在的,小说家的志向在于如何能够更合理、更理性、更艺术地用文字来搭建一个美好的文学世界,而不是为了某些主义而束缚自己的思想。
当你在写作时,你的背后是整个世界;当你打出一行行文字时,你眼前是一片崭新的世界。它们是同一个世界,又不是同一个世界。真实的、虚幻的、历史的、文学的、前辈的、自己的……但有一点是你无法摆脱的:你坐在那里,虚构一片新天地时,你就切实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之中,不管你喜欢它还是讨厌它。这是小说家的宿命,也是我们开始想象的宿命。所以你有在文字中驰骋奔腾的自由,但更有对得起你生活其中的这个时代的责任和义务。
鲍勃·迪伦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作《答案在风中飘》。歌中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真正称作一个男人?”一个作家究竟要写出多少作品才能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每一个作家在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写下去,并写得更好,是我的座右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