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隐在历史褶皱处的青春记忆与人性书写──从《芳华》看严歌苓小说叙事的新探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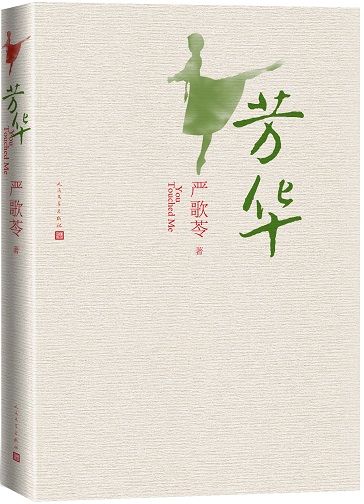
严歌苓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芳华》甫一面世,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芳华》具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是以第一人称来描写她当年亲历的部队文工团生活——作家虽然也写到了后来人物的命运变迁和故事,但只占小说很小的比例和部分。给人近乎作家“自叙传”这样的读后感,一点也不奇怪。且不说严歌苓的人生经历已多为人了解:她在军队呆了13年,从1971年12岁入伍直到25岁部队裁军退伍。整整跳了八年舞,演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她演过喜儿;演出舞蹈节目《边疆女民兵》《草原女民兵》《女子牧马班》,扮演英姿飒爽的女民兵;表演藏族歌舞《洗衣歌》;《小常宝请战》(《智取威虎山》)里演边唱边跳的小常宝……然后做了两年编舞,再成为创作员,与笔墨打起了交道。从军经历几乎伴随了严歌苓的整个青春年华,而这段从军经历成了她的创作源泉之一,且不说早期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2005年首版的《穗子物语》(其中《灰舞鞋》《奇才》《耗子》《爱犬颗韧》《白麻雀》是涉部队生活题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且其中部分篇章当时一经刊登,就高居各排行榜的首位。《穗子物语》虽然以长篇小说的名目出版,但所收是一系列与“穗子”相关的短篇和中篇。严歌苓自称“穗子”是“‘少年时代的我’的印象派版本”,现在看来,其意义和价值远不止于此,这些短、中篇还是作家长篇艺术构思与创作的沃土,让我们在许多年后能够拥有这部留有文工团员们年轻倒影的长篇《芳华》。《芳华》里的萧穗子,就是《穗子物语》当中一些篇章里面的“穗子”。《芳华》中萧穗子因为“谈纸上恋爱被记了一过”,是一笔带过,在《灰舞鞋》里反倒是头尾兼备的叙事。《芳华》近乎结尾,才揭晓当年是郝淑雯用“美丽的胴体”拿下了少俊、轻而易举地让少俊交出了穗子所有的情书、出卖了穗子,在《灰舞鞋》里,对应的是邵冬骏和高爱渝……《芳华》中“我”第一次与刘峰打交道,是同为警戒哨兵,站在靶场最外围,防止老乡误入,却因大意致“误伤”“老太太”的情节,在《穗子物语·奇才》里早就出现过,到了《芳华》这里有了些不同而已。更为奇妙的是,《芳华》的真正女主人公,其实应该是何小曼,对应《穗子物语·耗子》里的黄小玫(《灰舞鞋》里也有“耗子”这个人物),两个人物的身世、性情乃至最后的发疯,都可以作个比照阅读,同质之外的异质性,可以显出作家历经不同时间所作的艺术构思的差异性。而刘峰的原型,似乎便是《耗子》这个短篇小说里的池学春,刘峰的触碰事件以及所遭受的批判大会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众生相,都可以从池学春及其所曾遭遇、乃至穗子谈纸上恋爱被开批判会那里找到原型。当然,一个短篇,体量有限,难以容纳更充分的人物刻画、世态人心和淋漓尽致的人性书写。《耗子》以及《穗子物语》所不能够呈现和达致的,《芳华》能够竭尽所能给予最为充分的展示——文学书写,可以向人呈示青春是如何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说《芳华》是严歌苓“致青春”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
这当然是阅读《芳华》,令人备感熟悉、亲切和让人会心的地方,但也正是由于持续关注和研究严歌苓,还是对严歌苓以这样的第一人称叙事和她本人罕有的作家主体融入叙事——作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难免产生无法分离的混合性——的话语方式(尤其为她的“中国叙事”作品所罕有),为她这样的叙事方式、策略,感到有一点意外,甚至为她捏一把汗。众所周知,严歌苓一直致力于、近年来尤擅小说技巧层面的探索,陈晓明都称她的小说“技巧性很强”。即便是那部有震动效应,在陈晓明看来“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小说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认识所发生某种变化,也可以看到中国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不断伸展的特点”的《陆犯焉识》,陈晓明也特地强调了小说在叙事和叙述上的技巧性:“严歌苓是懂得现代小说的。如果先花花公子玩一通,再抓去坐牢,用线性叙述,这个小说就散掉了,完全没有价值。”阅读和研究都不难发现,在近年来的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当中,作家往往着意于对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探索,他们往往是最能够接近西方现代小说经验并有可能化用得最好的作家群体。尤其是严歌苓,令人叹佩的写作高产之余,也不断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孜孜以求。我曾经细致分析过严歌苓《妈阁是座城》在结构、叙事以及由之关涉的对人的情感、人性心理表达的种种暧昧繁富,不仅是这部小说所具有的明显不同于她此前作品的创作新质,而且对于当代小说如何在形式方面,如何在结构叙事等方面获得成熟、圆融的现代小说经验,提供了不无裨益的思考并且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而严歌苓的近作《上海舞男》,小说的叙事结构已远非是“歪拧”可以涵括,小说“套中套”叙事结构的彼此嵌套、绾合,那个原本应该被套在内层的内套的故事,已经不是与外层的叙事结构构成“歪拧”一说,而是翻转腾挪被扯出小说叙事结构的内层,自始至终与张蓓蓓和杨东的故事平行发展而又互相嵌套并且深度绾合——还要打个结儿为对方提供情节发展的动力。我甚至曾认为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舞男》是严歌苓截至当时在叙事结构、策略、叙述角度与限制视角上面,最为成功的作品。已经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等方面非常讲究并且具有明显优势的严歌苓,突然好似来了一个大踏步的“回退”,第一人称、个人自传色彩,在四十余年后回望自己的青春与成长期、并写出了文工团员四十余年命运的流转变迁,对于并不从事非虚构写作并且一直以小说的虚构性、文学性为典型创作特征的严歌苓来说,不啻又是一种小说叙事的新探索(当然是就近十几年严歌苓“中国叙事”的小说所作的讨论,2001年初版的《无出路咖啡馆》,虽然自传的色彩很强,因是海外华人生活故事,暂不在讨论之列)。小说的叙述视角、话语调适,尤其是小说的虚构性、文学性所会遭遇的局囿和困难以及小说如何还能够葆有丰赡的虚构性和文学性,都将是一个难题和小小的挑战。
一 、作家主体融入叙事与青春记忆复现
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凡是作家主体较多融入叙事的小说,往往有散文化和抒情性的特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郁达夫,在他从《银灰色的死》到《出奔》五十篇左右的小说中,属于自叙传小说的有近四十篇。其小说有一些直接以第一人称“我”叙事的模式,其它则是以第三人称“他——叙事”的叙事方式来结构成篇,其小说主人公无论以什么样的身份出场,都熔铸了作家太多的主体形象和心理体验。作家主体过多地融入小说叙事,对小说形式的伤害是明显和严重的,易使小说呈现散文化的典型特征。散文求真,不提倡虚构故事情节,散文多是抒情和记事,近期还有不少研究者和评论者对散文虚构故事情节表达了他们的愤愤不平之气,也说明了散文很少虚构故事。而小说是典型的虚构叙事文本(非虚构作品不在此讨论之列),对虚构性、情节性和可读性有着较强的要求,小说求真求的是艺术的真实。所以有研究者曾经从形式层面这样批评郁达夫:“小说则需要虚构,如果一个小说文本缺乏虚构则会近于散文,情节性也会几乎丧失,阅读的快感也会弱得多,郁达夫的小说则是这种情况。从形式上看,他的叙述人与人物角色几乎没有距离,距离感的丧失正是缺乏虚构意识的结果,而且感情毫无节制,成为启蒙之初个人欲望的泛滥。距离的丧失也导致了叙事视点转换的稀少,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极端向内转,其实是与个人经验直接相联系,缺乏虚构性的同时也丧失了叙事的丰富性,最终失去意义层面的丰富性。”
还有一个相反地、比较成功的例子,是萧红,她后期作品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等,虽然也是“内观”的“自传体”型作品,但却同时也是她最成功、最感人的作品。以其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为例,夏志清曾经给萧红《呼兰河传》这样的“最高评价”:“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散文化、诗化、抒情性,是它的典型特征,“这书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典型的小说,它大部分牵涉个人私事,叙述性强,但书中却有着像诗样美的辞章,以及扣人心弦的情节”,这句话难免矛盾和吊诡之处,“不能算是典型的小说”、诗化、抒情性,葛浩文的判断是准确的,但他同时又说它“叙述性强”。是什么给他《呼兰河传》叙述性强的印象的呢?原因就在于萧红非常恰当地将“我”在小说中出现的比例控制到了较小的份额——只占较少的章节,而且很多时候,是取其非成人视角的限制性叙事,达到了很好的叙事效果,避免了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人的一种高度混合性和过于全知叙事对于小说艺术真实感的伤害。与《呼兰河传》的非成人视角的限制性叙事相较,对此限制性叙事方式颇显示出一种呼应和长足发展的,是严歌苓的《穗子物语》系列小说。《呼兰河传》哪怕是作成人视角的叙事,也是取人物视角的限制性叙事——“我的人物比我高”(萧红),比如对小团圆媳妇婆婆的描写,等等,方才能够在叙事方面,克服郁达夫那种叙述人和小说人物几乎没有距离的弊病,令小说产生足够的艺术真实性和可读性。
同样存在着小说散文化倾向的迟子建,被有的研究者认为,其有的小说文本是“作者”无所不在地介入到写作中,“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小说中的人物确实存在着无法分离的混合性。即便如此,《额尔古纳河右岸》《晚安玫瑰》等小说,虽然用了第一人称“我”叙事,但“我”显然不是作者本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距离,作家主体与人物和小说叙事之间的距离。而具有先锋精神的作家以“我”作为主要叙述人,不鲜见。其中较成功者比如北村《安慰书》的隐含作者是把第一人称“我”(律师石原)而不是第三人称叙述者置于叙事层次等级结构中最高层次的那一个层级,由“我”的过去和现在所关涉到的所有人,都在我寻求证据、寻求证人、探寻历史旧案真相的过程中,与“我”打交道、发生关联,让不同的人物重复叙述、追忆同一个事件,产生悬疑推理,剥洋葱般一层一层剥开,最终让真相浮出水面。小说中的“我”不是作者本人,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是为呈现一个类似悬疑推理小说一样的叙事效果。就是严歌苓本人,在上一个长篇《上海舞男》中,有时以第一人称“我”(石乃瑛)来叙事,这个“我”也绝非严歌苓本人,可以说与作家本人有着天壤的距离。到了《芳华》,所用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尤其那段文工团经历中的“我”,几乎就能够等同于严歌苓本人,至少是有着高度的混合性、不可分离性。要知道,在几乎可以算作《芳华》奠基之作的《穗子物语》中,严歌苓也绝少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她《穗子物语》的成功,恰恰在于:“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芳华》一反常态,用第一人称“我”来叙事,不止符合严歌苓真实的人生经历。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是小说叙事的需要。我们知道,严歌苓的长篇总有一个“故事核”,陈晓明说她:“严歌苓有一点很独特,就是她的小说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故事核。”与她此前的那些小说不同,如果非要给《芳华》概括一个“故事核”,这个“故事核”似乎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部队文工团,一个言行近乎雷锋的男团员,因为情之所至而触碰了一个女团员,导致了命运的改变和悲凉结局……为什么用省略号呢?因为这个概括太不全面。第一,尽管考虑了时代性,“触碰”也并非像《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之故事核那样,并不是一个能够带来足够的悬念、惊奇和离奇情节的事件、故事之核。第二,正如小说名字“芳华”,小说不具备严歌苓先前小说当中那样高度聚焦的人物,它更加能够示人的是对一群人、一段历史及人物命运流转变迁的感怀,青春记忆、人性书写令小说呈现繁富的调性,小说的素材和写作对象,似乎先就命定了小说势必具有一种抒情性和略带散文化的文体特征。及至笔者写作此文,《芳华》业已出版,严歌苓与我的私人通信中还称:“我的新书‘芳华’或者‘你触碰了我’刚上市”——她不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定的名字就是《芳华》(原名《你触摸了我》),而冯小刚拍电影,名字选中的就是《芳华》:“‘芳’是芬芳、气味,‘华’是缤纷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冯小刚的选择,更加基于自己对于那段记忆的印象,《芳华》中当然不都是美好的气息和美的印象,但他还是准确把握到了小说最大的价值之一,便是青春记忆与气息的呈现和复现。据说冯小刚在拍摄电影时,尤为重视了刘峰和何小曼所经历的战争场面的渲染和拍摄,耗费巨资。据说:2017年3月7日,冯小刚在拍摄间隙发了剧照,纪念一场战争戏拍摄完成,他发文称:“从打响第一枪到结束战斗六分钟一个长镜头下来,每个环节不能出任何问题,炸点,演员表演,走位,摄影师的运动,上天入地,都要极其精准,六分钟700万人民币创造战争新视觉。相比集结号的战争效果其创意和技术含量都全面升级。《芳华》不仅是唱歌跳舞也有战争的残酷和勇敢的牺牲。”言语间十分自豪。从中可以见出,电影导演尤擅从小说中抓取能够产生最佳视听效果的场面和内容来进行艺术再创作。其实小说所涉战争的描写,实在不足以令电影大肆铺排和着力表现。导演之所以作如是观和为,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芳华》主叙事部分欠缺足够的悬念、惊奇和离奇情节的事件、故事之核,电影竟然要格外着意表现文工团员基本离散之后只是作为个别人物命运变迁背景的战争场面,以补足小说叙事文本所欠缺的悬念、惊奇和离奇。据此似乎也可以推测,改编后的电影剧本《芳华》,应该与原著小说文本有着很大的不同。
尤擅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严歌苓,当然不会像巴金写作《憩园》那样,还要日后日本研究者乃至陈晓明教授,苦苦讨论他的小说叙事结构到底有没有“平板之嫌”还是“歪拧”出了足够的价值。但第一人称叙事和作家主体较多融入叙事,的确考验她在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的智慧。首先,要压缩“我”在小说叙事中出现的频次和所占的份额,这其实是限制处于叙事最高层级的“我”的权力,也就是要取一种限制性叙事的叙事效果。其次,既然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不可避免“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细察《芳华》就会发现,严歌苓是两种眼光和视角都具有的,但尤其以“我”当年当时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运用尤多和运用得尤其得心应手,还自如化用事件发生时和当时其他人物的视角。这种限制性叙事的态度,最容易凸显现场感、艺术的真实性。再次,哪怕是带个人自传色彩的小说叙事,也要避免单一的线性叙事的窠臼,但又要努力在每个叙事、故事序列里,保持线性叙事的一致性和可连续性。如果说,每个故事序列是小说内套的一个小的叙事结构,严歌苓的叙述人“我”,就要具备串起连环套的本领才行。为了得心应手非常自如地实现叙事转换,《芳华》一如《上海舞男》那样,全面取消了章节的划分,整篇小说一贯到底——既无章节标题也无章节序号,整篇小说一贯到底,仅在作叙事转换时,以空出一行文字的空白行来处理,读来漫说是小说整个叙事和气势到底是一通到底。也只有章节壁垒的取消,才能够最大程度地气韵贯通、一气呵成、浑然天成。《芳华》小说开篇是三十多年后“我”和刘峰不期相遇在王府井,然后马上倒叙回三十多年前的老红楼生活。以及后来人物的命运变迁,小说结尾,小曼在刘峰的灵堂到处摆满冬青树枝:
冬青铺天盖地,窗子门框都绿叶婆娑。四十年前,我们的红楼四周,栽种的就是冬青,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冬青,无论冬夏,无论旱涝,绿叶子永远肥绿,像一层不掉的绿膘。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他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一直骑到红楼下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四月七号,成都有雾——她记得。(215页)
小说所叙文工团的生活,基本按线性叙事,但又不断旁逸出林丁丁、何小曼等的叙事,上一个叙事里,往往会为下一个叙事乃至很久以后的叙事和故事序列,埋下伏笔,有时候这个伏笔只有一句或者一小段,例如:“家境既优越又被父母死宠的女兵有时候需要多一些人见证她的优越家境和父母宠爱,我和何小曼就是被邀请了去见证的”(15页),已经首次出现了“何小曼”的名字,但仅此一笔带过;在叙述林丁丁故事的时候,插入一笔“连何小曼都有人追求”,简要叙述了她与排长的感情和她被文工团处理后的一些情节(37—39页);然后突然空白一行、来了一个叙事转换“啊,我扯远了。还不到何小曼正式出场的时候”,“回到林丁丁的故事中来”(39页);何小曼真正的出场,是以“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曼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开启(62—143页)。整个小说叙事,内部倒叙运用自如,错时的故事序列要辗转腾挪,打破单一线性叙事的沉闷。比如,是“我”看到刘峰要给要结婚的炊事班马班长打一对儿沙发(34-35页),然后内部倒叙接续了林丁丁有两个追求者的叙事(35-37页),又内部倒叙甚至预叙了“还不到何小曼正式出场的时候”的何小曼的叙事(37-39页),虽说是“回到林丁丁的故事中来”、刘峰已经来邀约林丁丁去看他打的沙发了(40页),却又旁逸出郝淑雯的情感叙事(39—42页),然后才较为完整回顾性叙述了刘峰“触碰”林丁丁事件始末以及所遭受的批判会和处理(42—60页)……而不同的故事序列竟然还要穿插和无缝连接、拼接——令人不禁莞尔,严歌苓要在心里乃至纸上,做好怎样的盘算,才可以不搭错情节和叙事的线索和关节。而这也正是小说家叙事的巧心和用心之处。
能够复现出如此打动人心的青春记忆,与小说所呈现的作家心灵的真实密切相关,这是单纯的技巧无法带来的。2016年4月,严歌苓完成新作《芳华》的初稿,2016年11月完成于柏林定稿——小说结尾落款“定稿于柏林 2016年11月6日”。那时书名还叫《你触摸了我》,“所有的心理体验都是非常诚实的,这本书应该说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比如:
短短一小时的自由,我们得紧张地消费。阴暗角落偷个吻,交换一两页情书,借一帮一一对红调调情,到心仪的但尚未挑明的恋人房里去泡一会儿,以互相帮助的名义揉揉据说扭伤的腰或腿……那一小时的自由真是甘甜啊,真是滋补啊,及至后来游逛了大半个世界拥有着广阔自由的我仍为三十多年前的一小时自由垂涎。(19页)
心灵的真实方才有可能导向艺术的真实。这样的心灵真实,是属于严歌苓的,也是属于文工团员们的,甚至是属于时代和那代人的。青春记忆的生动复现,得益于虚构的故事是建立在无比真实细致生动的细节之上,像萧穗子的刘峰的第一印象: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练功鞋都现成。他榔头敲完,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几榔头,才站起身。(6页)
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能有如许生动传神的细节化叙述,殊为难得。小说中唾手可得大量的这样的细节叙述,就不赘述和举例了。严歌苓说,“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细节全是真实的,哪里是排练厅、哪里是练功房,我脑子马上能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这是非常自然的写作。” 而且,“她觉得关于中国的故事,当在海外反复咀嚼、反复回顾后,比亲临事件后就立即动笔写,会处理得更厚重、扎实。”这也正是我在对《穗子物语》和《芳华》比较阅读后的阅读感受,《穗子物语》在非成人视角叙事方面拥有格外的优长和优势,而且可以力避第一人称“我”叙事的局限性。但《芳华》能够在第一人称叙事和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具有难以分离的混合性这样的容易削减小说虚构性和文学性压力中,依然很好地葆有小说的虚构性和文学性,不能不归功于作家的匠心和巧心。
二 、叙述视角、话语调适与小说虚构性
严歌苓《芳华》的写作,与非虚构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和追求一种“真实信念”(客观的真实而非艺术真实)不同,“非虚构写作”作为中国文坛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创作热潮,“它以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在直面现实或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创作主体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反思性等叙事特征,折射了当代作家试图重建‘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芳华》是建立在作家真实心理体验和诚实写作态度基础上的虚构叙事的小说文本。前面已经述及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带个人自传色彩,对于小说叙事、小说虚构性和文学性所会带来的压力和难题。严歌苓能够解决和克服这些难题,得益于她在叙事结构、叙事策略等方面的细思和巧妙处理。由于写作上的高产,很多人揣测严歌苓写作纯粹是一种技巧性写作,甚至是西方创意写作的产物,“写得太快”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评价,连严歌苓本人也感到了压力,“敬泽嘱我写得慢一点,你看我还是写得太快!尽管还穿插着影视创作。我不知道国内作家六七年写一本书是怎么写的,大概各种应酬会议太多吧?”我曾经专门关注和探讨过严歌苓出国后所受的西方写作训练对她写作的助益,中国文坛和研究者中,不乏人对技巧持不屑和贬抑态度,这当然与中国文学传统大有关联。但我们越来越备感焦虑的却是,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不是对小说写作技巧过于讲究了,而是还不够讲究、太不讲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开始的一段先锋文学思潮,又把形式追求推向了一种片面的极致,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得也带来失,先锋作家转型或者说“续航”(吴俊语),并没有在形式和技巧方面取得足够令人欣慰的佳绩。以致近年来,有识学者批评家像陈晓明等人不免忧虑还未获得现代形式的中国当代小说,该如何对待传统、创新和现代小说经验的问题。有研究者在张爱玲所受的褒贬不一的评价中,曾经指出张爱玲的写作:“那是一种少有人可比拟的生活智慧和情感体验,与其对生活的天才感悟和文学语言天赋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张爱玲体。其实如果从形式分析入手,的确会发现张爱玲过人的文学才华,这种才华,正是文学性的重要表现。”天才的作家,往往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张爱玲有张爱玲体,严歌苓也有严歌苓体。严歌苓在近乎无可比拟的生活智慧和情感体验以及对生活的天才感悟、很好的文学语言天赋方面,也让人称道、与有会心。当然,也必须从形式分析入手,才能够看出《芳华》的文学性。
1接下去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外面等噩耗。2一会儿,刘峰站累了,蹲下来,扬起脸问我:“十几?”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十三”。3他不再说话,我发现他后领口补了个长条补丁,针脚细得完全看不见。4棉门帘终于打开,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5我和刘峰对视一眼,是认尸吗?!6刘峰哆嗦着问子弹打哪儿了。7医生说哪儿也没打着,花了半小时给老太太检查身体,身体棒着呢,连打蛔虫的药都没吃过,更别说阿司匹林了!可能饿晕的,要不就是听了枪声吓晕的。(8—9页)(序号为笔者所加)
第1与2句,是混合了全知叙述和刘峰与我的直接引语、视点的叙述,第3句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第4句可以说是全知叙述,也可以说是刘峰和“我”的视角。第5、6、7句,都是取消了直接引语标志的自由间接引语,它不仅可以将数次叙事视点的转换巧妙隐藏起来,而且所产生的效果,是形成走得比较快的叙事节奏,与受述人可以形成一种了无间距、彼此无隔的叙事效果。这与严歌苓喜欢用最最独特的动词,“使文章变得非常有活力的、非常有动作的、非常往前走的”,形成“走得比较快的”叙事节奏,也是一致的。是严歌苓一贯习用的叙事方式,也可以说已经差不多形成一种严歌苓体。
除了这些严歌苓惯有的叙事技巧,《芳华》中还有为数不少西摩·查特曼所说的那种“对话语的议论”,这是以前尤擅隐身于小说叙事当中的严歌苓所不太采用的小说叙事方式,我将其视为严歌苓为葆有小说虚构性所作的一种“话语调适”。这种有叙述者针对话语所作的议论,几个世纪以前就非常普遍。罗伯特·阿特尔曾指出《堂吉诃德》中就有此详尽老练的议论,而查特曼认为还有更早的例子。严歌苓在《芳华》中将古老的叙事手法,作了巧妙的当代化用。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转述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或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那不是我说的话!”他们的抗议应该成立,明明是我编造的话,一放进引号人家就要负责了。所以我现在写到这段的时刻,把刘峰的话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地放到一对儿引号之间。(18页)
这一段,作家好似在努力标示她写的人物的对话,是原话、不是编造的,是对自己的小说叙事展开的议论,但实际产生的效果是,她提到了“人物原型”,她提到了“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地”处理方式,实际上真正的原话是不可能存在的,越在小说叙事中这样表白,反而呈现出的是小说的虚构性。果然,后面的小说叙事中,对于容易让读者产生是客观真实还是艺术真实疑问的叙事关节点,严歌苓都格外强调了自己的文学想象,有着对自己叙事和话语的议论——我视之为一种有意的“话语调适”。对于林丁丁最私密处的东西怎么冲破束缚、冲破灯笼裤腿松紧带的封锁线,飞将出去,直达刘峰脚边?严歌苓有一段细节化叙述,叙述人紧接着就说“当然这都是我想象的。我在这方面想象力比较丰富。所以大家说我思想意识不好,也是有道理的”(33页)。对于何小曼和排长因排胆结石而恋,也是细节化叙述,但叙述人马上直陈“当然,这场景是我想象的”(38页)。对于我们为什么“觉得跟刘峰往那方面扯极倒胃口”,“现在事过多年”,“我才把年轻时的那个夏天夜晚大致想明白。现在我试着来推理一下——”(54页)。而对于重要人物何小曼,叙述者这样议论:“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曼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曼。小曼,小曼,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才敲到第二遍,电脑就记住了。反正她叫什么不重要。给她这个名字,是我在设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样的家庭背景会给她取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家庭呢?”(62页)然后开始了整个小说几乎最为主干和也最为动人的关于何小曼一段的叙事,中间仍然有这样的穿插:“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82—83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对于刘峰与小惠在海口的的生活是怎么开始和有过怎样的好时光呢?“于是我想象力起飞了”(165页),严歌苓对此有很生动的文学叙述,这样的文学叙述当然是虚构的,是添加了作家想象力的翅膀才能够具有离地三尺的文学性的(165—173页)。
严歌苓的话语调适,是一种纯粹自觉的叙述,暗里也在启示我们她小说写作的虚构性。正如罗伯特·阿特尔所说:“自觉小说系统性地夸示自己的巧技情况,通过这么做,深入探查看似真实的巧技与真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一部充分自觉的小说中,从头至尾,通过文体、叙事观察点的把握、强加到人物身上的名字与语词、叙述模式、人物的本性及降临到人物身上的事件,存在一种始终如一的效果:传达给我们一种感觉,即这一虚构世界是建构在文学传统与成规之背景上的作者构想。”它是“小说之本体论地位的一种检验”。它“要求我们去关注(小说家)如何创作他的小说,这一创作过程中涉及哪些技术上或理论上的问题”。严歌苓不同往常地向我们展示了她自觉所作这种小说叙事新探索,也同时启示小说的虚构性、文学性,并在虚构性与小说艺术真实性之间,寻觅合理的衔接路径。
三 、枝节胜主干:旁逸斜出的人性书写
《芳华》小说的主叙事,是虽相貌平平却吃苦耐劳,几乎承担了团里所有脏活累活、成了每个人潜意识里的依靠,大家有任何困难都第一个想到要找的人“雷又锋”——刘峰。他获得了“模范标兵”称号,得到了各级表彰和很多的荣誉。在文工团小儿小女们对恋爱乃至性都是偷嘴小猫一样的氛围里,他是矢志不渝地爱上了独唱演员林丁丁,几年漫长的等待、在他真诚表白的时候,遭到了林惊恐的拒绝,而且“触摸”事件竟然扩大化到被大会小会公开批判进而遭到了“处理”。这在周围的人际和氛围里,实在吊诡,强副主任被人戏称“强奸副主任”、可以随意性骚扰般触摸女团员,若干年后知当时郝淑雯可以将美丽的胴体送进少俊的蚊帐、大胆地偷情,可刘峰连情之所至的爱与表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最为惊人和可怕的恐怕是林丁丁“她其实不是被‘触摸’强暴了,而是被刘峰爱她的念头‘强暴’了”(58页),可以说刘峰承受了所有人性的阴暗面和阴暗心理的对待……严歌苓在小说中一直通过话语的调适,也就是对话语的议论,想揭示当年大家对刘峰批判所犯下的罪与悔,以及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可以爱,刘峰就不可以——这背后所隐含的复杂的人性心理。
我从最开始认识刘峰,窥见到他笑得放肆时露出的那一丝无耻、一丝无赖,就下意识地进入了一场不怀好意的长久等待,等待看刘峰的好戏;只要他具有人性就一定会演出好戏来。在深圳郝淑雯豪华豪华空洞的别墅里,我这样认清了自己,也认识了我们——红楼里那群浑浑噩噩的青春男女。我想到一九七七年那个夏天,红楼里的大会小会,我才发现不止我一个人暗暗伺候刘峰漏馅儿,所有人都暗暗地(也许在潜意识里)伺候他露出人性的马脚。一九七七年夏天,“触摸事件”发生了,所有人其实都下意识松了一口气:它可发生了!原来刘峰也这么回事啊!原来他也无非男女呀!有关刘峰人性人格的第二只靴子,总算砰然落地,从此再无悬念,我们大家可以安然回到黑暗里歇息。刘峰不过如此,失望和释然来得那么突兀迅猛,却又那么不出所料。假如触摸发自于另一个人,朱克,或者刘眼镜儿、曾大胜,甚至杨老师、强副主任,都会是另一回事,我们本来也没对他们抱多大指望,本来也没有高看他们,他们本来与我们彼此彼此。(161页)
这是小说《芳华》的主叙事和主要层面的人性书写。但是,有意思的是,读过小说,最为打动人心的,又常常是那些在作家小说叙事里不占主叙事层面所展示和呈现的人性书写,枝节胜主干,在作家想要表达的主要维度的人性书写之外,旁逸斜出的那些人性书写,反而有入骨入心髓的力量和力道。查特曼在《叙事与话语》中将叙事交流活动作了如下图示:
叙事文本
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
虽然对叙事交流活动当中一些环节,也有不同意见,比如申丹。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叙事文本所产生的叙事效果,会因受述者和隐含读者(尤其是受述者)的个体差异及其不同的感受与理解而发生不同。《芳华》“触摸事件”带来的最抵达人内心的,更加或许在于刘峰被处理下放后,他在中越战场受了伤,却又故意给发现他的驾驶员指错路,错过了抢救的最佳时机,最终失去了当年触摸过林丁丁的那只手,而那一记触摸,竟然就是他当时二十六岁一生的情史并让他抱了送命的心……后来的海口生活,小惠不愿被刘峰“逼娼为良”,竟然在口角后“小惠鄙夷地看着熟睡的刘峰,将烟头摁在他的假肢上”,连一个执着为娼的女子,都可以欺凌刘峰。小说里其实作家一致试图想努力剖白“触摸事件”背后所蕴含的复杂的人性,但恰恰是众人的人性对刘峰心与身造成伤害,使他宁可在战场上送命,加上后来的一生命运沦落,这些才是最戳痛人心的。这伤害有多重呢?严歌苓还是有所意识的:“对那样一个英雄,我们曾经给了他很多的褒奖和赞美,最后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真正的活人去爱、给她女性的爱。”
刘峰与何小曼是严歌苓着墨最多的人物,严歌苓甚至可以不经意间说出他们原型的名字。何小曼,是与《穗子物语·耗子》中的黄小玫属于同一原型。在严歌苓本意里,何小曼应该是重要性次于刘峰的人物、应该算不得一号人物。但在展开的有关何小曼的故事和叙事中,何小曼的成长史、成长叙事,反而蕴含了小说中极为繁富乃至诡异的人性书写,甚至超过了刘峰故事和叙事里人性书写的力道,这恐怕多少有些是作家没有完全料到的,就像她在对话语作出议论时所说的,她写何小曼的故事,“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对于何小曼发疯的解读,往往是这样的:另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何小曼,则是因为家庭出身和不幸的童年经历,在团队中饱受欺凌和排挤,最后因为立功而突然获得种种荣誉,却疯了。“这也是有真事的。”严歌苓说,“一生都没有人给过她尊重,(突如其来的)太多的尊重把她给毁了。”但是条捋一下何小曼的成长叙事,就会有更深入的发现,也有着更为繁富复杂的人性书写维度和层面。
拥有母亲却一直是一个事实“缺席”的母亲、一生都缺乏母爱佑护,整个何小曼的成长叙事,就是一部虽然存在但一直“缺席”的母亲对女儿的伤害史。女儿在对母亲不断希望,然后不断失望当中,最终在某个人生的当口,就是那个唯一的不嫌弃她,能够触碰她的身体、她的腰,帮她完成托举动作的刘峰被处理下连队之后,“第二年秋天,何小曼也离开了我们。她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111页),她的下放与唯一不嫌弃、不孤立她的刘峰的下放,其实存在深度的关联性。一直对母亲失望、被所有人孤立当中,刘峰对她的触碰和托举,对于她的价值和意义何其重大:
那天晚上,其实小曼想告诉刘峰,从那次托举,他的两只手掌触碰了她的身体,她的腰,她就一直感激他。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他给她的,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他把她搂抱起来,把她放在肩膀上,这世界上,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109-110页)
只要认真读过何小曼的成长史,就会体会到这一段的意义。《穗子物语·耗子》中黄小玫的父亲并没有死,最后是平反了、官复原职。何小曼的父亲,却是在给她赊了一根油条后自杀了,而父亲为她赊油条、与她最后时刻的相处是这样的:
家门外不远,是个早点铺子,炸油条和烤大饼以及沸腾的豆浆,那丰盛气味在饥荒年代显得格外美,一条小街的人都以嗅觉揩油。一出门小曼就说,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条。四岁的小曼是知道的,父亲对所有人都好说话,何况对她?父女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从感情上到物质上她都可以敲诈父亲一笔。然而这天父亲身上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没有。他跟早点铺掌柜说,赊一根油条给孩子吃吧,一会儿就把钱送来。爸爸蹲在女儿面前,享受着女儿的咀嚼,吞咽,声音动作都大了点,胃口真好,也替父亲解馋了。吃完,父亲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绢替女儿擦嘴,擦手;于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替她擦。擦一根手指,父女俩就对视着笑一下。那是小曼记得的父亲的最后容貌。(63-64页)
这样的父女温情,在小曼“拖油瓶”的成长史和部队文工团的日子里,再也没有遇到过,直到刘峰在舞蹈动作中所作对她的托举和触碰,抚慰了她多年以来作为失去父亲的爱的受伤者的疼痛。刘峰表白林丁丁时情不自禁触碰林,收获的是批判和处理,舞蹈中刘峰对何小曼的触碰,却让小曼再度重温了失去多年的父亲所曾经给予过她的温情——这是多么吊诡、悖谬并且让人感到无言的心痛。而且,紧随这段父女温情的书写,作家继续在一种似乎不经意的笔调中写出了当年在那天唯一爱她的父亲的自杀,“何小曼不记得父亲的死,只记得那天她是幼儿园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于是父亲的自杀在她印象里就是幼儿园的一圈空椅子和渐渐黑下来的天色,以及在午睡室里睡的那一夜,还有老师困倦的手在她背上拍哄”(64-65页)。不动声色的文字背后,令人隐痛入心。她作为“拖油瓶”跟着母亲改嫁了,“母亲都寄人篱下了,拖油瓶更要识相”(68页)。吃破皮饺子、被继父吓病才得了母亲最后一次的紧紧拥抱。十年后,她在江南三月的夜里,泡了一个小时的冷水浴,就是为的生病,作家没有明示,但字里行间都是她对得到母亲拥抱的渴望……这样的家庭环境,五岁的弟弟都可以宣布拖油瓶姐姐是天底下最讨厌的人:
她深知自己有许多讨厌的习惯,比如只要厨房没人就拿吃的,动作比贼还快,没吃的挖一勺白糖或一勺猪油塞进嘴里也好。有时母亲给她夹一块红烧肉,她会马上将它杵到碗底,用米饭盖住,等大家吃完离开,她再把肉挖出来一点点地啃。在人前吃那块肉似乎不安全,也不如人后吃着香,完全放松吃相。保姆说小曼就像她村里的狗,找到一块骨头不易,舍不得一下啃了,怕别的狗跟它抢,就挖个坑把骨头埋起来,往上撒泡尿,谁也不跟它抢的时候再刨出来,笃笃定定地啃。(72页)
一个生活在上海的条件不错家庭(继父是厅长)的何小曼,缘何有这样村里的狗的习性?从日常母亲对她的每一分对待、从“红毛衣”事件,从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把她推向了不得不如此的生活境地。她把这些习惯带到了部队里,并且受尽嫌恶,饶是如此,她把临参军时母亲给她梳的法国辫子,生生保持了两周:“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间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头发打了死结”,她只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87-88页)。为了葆有一点“母爱的痕迹”,她付出了毁伤自己头发的代价——头发打了死结,剪掉死结后,是“刘胡兰头”乃至近狮身人面像的丑相。殊不知,这止是何小曼渴望母爱而不得、想望母爱却总是收获意外乃至伤害的一个小小隐喻而已。女兵们有父母输送来的五湖四海的零食,很少有人请何小曼分享,“小曼之所以把馒头掰成小块儿,用纸包起来,一点点地吃,是因为那样她就也有零食吃了”(134页)。她对母亲和母爱一次次的期盼,盼来的是“盐津枣”,而两分钱一袋、不雅别号叫“鼻屎”的“盐津枣”(这个情节《穗子物语·耗子》中也出现过,不过没有《芳华》当中这样让人寒心),竟然是母亲让她帮忙黑市交易、粮票换菜油的“报酬”。“小曼是不会哭的,有人疼的女孩子才会哭。”“她合上演讲稿,也合上一九七七年那个春天。”“二十多岁做孤儿,有点儿嫌晚,不过到底是做上了,感觉真好,有选择地做个孤儿,比没选择地做拖油瓶要好得多。”“歌里的儿子不会懂得世上还有小曼这样的女儿,因为他无法想象世上会有她这样的母亲。”“‘剪断’最不麻烦,是更好的持续,父亲不也是选择剪断?剪断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136-139页)何小曼的成长叙事,可以说是《芳华》中最为能够碰触人的心灵和灵魂深处的人性书写,本来是世界上万世皆休都能够令人一息尚存的母爱,在何小曼的成长史中,一直缺席乃至病态发生着。加上给了她在小时候父亲自杀后唯一的触碰和托举的刘峰下放后令她更加断绝对人世的希望,尤其是不断升级的对母亲和母爱的彻底绝望,何小曼疯了。何小曼的发疯,就是她对母亲和尘世的“剪断”。后来她终于能够康复出院,成了陪伴刘峰走过最后一段人生旅程的人。她和他是生活之伴,却没有成男女之侣。两人之间,作家所作的留白,足令人怅惘和叹息。
严歌苓从《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田苏菲与母亲关系等的描写,就揭示了女性成长叙事里母亲的问题,在《妈阁是座城》中对并不理想的母亲,也有少量涉及和描写。《穗子物语·耗子》中黄小玫的母亲,还不失一个母亲所能够给予儿女的温情与爱。到了《芳华》里何小曼的母亲,她对于小曼这个“拖油瓶”女儿,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缺席”的母亲。何小曼的成长史,在《芳华》主叙事里,说它是枝干也不为过,但就是这枝干,所旁逸斜出的人性书写,反而达到了最深刻和让人痛心的力道。这可能就是严歌苓说的她写何小曼的故事,“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旁逸斜出的人性书写,直抵人的内心深处。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