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瑞华:一种批评的责任意识——关于刘树元《小说的审美本质与历史重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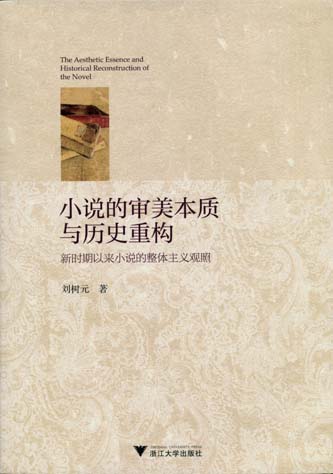
随着网络的普及,人的私化阅读的需求越来越多地得到满足;而此前许久文学的私化写作早已出现,它不断冲击主流的文学,一点一点渗入甚至以独立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马克思早就把人的属性分列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种,其后弗洛伊德又将人的心理层次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而每个层次都有各自的需求;所以不应否定私化阅读的需求,也不应绝对否定私化写作,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公众化的文学空间若被过多的私化内容充斥,社会化行为被编造得全由私欲所支配,无异于扼杀阅读者被真与善、美统一体感动的需求、推倒阅读者向崇高的阶梯。《小说的审美本质与历史重构》这本著作里对公众化文学有着深切的忧患与责任意识。
书的开端是对“文学的整体性”的理论阐释,刘树元教授以大量文学家如高尔基、鲁迅、海明威、莫言、罗伯-格里耶等实例为支撑,并调动了从《文赋》《文心雕龙》到茅盾的文论,从托马斯·曼、果戈理到米兰·昆德拉,从阿瑞提、皮亚杰到马斯洛,从朗吉纳斯、康德到朱光潜,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卢卡奇等繁复的文学、心理学、美学理论储备,表达了有关文学的整体观的多重含义;各种文学批评的方法,有的看似针锋相对,刘树元教授认为未尝不可以互补兼收,可以理解为批评无定法。
批评方法的兼容并包当然不意味着放弃对文学的评判与期望。在对新时期以来各派各家小说精神面貌的全面把握基础之上,刘树元教授在文学批评中显示出鲜明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由“艺术的真诚无伪之心”而上升至“庄严的叙述”。
艺术创作应秉承真诚无伪之心,才能发现与展示世界之真。被称为“弗洛伊德之后最伟大的精神生活的探索者”的加斯东·巴什拉尔认为“有一种在其自身泯灭一切个人思想之痕迹的客观意识”。文学中的客观意识可以成为个体体验的承载,可以是人的一种顾影自怜,创作者在日常中的心理郁积无法疏通的情况下找到文字与文学这条通道,写作的过程从而具有宣泄与治疗功效。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称《周易》《春秋》《离骚》《兵法》《国语》《吕览》《说难》《孤愤》以及《诗》等文学的写作莫不因“此人皆意有所郁结”,司马迁的《史记》、孟郊的“苦吟”、李贺的怪异之诗、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同样堪称文学创作以释怀的明证。该现象还可证之于杜拉斯的写作体会:“身处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当某种情感压迫得人处于寝食难安的地步时,每个人都有一种诉说的冲动。哪怕是抒发出社会关怀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创作,也具有自我解压性质。情感的现实挫折会催生文学创作,文学则成为心理失衡与缺失感的暂时寄托与补偿的一种艺术化的途径。
文学中的客观意识肯定可以超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治疗”需求、超越个体的生命体验的直接书写,带有更广阔的关怀意识。巴什拉尔的说法听起来玄秘,刘树元教授说得比较具体:“应对人类的精神处境和生存处境给予关怀,并为解脱人类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与热情,要以自己特有的话语形式显示对人性的向往与关注”,而关键是克服“主体意志薄弱”问题。
创作主体意志薄弱,会变得急功近利,或迎合某些褊狭规则随意编造,或趋附某些低俗口味大肆渲染人世的私欲。在其批评中,刘树元教授表明了对叙事作品中违背文学创作的自有规律而张扬非理性化之力的质疑。
文学创作不为追逐名利,首先是对创作者理性克制力与文学理智化的要求。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都意味着,文学的象征形式虽然是以作者强烈的情感感受为基础的,落实到作品中却又需要经过理性的节制和过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诗派”与“京派小说”都是注重理性节制情感的典型。文学本应具有区别于本能欲求的真诚与崇高特质。
在曹禺的《雷雨》中,与后母恋爱过的周萍为了摆脱道德乱伦的压抑,抓住了女佣四凤,不料后来方知四凤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最终他自杀了,四凤也再无法面对任何人。类似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结局。这说明一个问题,欲望固然与人同来,但人同样有追求社会化尊严的能动力,哪怕是在家人面前。马克思、弗洛伊德都肯定了人的同乎兽的一些属性,另一方面可见不能脱离社会去阐释人。刘树元教授“庄严的叙述”的说法,包含了对群体、社会的责任意识。
叙述如何变得庄严?这是在理性克制力基础上更高一步的要求,但不尽同于韩愈的“不平则鸣”,刘树元教授强调了“底层关怀”,认为“文学精神是文学的灵魂……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更需要深厚的人道精神的支撑……”呼吁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道德意识、伦理意识等良知。
在《小说的审美本质与历史重构》这本书里,文学批评的责任意识不是“我以我心荐轩辕”的慷慨激昂,也不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小心隐忍,而是从生活的实际需求出发的言语。在所有的个我尽兴之外,还有生活中的种种需要满足的期待,尤其是为人父母者,什么时候能忘记弃一己的放纵而去迁就孩子?所以,责任感在这部著作里有着验之生活的朴素。
扎根生活但不溺于生活,这种文学批评的责任意识与心怀虚静的批评素质,也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种表现。其评价韩东城市生活题材作品,“《利用》《烟火》……驻足边缘地带的张望和穿过喧嚣烦乱空间时显出的冷峻”,就显示出超然物上的情怀与诉求。
文学何以堪称人学?什么艺术现象不是人学?甚至可以说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人学——是人为的,是关于人及其周围的,而且是为人的。但是惟有文学,在表达同情这点上直接表现了人是非同寻常之动物。在众多可以促成文学象征的事理当中,有为己为人为强为弱之分。惟有对弱小的同情,是善的,也是美的,是具有最高意义的。用文学作品表达对人的困境的同情,是作家的一种责任;用文学批评强化或建构公众化文学的精神,是批评家的一种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