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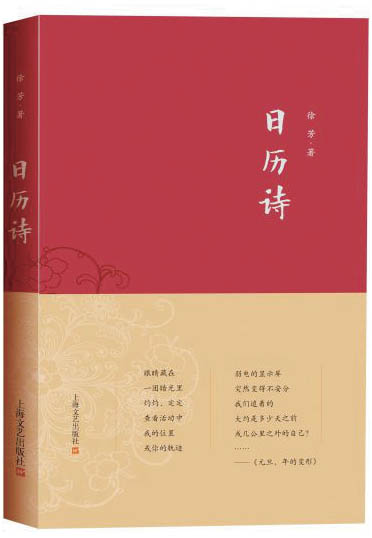
我尝试过各种文体写作,但我不写诗。年轻时读过大量的诗,也整本整本地抄过古今中外许多大诗人的诗。但我从不写诗。诗,是我最为敬畏的文体,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古人说,诗缘情而绮靡。西方人说,愤怒出诗人。诗,是在感情、人生最为激烈时刻,溅出来的灿烂火花,是一种特别需要感情和才情的文体。
诗人徐芳起步于华东师大丽娃河畔,是华东师大夏雨诗社出色的女诗人,是上世纪80年代优秀的女诗人。她在诗中流露的才华才情,连施蛰存这样才气十足的文学大师都禁不住喝彩,说她的诗“正站在她手帕的边缘上,要回她的青春”,鼓励她继续去追,去追回诗的青春。我想,徐芳是一直牢记着施先生的这些话的,直到今天。但是她当年的花手帕已经丢失了。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灰色而浑浊,喧嚣还有点无聊。很难说,这是抑或不是一个诗的年代。
徐芳的《日历诗》是对诗既定的文体性的挑战。在那些感情并不如火的寻常而略有涟漪的时日里,在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里,创造出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诗,是对青春的诗性的中年回声,是对“逝者如斯夫”的连绵不断的时间的回应。于是高贵的诗有了世俗的气息,有了与芸芸众生相同的人间烟火的气息。
时间,流过,在日常凡俗的生活流过,在灰尘般细碎的细节中流过,在我们经常空无的思想里流过。徐芳试图用诗的触角抓住那些“流过”,用诗的语言把“流过”像琥珀一样晶莹剔透地凝固起来。
禅宗说,我心即佛。徐芳是“我心即诗”,在传单一样撒落的每一张日历中,在生活的流水账里,寻觅诗意。流水无意,落花有情。于是,几乎类同的每一天肌理深处就有了诗的意味,散发出了诗的淡淡的芳香。“时间在蒸锅里打个滚/馒头已熟香”。韵味、香味,一起扑面而来,缭绕在你的心头。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的形象和江南的意象,在一张日历里折叠在了一起。于是,我接触多年、稔熟在心的越剧名角就这样有了诗的意象。漫长焦灼、反复咏叹地“想你、想你”声中,最后,想到的是黄梅季节期待的一个“大晴天”——“一个过长延迟的/太阳的蒙太奇”。青春时代对爱情的焦灼渴望和热情,变成了如此日常的对天气的等待,变成了每一个江南人共同心理的诗化吐露。
在《日历诗》里,徐芳把一个天天在都市里忙忙碌碌的母亲触目所见,一一变成了在读者心中跳跃前行的诗行,小到牵牛花开的一个清晨、一碗热汤,大到“5·12汶川大地震”被撕裂的母亲的心、那架永远迷失在茫茫大海深处的MH370缥缈的踪影,还有流传了千百年的节和节气,它们精灵般地如期到来,每每都会在诗人的心头,撩起一股淡淡的云烟般的情愫。诗人徐芳同时把低头所思写在她的日历上,有各种各样的思绪、情绪,随着时间的脚步,集合到她的笔下,滚烫的、冷峻的,浅浅的、深深的。她似乎随手都能把现代都市女性微妙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的瞬间律动捕捉到诗的巢穴里来,生出一个个探头探脑的文字小鸟。
我特别感动于,一个诗人母亲对儿子的一汪深情,仿佛絮叨的字里行间隐含着含蓄而有节制的情感表达。从1月到12月,从今年到明年,岁月更替,徐芳可以这样慢慢地一直在日历上写下去,写出一卷当代的诗的《清明上河图》,把21世纪日常生活的情感细节,白描式地呈献给未来。我有意尽量回避诗句的直接引用,是怕亵渎诗的神圣庄重。任何应用都会割裂诗的美丽。哪怕它写在日历上,写的是最寻常的“过日子”。诗,其实是用心去读的,不是让理性来分析的。
把唠叨,把一碗热汤,把打盹儿,把读报,一朵花、一条小鱼、一次外出旅游,一辆疾驰而过的地铁列车,把所有最日常的东西,点铁成金。在写了几十年诗以后,徐芳继续在路上,在探寻诗的新的路径,让诗能在都市生活的寓所、马路里自由地徘徊。当读到《日历诗》的最后一页,我知道,诗人成功了。她,使高贵的诗的脚步,走进了我们这些无诗的人的生活里了。她使我想起了白居易,但,她不是白居易。
(《日历诗》,徐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