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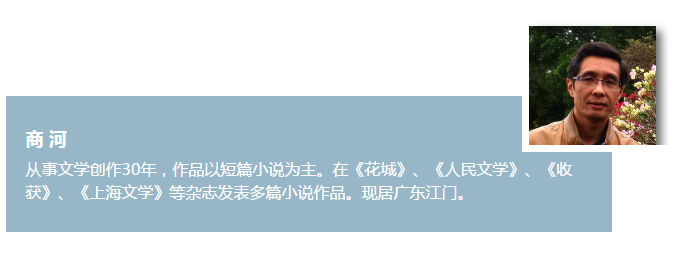
别人的作品不好谈,自己的作品也不好谈。这是私见,亦是源于自况。特别是,《临界》写于四年前,已有一段不短的时间距离。勉强谈,只是想给有兴趣的读者一个可能的参考。
作品形式,如同一个人的外貌,一眼望见:不是传统的,或者说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多年前讲先锋文学,我虽处边缘,仍是这个流绪,亦因处边缘,先锋的精神入心入骨,早与自身个性扭成一堆,再难分解,即与世界,与人事,形成了强烈的紧张关系。个性铸就外貌,内容成就形式,两者一体,虽然随时日流驶,有所改变,终然是细节,如同外貌,无非在脸上打多一道皱纹罢了,还是那个自己。结果或对或错,终归休咎自取。当然多的是错,就是说,他对世界与人事的判断总是由一己的个性和情绪影响、决定的,带着他扭曲的痕迹。因此我一直有个自觉,不敢如那些现实主义者,敢于断言作品表现了现实,而只敢断言所表现的乃是现实在心中的一个自私的烙印。如是,可以粗谈《临界》。
它是心象。肯定在写作时,我正处这样一种状态:在得与失的转折,在存与亡的嬗替,在心境的正常向崩溃蜕变的间隙之间。我得以观照。现实给予了我一次真实的机会,即一个真实的观照的地点,还给我带去一本书的巧合,而记忆则给予我与此心态相契的人和事,几个场景早已涌现,只在乎如何有机地组合。但是它们毕竟组合起来了,其中的内涵,次序,为什么这样排列,现在已很难说得清楚。似乎是不自觉地,又似乎是它更强烈地首先涌现出来,我只是顺乎自然地把第一个场景写成一种幻视,同时也从两个对谈者的角度,客观地审视着在廊下坐着的“他”这个观照者本身;自然,会先有一些引导性或过渡性的描写,它也是各个场景之间的粘合剂,我指的就是那部“他”值班时带去的书,这部曾经作为“他”的圣物、甚至是拯救物的书。从书中引出“临界”的概念,用后来涌现的几个场景作为注释,同时也隐约表达了对这书在描摹“临界”时语言的繁冗和暧昧的不满。因为现实发生的“临界”对于叙事者来说,早已变得更加紧迫和直接了。
场景其实只是三个。通过对话或事件交代它们的时间性。比如,第一个场景是一百年前的人物,第二个场景描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后续故事,第三个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一个场景是由“他”在值班的地点直接唤起的,“他”没有、也不可能参与,或只能想象性地参与其中。而后两个场景则是“他”的亲历,比如第二场景,是由两个游客到来引起的一次会面的记忆,第三场景同样是记忆,也是终结,以对“临界”作出最后的评说。
事实上,对“临界”的评说在前两个场景里已经发生,尤其是第二场景,两个曾经志同道合的人在八十年代末之后分道扬镳,另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既得利益者,满可以用物欲性的临界来对叙事者的“精神临界”进行一番嘲讽,对话以“他”的致命性的反讽结束。当然,这种“致命”对“他”来说才是更致命的,后面“他”有所解释,也作为铺垫引出最后场景。也许,在第三场景,这场最后的对话中,有“他”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批判性倾向以及对“她”的怜悯,但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突出“她”的命运的奇特,以之作为对所谓的“真实临界”的界定,切入一种准宗教的状态,一次从“异境”的回望。但看似是有了界定,而其实并无最终的答案。
因为到底只是“他”的心象。因为现实到底只是搅扰和破坏叙事者心中的确定性。而“他”竟然欢迎搅扰,欢迎破坏,以迎合、组建“他”的心象。使之与那部书的作者一样陷入了同等的暧昧。使亲历事件的作者,我相信包括未参与过事件的读者也一般地陷入了。在这个越益分化和暧昧的时代,这样的叙事对叙事者和读者而言,意义何在,也无答案。结果,作者自己无非在这“心象”的包裹下一味堕入最终的颓唐,以及无法言说的尴尬和沉默。
说到这里,关于这篇小说,已无甚可说。引李商隐诗“只是当时已惘然”,呈作者此刻的心态,可以小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