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伦,生于1994年,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学院,入选剑桥大学2017年社会人类学硕士项目。(资料图片) 21岁从美国休学,回国打工,从东莞、大理、定西到苏州、北京、成都,90后少年孙中伦写下他一个人的“寻路中国”,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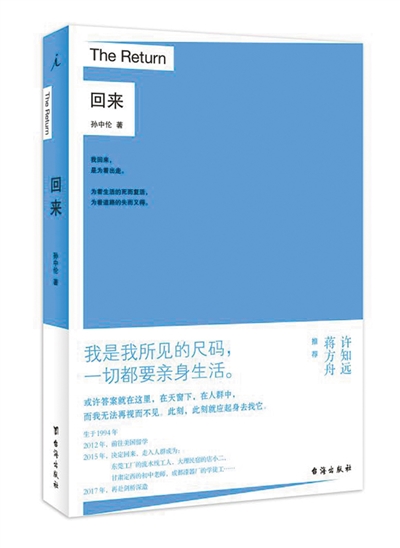
《回来》孙中伦 著理想国·台海出版社2017年6月
2015年夏天,21岁的孙中伦大三结束,他决定中断学业,从美国波莫纳学院休学一年,回中国打工。他去到东莞、大理、定西、苏州、北京、成都,做过流水线工人、民宿招待、初中老师、新媒体编辑、寺庙居士、漆器厂学徒,一边流浪一边工作。
在东莞的流水线上,他追问工人们的生活与理想;在大理的民宿中,他遇见不得志的诗人;在北京的编辑室里,他对青春的痛与梦有了深切的感悟;在成都的漆器厂里,他理解了坚守和匠人的意义;在定西的孩子、父母和老师们中间,他重新认识了生命的真谛、贫穷的代价,以及人与人之间难能可贵的相遇和相知……
除了这一年的经历,他在给未能出生的胞兄的七封信中,写下了一个青年人对生活的困惑、对世界的求知和对自我的质疑。青春的迷茫、张扬和省思,在字里行间娓娓道来。而在给想象中的胞兄的七封回信里,他似乎终于完成了一场与自己、与家人、与世界的短暂和解。
可以说,孙中伦的《回来》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年轻人一路的所见所闻,更是他对外部世界的探寻、对社会历史的思考。比如,在定西当实习老师的时候,孙中伦与他跟随上课的王老师交谈后,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故事是平淡的,只是在叙述了千回百转的人生轨迹后,她重又把它擦干净。这是许多人会做的事,在回忆水涨船高时戛然而止,以便以平静的姿态步入现时。我在独处的时候把它们记下来,仿佛置身事外。在别人的自白里,我从来都是一个他者,一个叙述的幽灵。然而世上真有如读心术般心心相印的叙述吗?我怎能肯定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而非自己的?时常,我怕像《丰饶之海》里的本多一样,在叙述的尽头发现物我两空,一切只存在于臆想,最终都将遁入虚无。”
该书甫经出版,犹如投石荡起层层涟漪,受到社会和学者的很大关注。原因何在?诚如波莫纳学院教授Stephen A. Erickson评价所说:“作为一名充满智性的哲学学习者,中伦深刻地明白,生活的诸多维度都要通过直接的体验才能理解,因此他选择中断学业,投身那些曾经不为他所知的生活环境。他充满思想性的省思,绝对值得我们投入时间和关注。”而作家蒋方舟的看法同样入情入理:“对一位在优质美国高校读人文社会学科,却不满其精英、浮夸风气的中国少年来说,青春期的迷惘和思索十分可贵,为了这种迷惘和探索而勇于休学‘回到’中国这片土地,更是有着珍贵的价值。仅凭此点,他的经历就值得、也应该被阅读。”
当“肤浅”、“不负责任”、“过于自我”等标签被贴在“90后”身上时,这是否为“90后”真实的写照?应该如何从“90后”一直饱受争议的成长历程中去厘清他们的精神追求?孙中伦正是“90后”一代中具有表征意义的代表。他年方23岁,但无论想法和行动,都散发出“90”后身上那种令人欢欣鼓舞的可能性。而这也是本期《读书周刊》愿意关注这个“90后”作者的原因。
据了解,孙中伦生于1994年,本科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学院,主修PPE(政治经济哲学)和德语专业,今年即将继续前往剑桥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的硕士项目。近日,围绕《回来》一书的写作,孙中伦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专访。
我想了解真正的“劳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当你大三结束,考虑休学一年的时候,为何选择一定要回国打工?当时有没想过留在美国,或者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打工呢?
孙中伦:我没有想去国外打工。对我来说,当然劳动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更想了解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因为它跟我的童年,跟我的整个成长历程都息息相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此之前你从来没有过打工的经历?
孙中伦:之前我没有,其实我不希望去体验那种很浪漫的劳动,比如去新西兰打工,甚至半工半游,通过陆陆续续的游览去了解另一种文化。我并不是这么想,我想了解劳动,是真正的日常里的劳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强调“劳动”这个词让我很感惊讶,因为“劳动”似乎在“80后”“90后”乃至更年轻一代的日常语汇里隐匿了。
孙中伦:我觉得也有,只是我们越来越少用劳动这个词。劳动这个词好像已经成为过去式,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劳动者。这很有趣,为什么我们这一辈不太喜欢用劳动这个词,劳动这个概念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太重要,不像以前那么彰显。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如何理解劳动的意义?
孙中伦:以前劳动并不仅仅是跟物质挂钩,还上升为一种时代精神,现在已跟物质回报画等号了,劳动在物质之外的意义被隐没去了,所以说很少人提到。
政治经济哲学教会我提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政治经济哲学的学习能不能帮你解决思想的困惑?
孙中伦: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的,对我来说不是这样一种关系。我本科学的是政治经济哲学,它并不是教我去解决什么问题,得到什么答案,而是教会我一种提问的方式,即可以从怎样的角度去提问。所以,有困惑是再正常不过的。你提了这么多问题,肯定想寻找一个支点去接近那些答案,休学这一年就是我作出的努力。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就是要有行动的支撑。
孙中伦: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但是,每个人选择的方式都不同,我觉得哲学家不是就要在书斋里面,但一辈子在书斋里也未尝不可,拥有广泛的生命体验不是做哲学的必要条件。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比较喜欢哪些哲学家?
孙中伦:这是非常主观的问题,我个人更喜欢读一些外国哲学家的作品,比如康德、尼采、克尔郭凯尔等,因为外国哲学家讨论的问题比较宏大、本质一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本科学习的过程还是愉快的?
孙中伦:当然,学习的时候是比较愉快的,上课的时候是比较苦恼的,读书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我也会把傲慢写下来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休学这个决定,最初得到的支持多么?跟国内外的朋友都交流过想法吗?
孙中伦:我没有跟朋友做过多的交流,主要是跟学校的老师讲到这个事情,也并没有征求过学校里同学的意见,更多是我的长辈一开始会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你为什么不利用寒暑假去做这个事情?或者说,你一定要这个时候做吗?为什么不大学毕业以后才去,先把大学上完了。事实上,后来他们也能理解。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最后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孙中伦: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正是这样一件事,没有什么规划,或者会想到什么后果。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东莞、大理、定西、苏州、北京、成都,这些行程点也都是随意去的?
孙中伦:是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苏州当居士时,你提到最初是要“去探索它世俗化的结果”,“若文学要求我,我甚至愿意扮演魔鬼”。是不是每到一站,对于流水线工人、民宿招待、初中老师、漆器厂学徒这些职业的体验,事先都有过一些过程的想象或判断的预设吗?
孙中伦:对,当然心里会有一些想象,但不会对职业抱有偏见和预设,然后用自己的经历去佐证它,大多时候还是会保持一颗比较开放的心。因为毕竟是要写东西,要写的东西是真实的故事,不是自己先有想象,然后用一个框架去植入故事。但是有些时候,我自认为在比较失败的行程里面,确实是有这样一些预设的情景在,比如我去紫泉寺,我先预设这个寺庙是一个已经被世俗化的佛教视角,但结果里面的僧人都非常虔诚,这就是我一个比较失败的行程。
简言之,我在整个行程中并不是一直维持一颗开放的心,一开始是这样,后来有些时候比较傲慢,但我也会把这些傲慢写下来。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所以,心态一路上还是会比较起伏的?
孙中伦:对,会有起伏,你说得对。
不想作为写作者高高在上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那么,体验的结果与故事的设想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些地方?
孙中伦:我不会有什么设想,我之前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只是体验工种,比如是工人,是服务员,等等。工种是一种标签,像服务员是苦的,定西就是贫穷的,但实际上在这种标签化之下,人生是被影射的。我希望一开始就提供一种对他人生活比较具体的描写,好像你会顺着你父母的生活轨迹一样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一样。他们有名字,有血有肉。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由于生长和受教育环境不同,你面对这些不同的工种及其群体曾经有过某些幽微的心理吗?比如“轻视”、“傲慢”之类?
孙中伦:我没有藐视过什么工种或者某一类人。我希望自己不是这样的,我自己不太喜欢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虽然很多人认为我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情绪在里面。但我是尽量去避免。我不想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显得高高在上。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是一种“平等”的态度?
孙中伦:不能说是平等,平等其实涵盖了一种好像可以去高高在上看别人或者可以仰望别人的意味。我会像对待身边的朋友一样,不去强调一种阶层身份。
他们不希望做“受助者”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当你用脚步和目光丈量城市与乡村的日与夜,用心倾听每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痛苦与幸福时,最终找到的一种具体的精神指引是怎样的?
孙中伦:没有找到精神指引。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至今仍是困惑的?
孙中伦:那是肯定的。怎么可能通过一场旅行就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你可能有一个阶段性的想法,但我并不觉得困惑就消失了或者缩小了。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怎样的位置?这些问题人怎么可能都想得通呢。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广泛意义来讲,你在书中记录的,并不都是光鲜的、欢欣的、鼓舞的见闻,大多是带有一种灰色的、失败了的、让人有点郁闷的色彩。可是当你写完了,与他人分享,其实那些生活如今到头来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你怎样看待这种心情?
孙中伦:那当然了,这是要去面对的问题。你是作者,你有责任要把他们写下来;但你作为一个朋友,你可能会去帮助别人。很多时候我只是强调了写作者的身份,并没有尽好作为朋友的义务。但是,大家不要误解我的书,虽然我描绘了很多贫穷的生活,但我书中描写的很多人都是困境下有尊严的人,他们不会希望做“受助者”,受助的角色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们都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处理自己的困境。所以,我并不希望自己好像要去介入改变他们的生活。
城市化对个体有利有弊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认为当前的城市化发展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孙中伦: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城市化可能比以前更好地解决了贫穷这个问题,或者带来很多工作机会,但同时令身份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前贫富没有悬殊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活得比现在更有尊严一点,现在城市化所带来的那种个体间的财富的差异,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能享受更好的生活。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社会阶级身份在这个环境里被夸大了。简单来说,就是更多的人被排斥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美国波莫纳学院、休学、打工、剑桥大学,这些关键词串成了目前很多人对你的认识。你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发挥多大的力量?
孙中伦:我不知道,我当然希望更多的人读到我的书。我的想法和所有写作者的想法是一样的,希望他人在我的写作中能够被触动,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自己。这种想法是每个写作者都有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接下来你将到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跟这段打工经历有关系吗?
孙中伦: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转到一个更具体的专业,去跟更多人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平时很喜欢文学写作吗?
孙中伦:是的,我也写博客。但我觉得跟真正坚持写作的人有很大的差距,很多人天天写,我可能就一个星期写一篇,最近好久没写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之前对非虚构写作有过怎样的了解?
孙中伦:没什么了解,就读过几本书,我之前对这个概念一直抱持质疑态度,不知道非虚构到底有哪些范式,对我来说,就是写真实的故事。换言之,真实的故事就是非虚构,想象的故事就是小说。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暧昧的边界,比如怎么写,对事实要核实到怎样的程度,这是非虚构的要求,可是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