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松部分作品 《积木书》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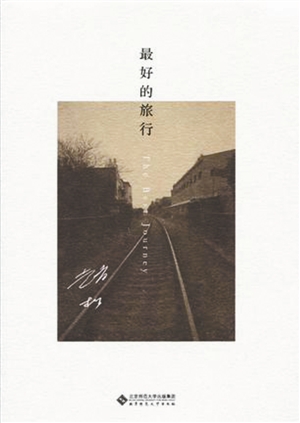
《最好的旅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抚顺故事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3月

《空隙》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5月

“新的文学断然只向少数人开放。”法国小说家罗伯·格里耶颇具煽动性的言辞及丰硕而优异的创作成果,激励着众多写作者在叙述语言和书写形式上不断探索,不断进行着开拓性的实践。赵松就是其中颇为卓异的一员。其2007年出版的小说集《空隙》,2015年出版的《抚顺故事集》,以及今年刚推出的《积木书》,无不展现出独特的形式技巧和语言风格。
《积木书》的部分篇章正以专栏的形式在《晶报·深港副刊》连载。在该书中,作者仿佛注入了一种“恋物癖”般的书写激情,以长镜头兼微观视角的叙述语调,展开对身边世界的诗意描写,充盈着精妙的想象力和思之延展性。除了《积木书》,赵松今年还推出了随笔集《最好的旅行》,日前,记者专访了赵松,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从他的小说传统开始。
晶报记者 欧阳德彬 谭智锋
写《积木书》
受古代笔记体小说影响
晶报:从第一部小说集《空隙》到后来的《抚顺故事集》,你对小说有着怎样的思考?
赵松:我在2013年以前的写作,无论是中短篇还是小长篇,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法,大体上都还算是“中规中矩”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我对于现代小说的各种样式都有过比较深入的了解,但这种“了解”也导致我对于小说这种体裁的认识进入一种相对“规范”的状态。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也确实认为,现代小说经过一百年来的发展在形式上已差不多穷尽了各种可能,很难再有大的创新,要变化,只会是小的变化。
从追求技巧变化的短篇小说集《空隙》到后来刻意做出些传统姿态的《抚顺故事集》(虽然出版于2015年,但实际上主要部分是2006年完成的),表面上看是要往回收的感觉,但其实是在找新的可能性,尤其是整体结构上的可能性。我当时已经清楚的是,局部技术的变化与丰富并不能改变作品的本质,关键还是要看整体结构方式上的变化。
晶报:今年出版的《积木书》似乎有了新的变化,书中每一篇小说都不长,多数篇章也就数百字,为何选择这样的篇幅?
赵松:在2013年至2015年间,我读西方小说少了很多,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古代笔记体小说、包括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研读上。当时刚好有出版社约我编本笔记小说的赏读选本,我花了近一年时间编选出了《细听鬼唱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这个回溯的过程,现在看来还是挺重要的。首先是让我重新认识了古代中国人的那种跟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而且也让我发现了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像废名、孙犁、汪曾祺等人的小说样式与笔记小说的各种微妙的渊源,看到了长期受西方近现代小说影响的中国小说对传统基因进行激活的诸多可能性。
其次是我注意到,在笔记体小说里还有一些比较另类的作品,比如《邢史子臣》(录于据说是战国时人所作的《汲冢琐语》),全文不满五行字,讲的是宋国大臣邢史子臣的三个预言(他自己的死、吴国灭亡、宋景公的死)以及应验,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故事,只是用简约的笔法交待了应验过程,但却强烈地呈现出人对于死亡预言所导致的巨大恐惧,出人意料地营造出极大的想象空间。于是就让我想到了小说叙事空间的构建与生成问题,同时也想到了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之外,是不是还存在着什么可能性?
晶报:因此你开始了“笔记体”的写作?
赵松:笔记小说看多了就会发现,在中国古人那里,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可以写下来,比较自由,也很随机,很多都是片断式的,有很多都并不追求什么叙事的完整性和逻辑的清晰性,有很多读来甚至就像是最简单的素材,但结构上又非常紧凑。然后我就开始尝试写我的“笔记体”小说。当然我不是要像古人那样去写,尽管我也会有意借用、改造一些跳跃、空白、嵌插的手法。我的着重点,是以视觉效果为主体的叙事性营建,主要的方式就是化实有为虚拟,因为我知道文字的间接性特质决定了它无论如何去试图“写实”,最后导致的效果都注定近乎“虚拟”。
晶报:写作这本《积木书》有着怎么样的构想?
赵松:一路这么写下来,大约有几十篇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有数了,因为我能感觉到一个更为庞大的叙事空间的存在。同时我也基本明确了这本书的样式,是介于长篇与短篇集之间的模糊地带的一种样式。并且明确了几个基本原则,一是时间性的缺省,二是空间背景的模糊,三是所有的人物都是无名的,只有人称代词,四是每篇都以省略号开头,以示无始无终的突现与闪去状态,五是没有贯通全书的线索与情节。
如果一定要为这个形式找个对应的东西,那就是梦。这里所呈现的所有篇章都可以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梦中生活的捕捉与呈现,你可以看作是作者的梦,也可以当作是读者的梦。它们是一阵阵出现的,也是一阵阵消失的。我希望能有一种读不完的感觉。
晶报:《积木书》似乎可以从任意一篇开始读,或者可以说像自行搭积木般地阅读?或许一以贯之的文气可以消弭支离破碎感。
赵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确实就像是很多块“积木”,只要你觉得有意思,就可以随意拿起一些篇章,自行搭建出什么,当然你也可以随手推倒它们。我希望的理想阅读状态,确实就是随便翻到哪一篇看都可以。真正起到串接作用的,或许就是文字本身的气息与味道吧。我不敢说在阅读过程中会彻底地消除那种天然存在的支离破碎感,但是,我可能会倾向于把整个阅读过程比喻为对现实世界本来就支离破碎的生活状态的某种感应,而那些所谓的有着碎片特征的篇章应该是始终弥漫着的状态的,这种弥漫,或许又有着天然的整体性。
受契诃夫启发
随手记片断并琢磨其可能性
晶报:在日常生活中,你是不是有随手记录的习惯?
赵松:平时我确实有这样的习惯,经常会把看到的有意思的场景、人物、事件随手记下来。这一点无疑是受契诃夫的札记的启发。所不同的是,契诃夫在记下那些片断的时候,是当作素材来积蓄的。而我在写的过程中就开始琢磨“它们”不是“素材”的可能性,尤其是它们如何获得与之相符的形式感,换个角度说也就是它们的结构方式,它们的存在方式,让它们不再是那种简单的原料状态。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以来的带有实验性质的小说跟近代传统小说的创作机制上的差异性,就是更关注材料本身的生成能力,而不再是材料属性与未来功能上的可能性。
晶报:你在书中写到一位玩微型积木游戏的友人,这位友人在写一本关于如何玩积木的书,献给“某位远方的姑娘,她怕冷,怕风,平时以种花为生。”这看起来是在写你自己,给人一种双重虚构的感觉,又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彩。可以讲讲其中的奥妙吗?
赵松:这篇坦白地讲真的不是我的自况。它的原型取自一位老友,源头是他的一段已然结束了的爱情故事。这篇也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因为它完全地转化了原型,只保留了部分环境细节,其它的都是虚构的。小说是我写的,自然与我的心境也有某种关系,同时也跟原型有某些关系,但它完成后刚好处于我们之间,不属于任何一方了,无论是我来读它,还是我那个朋友来看它,都是能隐约感觉到它来自何处,但同时也知道它就是它而已,这或许就是你所说的双重虚构吧。
如果一定要跟你所说的“理想主义的光彩”搭上边的话,那也是因为原型生活状态里的某种纯粹性的特征,诸多人们习惯的现实利益的考量都被那个朋友或多或少地放下了,正像他惯常的那种离群索居的状态……或许,在这一篇里,我捕捉到了一种微妙的光亮,它不耀眼,甚至也不会引人注目,就像黄昏时或清晨里出现在墙上的一小块光斑,偶尔看到的人,会注视它,直到它被光明或黑暗所吞没。
一个小说家首先也是个读者
晶报:你的写作或许是属于比较小众的那一类,与那些主流的、流行的文字有所不同。你怎样定位自己的写作?
赵松:其实,我真的没办法去考虑自己的写作究竟应该大众还是只能小众这样的问题。我儿子在看过我的书之后,经常会忍不住问我,“爸,你为什么不能写些大家都能看懂的东西呢?”说实话每次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我实在无法想象在写作之前以及过程中去思考谁会读、谁会读懂、谁会喜欢的问题。
如果一定要定位自己的写作,那么我只能说,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通过写作来完成我对自己生命以及这个世界的某种体验与想象,我享受了这个过程,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有读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更新他们的观察、想象的习惯甚至是思维方式,而且,我相信,成立的作品,自会找到它的读者,仅此而已。
晶报:作为一名小说家,你同时也是书评人。在你那里,写书评、写小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赵松:一个小说家首先也是个读者。他的小说写作一定是基于对前辈们的写作成果的认识与感应开始的。我向来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在评论别人的小说作品、尤其是那些经典的小说作品时,不仅仅能暴露出他的小说眼光,还能立即看出他的小说写作处在什么水平上。这一点在实际应用中非常有效。我们甚至可以不去看一个小说家的作品,而只需要看他如何谈论经典小说或别人的小说,就可以知道他的小说水平。
所以这么些年来,我一直坚持写书评,主要是小说作品的书评,这种写作给了我不断加深对于小说认识与理解的过程。也正是在不断评论别人的小说作品过程中,我才更为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小说语言、小说技巧,是只属于“那个作品”的,而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条例,它们只能在非常具体的“那个作品”里生成。同时我也明白了自己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而不会是某种意义上的“声音模仿者”的状态,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之成调、成体,并不断地生长、变化,这是一个小说家必须做好的工作。
希望能让读者
意识到体验的重要性
晶报:在你的书中经常出现“美术馆”“艺术展”之类的背景和事件,这些是否跟你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
赵松:确实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差不多有十来年的时间是工作在美术馆的,经历过很多展览活动,接触过很多艺术家和作品,自己偶尔也会策划些展览,写些艺术评论,也算是个艺术圈里的人吧。这种背景与我的密切关联,我认为是在不知不觉中给我带来很多益处的。比如我对于“视觉”的重视,还有我对于“视觉”在文字中如何转化为另外的东西所做的一些研究,当然也包括前面提过的对于如何构建“叙事空间”的认识,都很有帮助和启发。
当然也让我更为清楚地意识到,视觉艺术与文学,又确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即使有所借鉴也是非常间接的,只可意会的。即使是当下很多艺术家喜欢在二者之间做些跨界的探索,在我看来也是徒劳的,这也正像阿兰·罗伯-格里耶在谈及电影与小说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电影是电影,小说是小说。
晶报:读你的文字,会有一种舒缓、优雅的感觉,也就是说非得脚步慢下来,心静下来,才能领悟其中的精妙。这种安静与缓慢,是否就是你平日里的心境?
赵松:不得不说的是,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好像任何事情都处在快速变化进程中的时代里,似乎快得让人喘口气歇会儿的工夫都难得有。而我认为这实际上也只是当下世界的一种表相,而远远不是全部。因为所谓的“世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永远都是“主观”的存在,我从来不相信存在着“客观”的世界。人生是出生入死的过程,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赶路呢?我匆匆忙忙地要去哪里呢?我匆匆忙忙地要找到什么答案呢?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不论什么人,成功或失败,卓越或平庸,他的一生所能拥有的,除了体验还能有什么?如果非要说我在书中能提供什么的话,那我希望它们能让读到的人意识到体验的重要性,尤其是意识到体验方式的个人化的重要性。
晶报:感觉你是一个活在慢生活里的人。
赵松:有独特的个人体验才会有独特的人生。而独特的体验必须是“缓慢”的,是那种类似于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下来的瞬间的正常速度播放的效果,极快的捕捉结果是极慢的呈现,那种感觉是非常特别的,无法复制的。而作为写作者来说,或者说,作为世界的观察者来说,内心的平静确实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个浮躁的心是无法看清什么的,它只能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情绪所淹没、裹挟。
至于我的现实生活状态,总的来讲属于比较有规律的那种。这种规律其实也是有些被动的。因为我白天要上班工作,晚上才能回家看书写作。时间、精力都是非常有限的,这是我的现实处境,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聚精会神,让自己能够平静地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在那里拥有属于我自己的另一种生活。
寻找为数不多的缝隙,再一次上路
晶报:你在《最好的旅行》后记中谈到,像佩索阿那样,你更喜欢想象中的旅行。现实中有诸多不自由,如何在不自由的世界中自由地旅行呢?
赵松:绝对的自由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只有在想象中才会有绝对的自由状态。世界的丰富性是摆在那里的,天然存在的,与日俱增,与日俱损的,也在不断变化着。但这所有的一切如果你既不能感知、也无法回应,那只能是视而不见的状态了。
在这个无比现实的世界上,每天每时每刻里,消磨人的感知力与想象力的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极为强大的。作为现实世界的“囚徒”,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或许也就是尽可能地保持某种直觉的敏感强度,不去迷恋知识,警惕习惯性思维与感受方式,避免陷入群体性思维的盲目冲动,尽可能地给自己留出一点空间,一点时间,让自己能够保持内心深处的宁静,去倾听,去凝视,去体会,去想象,去造梦……在这些过程中重新发现黎明、黄昏、阳光、露珠、沙子、空气、阳光等等事物,或者概括地说,去发现一个自己的世界。在我心里,真正的旅行是没有地图的。
晶报: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每天都写作吗?
赵松:应该说是一种缓慢的与迅速的交替的写作状态。做不到每天都写,但始终在试图努力做到这一点。实际上现在的阅读欲望比以前减弱了不少,因为想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书在一本本地出来,这意味着它们都已是过去时的了,不再跟我的写作有什么关系了。也意味着我已经把自己清空了。我如释重负,同时又是两手空空。我能做的,就是寻找为数不多的缝隙,让自己能够再一次上路。
晶报:接下来是否有什么写作计划?还会推出哪些新书?
赵松:接下来有几个计划,也意味着面临着抉择,哪个先写,哪个后写。《积木书》完成后,实际上把原有的计划又都颠覆了一部分,因为在小说形式上,有了更多具体的想法。
计划中有本小说,是关于“造假”的。因为造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很多人早已习惯于也更容易被各种假象所吸引,进而沉湎于假象的世界里,并以为是真的,以至于根本不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些聪明人在利用这种状态,推波助澜,假中生假,生生不息,造一个巨大无边的局,他们相信自己完全可以掌控这个局,而多数人都将被变为其中设定好的群众角色,并让他们在虚幻的状态中获得某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感。
说到新书,下半年会出《空隙》的十周年纪念版,当然也是重新修订过的新版。有可能还会出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两本文学评论集,在年底,也可能是明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