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丘彦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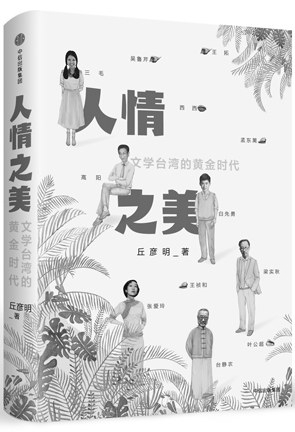
《人情之美》,丘彦明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4800元
“情”是很复杂的人类心理活动。我这本书,写作者与编辑之间的人情之美,但人与人之间关系常常既有美,便会有不美,只要内心存有“情”字在,就会影响生活的轨迹。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政治环境趋于宽松,经济初现起飞端倪,报刊的副刊蓬勃发展。当时,台湾《联合报》邀从美国回来的诗人痖弦出任《联合副刊》“掌门人”,年轻的丘彦明作为编辑,在痖弦的鼓励下,开始与众多华人世界的重要作家打交道(约稿或访问)。他们当中,有年事已高的台静农、梁实秋,也有年过半百的吴鲁芹、高阳,正值壮年的白先勇、三毛,还有隐居美国的张爱玲……这些闪耀华语文坛的名字成为丘彦明编辑生涯中难忘的印记。
若干年后,丘彦明从将近10年写出的文字中选出关于12位作家的采访文章,依据文章的新闻性、篇幅等要素进行增删,加入一些老照片和书信手稿,以《人情之美》为名由台湾的允晨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后来,她与丈夫定居荷兰乡间,养花种菜,画画写作,融入当地的生活和文化,乐在其中。记录这些经历的《浮生悠悠》《荷兰牧歌》等作品先后在中国大陆出版。
时过境迁,如今距《人情之美》首版已有28年,书中所写作家多已作古,但仍然在华语文坛占有重要位置,甚至,有些比从前更加重要。最近,《人情之美》中文简体版也将问世。为此,丘彦明再度对这些文章加以调整、改写。当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年轻编辑,也已年岁渐长。忆及书中这些故人往事,她在“后记”中感叹:“他们大部分写作的高峰期,正是台湾报纸副刊最蓬勃的时代,而我正巧在那段黄金时期担任编辑,与他们展开文学因缘,何其有幸!”
中华读书报:其实很羡慕您的机遇——在台湾报刊业繁盛的年代,接触那么多现当代华语文坛重要的作者,您和他们的交往有友情成分,看您写梁实秋先生那几篇,觉得还有亲情成分。
丘彦明:我觉得编辑和作者之间绝对有缘分深浅的差异。梁实秋先生年岁大了,耳朵重听,逐渐减少与外界的交往。儿女常年不在身边,梁太太韩菁清有时去香港处理事务5至7天,担心梁先生独自在家,因见我常去约稿,便委托我抽空去陪伴他吃饭。常此以久,便产生出亲情般的关系。
我很珍惜和作者之间的特殊情谊,尽量不利用于工作上。尊重作者与其他报刊编辑的交往,尊重作者投稿的选择;站在作者角度,为他设想立场。唯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进退有据的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也才能维护住衍生出来的私人交情。
中华读书报:《人情之美》的文章写于十几二十年前,现在出简体版反而正逢其时,毕竟书中有些人物和他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大陆没有今天流传得这么广,比如张爱玲、西西、白先勇……简体版《人情之美》和当年台湾那版相比有哪些变化?
丘彦明:记得当年书初版时,12位作者有9人健在,现在已有10位去世。原来的作者介绍、一些文章的内容不得不做更改。另外,由于对逝者的思念,在新版中梁实秋、张爱玲、高阳、三毛、孟东篱各卷都增补了新文。如今,书写的作家只剩白先勇先生和西西女士在世。
这27年不单这些作家变化大,我本身也改变极多,先是离开编辑台出国留学,而后结婚定居欧洲。
附录的《从“波丽路”到“明星”》,因岁月变迁的重寻而记录下新印迹。原本书中几篇内容略有重复或过于学术的文章,则修改归并或删除。如此加减增删,新版比原版多了好几万字。
中华读书报:“人情”这个词非常有中国特色。您做编辑时与那些作者间的“人情”,如今看来尤其难得。时代变了,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丘彦明:离开编辑台20多年,我的角色转换成作者。我在两岸的报纸、杂志写专栏文章,在出版社出版书籍。与我接触、联络的编辑,彼此互相信任,写封信问候,寄送书籍。台北的编辑朋友,每次我回台北,必会见面聊天,喝杯咖啡或吃个小馆子。大陆的编辑朋友,我到大陆,能见的则见,不能见的总会通个电话。我感觉,现在的编辑和我当编辑时一样,很照顾作者呀!
中华读书报:追记台北的老咖啡馆那篇《从“波丽路”到“明星”》和整本书的风格有差别,却是互补。看到那些咖啡馆中的往事和人物同样令人唏嘘。今天,越来越少的人在咖啡馆谈文学了,属于文学的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丘彦明:很幸运和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重叠过,但我真不知道属于文学的好时代是否一去不复返?
写《从“波丽路”到“明星”》,把文人在咖啡馆里的活动浓缩,或许会有些误导,提高了那时代咖啡馆的文学地位。其实不论咖啡馆、茶馆、酒吧,本身就是布尔乔亚情调的公共聚会场所,不单作家艺术家爱之,各行各业人士都有可能在这里擦出事业的火花。这些虽不属谈文说艺的氛围,却都是能成就文学的素材。
我查过荷兰的vanDalen大辞典,什么是文学?文学是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留下的总体文字。我很欣赏这广义的文学定义。任何事缩小来看,问题重重;放大而观,海阔天空。文学现象亦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只要有人写人生百态,文学的好时代就不会远去。
中华读书报:您在《人情之美》后记中说,“人一生最怕被‘情’牵绊”,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不是最应该被“情”牵绊吗?
丘彦明:你把我内心错综复杂的情绪给抓出来了。“情”是很复杂的人类心理活动。我这本书,写作者与编辑之间的人情之美,但人与人之间关系常常既有美,便会有不美,只要内心存有“情”字在,就会影响生活的轨迹。正因“情”,让人产生牵挂,从而引发意想不到的故事。活在世上,自己和亲朋好友随时为亲情、人情、爱情而喜怒哀憎忧惧,故说一生最怕被情牵绊。好像转入哲学问题的探讨了,还是就此打住好些。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编辑生涯中,有过交往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定不止书中这些作者,为什么选择书中这些人物来写?
丘彦明:为何选书中这12位作家来写?其实不是选,主要是《联合报》和《联合文学》杂志有时做人物专辑,正好其中几位作家被选为专辑人物,我便深入去书写了。
写作时没有想过结集出书。当我决定暂停编辑工作到欧洲游学时,正好台北允晨出版社希望能建立“允晨文选”系列,找我商量,我请出在香港的郑树森教授协助策划,他建议我把做过的作家访问趁机整理,也算是编辑生涯的纪念。
我去掉与作家无关、新闻性太浓、文章太短有待补充内容的文稿,这12位作家在我笔下呈现的面貌最为完整,于是略做修订,配上小传、照片、手迹,结集成书。
中华读书报:能介绍一下您目前在荷兰的写作、工作和生活状态吗?和之前您写荷兰生活的几本书中提到的有哪些变化?
丘彦明:写作《浮生悠悠》《荷兰牧歌》的岁月,我的生活非常轻松,经常旅行,养花种菜、书写、绘画、弹琴,玩得不亦乐乎。
9年前,丈夫唐效找了以前一位英国同事合伙创立Mintres公司。自从当了老板之后,他的全部时间精力放在公司上面。以前,他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有闲暇做许多家务事及园地活。他经营公司之后,每天总有做不完的公事,我便把家务和花围菜圃等杂事都揽了过来。这些年邻居们就见一个瘦小的中国女子,扛着不相称的工具,体力不足做做停停。因为这样,我常常腰酸背痛不说,还不时受伤;但我只要见到花美菜绿,足够了。
去年开始,家中种植的葡萄、猕猴桃果实累累,自己吃送人仍余下许多,我们开始酿酒。买来专业的工具,以专业的态度与过程酿制。结果酿出的法国勃艮第口味红葡萄酒口感顺畅、醇厚。
有了这桩新事物,我的“农妇”生活更加忙碌,从如何培育生产甜美果实开始,到收获、清洗、酿造,无不需要付出耐心和时间。
我琢磨出另一类型度假放松的模式:寻找离家半小时至一小时车距的旅馆,订晚餐、住宿一或两夜。趁机不做家务,吃吃馆子,躺床上读小说。
中华读书报:您眼下在写作什么题目?除了荷兰生活记录,是否会继续《人情之美》这样的写作,或者,从您擅长的艺术领域出发,写写艺术或绘画话题?
丘彦明:近6年多以来,我一直在《深圳商报》写专栏,文学、艺术、旅行、朋友、家居生活的感悟,无所不谈。早些年曾写过一个月一次的短期专栏,有些报纸主编约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写一年专栏,我都婉谢了,因为不愿给自己束缚与压力。
我写作速度很慢,一篇千字文,写下初稿后琢磨又琢磨,修改再修改,要花三四天时间。写书也是这样,好几年才能出一本书。
荷兰田园生活的写作,已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浮生悠悠》《荷兰牧歌》,第三本是《我的九个厨房》,这是我的荷兰家居生活三部曲。说及艺术写作,我长期在台湾《艺术家》杂志、《艺术设计+收藏》杂志担任海外撰述,近20年来写了逾百万字的艺术报道和评论文章。我花10年时间游历荷兰、比利时、英国和法国,写出的文字,可归类为追寻梵高足迹的深度旅行报道。
我写了上百万字的作家、艺术家采访文章;另外,我手边留存有好几箱的作家信件。十多年前,我曾想过继续“人情之美”的写作,仍在编辑岗位上的台湾老友也一直鼓动催促我写,多为台湾文学的黄金时代留下一些史料。但年纪渐长,常有力不从心的顾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