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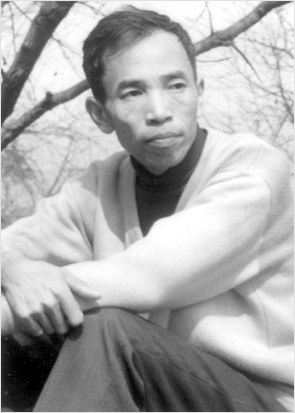
牧 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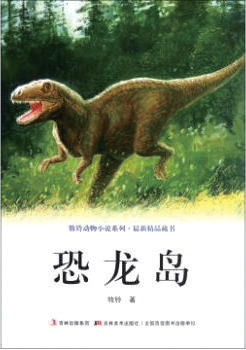
牧铃,湖南平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岳阳市作协副主席。15岁“上山下乡”,先后在牧场、林区、山村劳作;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先后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上海优秀少儿图书奖、儿童文学小说擂台赛金奖等。著有《牧犬三部曲》《牧场英雄》《牧犬小乱子》《梦幻牧场》《恐怖牧场》《梦幻荒野》《艰难的归程》《野狼谷传奇》《荒野之王》《丛林守护神》等作品。
牧铃的创作是率性的。虽然他也重视外界的批评和反映,但一旦拿起笔来,他首先注意的还是自己的故事,是怎样使故事更好看,更有趣,更能吸引孩子;而同时,他又熟悉儿童生活,懂得他们的心理,他笔下的儿童总是活灵活现——所以,他的故事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没有纯为故事性而写的作品,他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品位也决定了他的作品多有很高的文学性。
这样一种率性的创作,使他常常能以自己的作品,向文学界提出新的、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比如他2010年出版的长篇少年小说《影子行动》(中少版)充满了令人感动的喜剧气息,这既不同于当时极为流行的浅薄搞笑的所谓校园系列小说,也不同于过去俄罗斯被称为“带泪的笑”的果戈理、契诃夫等人的喜剧——那其实是带有悲剧内涵的喜剧。我在《回到生活,回到文学,回到美》一文中曾说:“牧铃所提供的,是‘带笑的泪’——这是真正的喜剧,但不是讽刺喜剧,它给了我们积极、感人的青春魅力,快乐而又阳光……小说中感人的力量始终未被喜剧形式所冲淡——我以为,此中含有新颖的美学特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但这种率性,也常常使他的作品显得驳杂而难以定性,有时也确实影响了作品的质量(因许多约定俗成的“定性”其实还是有道理的)。他的动物小说最能说明问题。他长期生活在山区,热爱动物和大自然,从小和动物打交道,按理是最适合写动物小说的。他写了大量动物小说,很受小读者欢迎,文学界的反响却不是太强烈。我读后发现,他在认真观察动物之后,又做了大胆的想象,并在动物小说里掺杂了科幻的成分,这样的作品看起来当然丰富复杂,可这些成分本身却形成了不可解的冲突:这是真实的动物吗?不是,有一部分真实,其他部分则是明显虚构的;这是虚构的幻想作品吗?也不是,有些地方又写得很实。在写作上,它们有时也让人感到些许的焦躁和匆忙,不够从容、愉悦、自信。我知道他正走在探索的路上。
小说《智豺》也是某出版社推荐我读的,这里有很有趣的情节和想象,开头尤其抓人(写一个科研人员不得不消灭最后几只濒临灭绝的红豺,因为它们染了疯病,此病很容易在林区蔓延)。后来,总算有一小群红豺被保护下来,为了监控是否还有疯病残余,另一个研究者异想天开地在它们脑中植入芯片,这芯片后来又成为人工控制动物的入口,竟使这些红豺渐渐具有了人的智力甚至道义……我也觉得作品好看,但又感到,这样的幻想是否太轻率离奇了?更重要的是,它是标榜为“动物小说”的,在我心中的动物小说有明确的定义,我坚信真正的动物小说应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所以我以“离动物真实太远”为由婉拒了批评的任务。现在想来,没能从中看出牧铃创作上的一种新的动向,是有点可惜的。
几年之后,我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读到了他的长篇新作《恐龙岛》(湖南少儿出版社),虽仍标榜为“牧铃动物小说”,我却被作品深深折服了,我得到的是一种清新脱俗的审美愉悦。要说动物的真实性,在这一篇中更渺茫了,这里的恐龙还不是数千万年前曾有过的真实的古生物,而是今天现实生活中被“复活”出来的,作品的虚构性一眼就能看出。这里所写的其实是人,是一位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的中学生,和一个功底很不扎实却富有想象力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发现了能使植物产生返祖现象的病毒,就将它用到恐龙蛋上,结果真的孵出恐龙来了,而且不止一头,林中渐渐成了恐龙的世界,恐怖而离奇,其中还有本领非凡的“智龙”。他们几乎闯下了大祸。这样的故事该有怎样的结局?结局有点凄惨,很快恐龙们全都死了,一点挽回余地也没有,因为它们没法适应现在的环境,尤其是经过人类污染的水和空气。垂头丧气的学生回到了学校;那位科学工作者也终于承认,他其实只是珍稀动物研究所的一名勤杂工,但却有许多异想天开的科学梦。研究所长带人清理了现场,将那位不听话的职工召回了所里,让他从头学习基础课(所长其实很喜欢他的大胆和想象力)。同时让他转告中学生:“所长很欣赏你的好奇心、探索精神和种种大胆的设想,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你跟我一样,需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来打下扎实的基础……他甚至还当着我的面与你们学校的校长作了一次电话长谈,并且许诺:只要你能以优异成绩从州立农校毕业,他将为你提供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机会。”
读这部作品,让我想到老作家任大星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则短篇童话:《大街上的龙》。那也是写几位少先队员和恐龙的故事,也是清新离奇,很有生活气息。同时,又想到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早期科幻佳作,如《海底两万里》《气球上的五星期》《八十天环绕地球》等。确实,这样的作品,无论如何是算不得“动物小说”的,它更接近童话和幻想小说,理应属科幻文学;但又不是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硬科幻”,却是最适合儿童阅读的那一种。想当初,我还是小学生时,读儒勒·凡尔纳,那可真是如饥似渴,三卷本的《海底两万里》不用三天就可读完,一读完马上去找他的新书。今日的创作中,这样的作品已不多见,感谢牧铃又为我们找回了这一重要的文学品种。
而牧铃,也正是在这样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我以为,他原来的一些动物文学的创作,因为存在着种种矛盾,使他下笔时不够沉着和自信。但在写《恐龙岛》时,他已摆脱了动物文学的框框,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写了,整个作品自由、顺畅而圆润。他的着重点是写人,并不是动物,这动物只是他们试验的产物。在写人上,他无疑是高手,性格和心理毕现,让读者如身临其境,时时受到感染。据牧铃自己说,他最初的创作,就是从科幻小说开始的,因当时成人文学刊物不发那类作品,而少儿出版社的《巨人》杂志照单全收,刊出后又深受小读者欢迎,于是走上了儿童文学之路。这就难怪,他后来一写动物小说,常会忍不住加入科幻的内容。我想,今后,他完全可以不以“动物小说”作标榜,而干脆打出“科幻文学”的旗号,也不必与刘慈欣那样的“硬科幻”争高下,就写自己这种以刻画今天的孩子为重心的“轻科幻”,相信定能打出一片全新的文学天地来。
如果说,传统童话是“古代童话”(常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幻想小说是“当代童话”,那么,科幻文学就是“明日童话”或“未来童话”——它的现代意义显而易见。只要写得好,它们受到今天孩子的喜爱也是必然的。因这一体裁的特殊性,作者似不应耽于一己的幻想,而要向科学家们学习,在每篇构思之初,也许还得做些“采访”或“补课”的工作。只要处理得当,更丰富的科学依据不但不会成为想象的障碍,还会为想象的展开提供新的契机和源源的动力。
同时,我们也不应忘却,《恐龙岛》的魅力离不开其中对儿童的描写;另一巧妙之处是写出了科研的难度——它不是那么易于心想事成的,这都增加了作品的现实感(相比之下《智豺》所写就显得有点悬空)。可见,对这类“轻科幻”而言,写人,写当下的熟悉的生活,尤其是写好儿童形象,其实是成功的一大关键。作品中的儿童应是独特的,同时也是血肉丰满的,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希望牧铃今后的此类创作,能多塑造几个立得住的儿童形象,使他们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人物长廊中占据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