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人工智能对文学造成冲击和影响
韩少功:关心了解新科技,是应对新挑战时的功课

韩少功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会是怎样一番不可思议的景象?这看似一个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可能有的假想,作家韩少功却由这个假设性的命题出发,做出了自己现实的,辩证的,且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这篇长达八千余字的文章里,韩少功不无幽默地说,如果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不会要吃要喝,不会江郎才尽,不会抑郁自杀、送礼跑奖,也免了不少文人相轻和门户相争。当真好处不算少。
其实,这只是韩少功的调侃性修辞。他真正要探讨的命题是:机器人,也就是人工智能将对文学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事实上,传说中的人工智能与其说离我们还很遥远,不如说已经对我们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在某些科技和生活领域则已然是触目可及的现实。人工智能发展还被写进了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但要说到人工智能将在文学领域势不可挡地长驱直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的写作,这听来会不会像是天方夜谭?但事实正在发生。韩少功举例说,IBM公司创设的一个玩诗的小软件“偶得”模仿宋代词人秦观的《金山远眺》“做”了一首诗。当他将其拿去某大学做测试,三十多位文学研究生,富有阅读经验和鉴赏能力的专才们,也多见犹疑不决抓耳挠腮。“如果我刷刷屏,让‘偶得’君再提供几首,混杂其中,布下迷阵,人们猜出婉约派秦大师的概率就更小。”
由此,韩少功坦言,“偶得”君还只是个小玩意,其算法和数据库一般般。即便如此,它已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真伪难辨,更在创作速度和题材广度上远胜于人,沉重打击了很多诗人的自尊心。而出口成章,五步成诗,无物不可咏……对于它来说都是小目标。如此这般,要再进一步,人工智能将把文学“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如韩少功所说,法国人罗兰·巴特早在1968 年发表著名的《作者之死》,似乎就暗示了今日的变局,但估计他也想不到,作者最后将“死”到哪一步,将“死”成什么样子。“是今后的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都将在硅谷或中关村那些地方高产爆棚,让人们应接不暇消受不了以至望而生厌?还是文科从业群体在理科霸权下日益溃散,连萌芽级的屈原们也统统夭折,早被机器人逼疯和困死?”
这确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严肃的问题。如韩少功所说,技术主义者揣测的也许就是,人工智能将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文学。但在他看来,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毕竟,技术万能的乌托邦从未实现过。即使是计算机鼻祖高德纳也不得不感叹:“人工智能已经在几乎所有需要思考的领域超过了人类,但是在那些人类和其它动物不假思索就能完成的事情上,还差得很远。”人工智能还差得很远的,是哪些方面呢?当然不是人工智能擅长的形式逻辑的方面,而是从平常看貌似人类智能的“弱点”的方面。韩少功举例说,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的工作。如此在韩少功看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也不会一无所获,但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等看来只能让机器人懵圈,而技术主义者,要把人的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实现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以便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也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韩少功引一位美籍华裔的人工智能专家对他的说法,至少在眼下看来,人机关系仍是一种主从关系,其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特别是一旦涉及到价值观,机器人其实一直力不从心。如此看来,很有可能的事实是: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下棋和揪魔方等一般娱乐,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是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断言,人工智能即使在文学上可望相对地做大做强,也终究只能是一个二梯队团体。也就是说,机器人写作既可能又不可能。说不可能,在韩少功看来,是因为它作为一种高效的仿造手段,一种基于数据库和样本量的寄生性繁殖,机器人相对于文学的前沿探索而言,总是有慢一步,低一档的性质,总是有只能作为“二梯队”里跟踪者和复制者的性质。说可能,是机器人至少可望胜任大部分“类型化”写作。事实上,韩少功在文章里力图阐明的核心观点,就机器人写作的“既可能又不可能”然而,在这“既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文学该有怎样的可能?
低价值/高价值工作的区别,在人工智能的撬动之下,突然得到凸现和放大
记者:读完你这篇文章,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基于人工智能对当下生活产生的潜在或显在的影响,我们即便不知其所以然,但多少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怎么深入想过它会对人类社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文学艺术产生怎样的影响,更不要说有像你这般系统的分析思考了。我挺好奇你何以对这方面有如此深入的关注和研究?
韩少功:不是说作家应该关注社会和深入生活吗?人工智能这事已沸沸扬扬,老百姓在谈,企业家在谈,政府在谈,作家们充耳不闻倒是不正常吧。在我所居住的那个乡下,一个砖厂老板都买了四个机器人(手)干活,农民都在议论。作家的现实敏感度不应该比农民还低。
记者:就我而言,我特别感兴趣人工智能对未来文学的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的多样性会造成怎样的冲击。会不会等到人工智基本覆盖的那一天,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等都得统统消失,而通俗文学则完全被替而代之。未来会不会只剩下两种文学:不可复制的,更为纯粹的纯文学;可以“繁殖”的,普遍意义上的机器人文学?
韩少功:重复性/创造性工作的区别,低价值/高价值工作的区别,在人工智能这一个杠杆的撬动之下,突然得到了凸现和放大。这一点各行各业都一样。就像我在文章中说过的,像我们这些“构成文化生态庞大底部的庸常之辈”,今后也许还能活,但生存空间无疑将受到极大的挤压。事实上,眼下有些通俗文学的写手已经半机器化了,比如俗称“抄袭助手”的软件,网购15元一个,可用来抄情节,抄台词,抄景物描写等,只是用人类的署名掩盖了这一切。由此引起的诉讼案例已经不少,可视为机器人的“挤压”事实之一。可以想象,当机器人更加“聪明”以后,大规模走上前台以后,我们这些庸常之辈还怎么写,确实是一个难题,与其他行业的难题差不多。
记者:我倒是想文学的范畴、概念,会不会因人工智能的冲击而进一步刷新?因为文学是人学,是为了人的文学,当部分写作的主体变为机器人,由“他们”制造出来的文学,该怎样体现诸如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等价值观?即使有所体现,我们又该怎么去信任这种由机器人预设和制造的价值观?
韩少功:机器人写作必须依托数据库和样本量,因此它们因袭旧的价值判断,传达那种众口一词的流行真理,应该毫无问题。但如何面对实际生活的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创造新的价值判断,超越成规俗见,则可能是它们的短板。
记者:很赞同您审慎的乐观态度。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对文学艺术带来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未必是终结,也可能是另一种解放。比如说,摄影兴起的时候,人们都以为艺术要完蛋了,但艺术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又比如说,影视来袭,人们以为文学要完蛋了,但文学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以此类推,也很难说,人工智能来了,就再也没文学艺术什么事了。尤其是你说到的文学最擅长传达的价值观。我想问的是,不可为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是已有的,或是约定俗成的,可以转换为人工编码输入的价值观,我想人工智能是可以达到的。如果是具有很强的个体性,且随着个人的变化而时时有变化的价值观,或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韩少功:我从不算命,给价值观开列清单也会没完没了。还是从具体事例来说吧。江苏卫视有一档很火的节目“最强大脑”。主要是人的识别、记忆、推理能力的比拼,而且还有人机比拼的尝试。很明显,很多参赛选手令人惊叹,“强”得不可思议,但在另一方面,那些能力显然并不构成“大脑”的全部。可以肯定,机器人将来在这些方面要超过人类的,百度机器人就已经出手赢过了几回,但价值判断呢?人类选手即便输了,他们曾经的学习、锻炼、实践运用等就一钱不值?如果人类选手赢了,他们的能力是否有普遍意义和普及价值?是否值得人们一窝蜂模仿与跟进?更重要的,不论是机器还是人,这些“最强大脑”能解决自然、社会、文化艺术中所有的难题?……这些都是绕不开的价值判断。显然,仅靠识别、记忆、推理这些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说过的,人类在很多能力方面不如动物(如听觉和嗅觉),在很多方面将来肯定也不如机器(比如记忆和计算),但这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此电视节目上的所谓“最强”,只是涉及人类智能的一部分,工具理性的那部分,我们尖叫之余却不必在理解上越位。
记者:我还想追问下,你说到机器人写作终究只能是一个二梯队团体,恐不易出现新一代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等巨人的身影,我完全赞同。人工智能的倒逼,也会使得我们问问,最高意义上的文学,究竟在哪些核心的方面为一般写作所不及?比如说,文学所必需的故事、情节、语言等等,机器人都能掌握,且未必弱于一般的写作。那不可替代的只是价值观?要这么说,文学之外的哲学、宗教等等,不也同样适合作为传导价值观的载体?
韩少功:所谓“高价值”,并不是体现为一些结论,一些标签,而是体现在你说的“故事、情节、语言等”之全过程,形成一种总体的美学创造效应。哲学、宗教如果要有创造性,也必须回应和处理各种新问题,形成一场又一场生动活泼的思辨接力赛,不是简单地复制前人。否则,和尚念经,牧师告解,哲学家演讲,各种“心灵鸡汤”,只是陈词滥调人云亦云,我们以前称之为“留声机”的那种,当然是可以用机器人来代劳的。事实上它们已经部分地被代劳了。从“留声机”升级为机器人,恐怕是很容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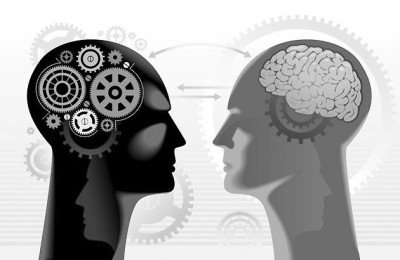
当机器人作为一种“亚主体”或“二级主体”到场以后,有关秩序和规则都需要调整
记者:你说到“人类智能之所长常在定规和常理之外,在陈词滥调和众口一词之外”,还有“文学最擅长表现名无常名、道无常道、因是因非、相克相生的百态万象,最擅长心有灵犀一点通”,很感欣慰。因为我联想到,相比更为偏重逻辑的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似乎最擅长表现这些“其复杂性非任何一套代码和逻辑可以穷尽”的事物,而你举到的那些言论,也都出自中国古代文人之语,是不是由此可以推测,在人工智能全覆盖的将来,如果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中国文学会有更好的前景,且有望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韩少功:西方文化也是蛮丰富的,比如他们确有很强的逻各斯主义传统,与中国有异,但他们也有过强烈和深入的反思。最早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是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那些人,对于中国学者很有启发,丰富了我们对“术”和“道”的理解。在坚守人文理想方面,可以说东、西方知识界各有贡献吧。
记者:说得也是。不过有一个观点,我不是完全赞同。如果说人机关系仍是主从关系,那人工智能还是有赖于人的指令。既然是人在操控,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确是不会要吃要喝,不会江郎才尽,不会抑郁自杀。但人工智能背后的利益归属还在于人,所以是不是因此就少了送礼跑奖、门户之争,就不好说了。
韩少功:对我那些调侃性的修辞,你不必太过认真。如果人机关系处于主从状态, 机器人当然会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人类的影子和指纹,不过是一种配比不同的人机组合关系。但机器人介入进来以后,情况毕竟会不一样,比如一个像“偶得”那样的写作软件,写出来的诗有无版权问题?这个版权是属于制造商,还是属于购买者,还是属于使用者(如果不是购买者)?抑或有关“版权”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承认?……这些新问题都会冒出来。维基百科就与所有传统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不同,是无数匿名者的作品,公共化产品,几乎没有作者和版权可言。在“云”时代,各个终端的“个体”意义越来越弱,而前面说到的公共化、半公共化产品会越来越多。
记者:的确如此。文章主要分析了人工智能会对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同时也好奇,在不久的将来,文学对其力图表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呈现?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嘉兴某个地方的织袜厂面临倒闭,用机器人代替人工降低劳动成本后,又重新发展了起来。就这个报道来说,我更关心的是,原先在那里工作的工人,离开那个地方后会怎么样。由此联想到,将来要如你所说,至少45%以上的智力劳动都要被人工智能取代,那有闲的人倒是多了,按常理说,搞文学艺术的人也该多起来了。但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包括矛盾冲突等,都可能淡化的社会里,文学能表现什么呢?
韩少功:说以后社会冲突会随之“淡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纳米材料……这些东西将缓解哪些矛盾,又将造成哪些危机,眼下乐观派和悲观派都不少。作家们也许不必急于选边站队,但关心和了解这些新事物至少是必要的第一步。而且中国人常说“有其利必有其弊”,这话反过来说也行。各种新技术的关联影响可能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基因技术似乎也是吉凶并存。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人类战胜很多疾病,是大好事;但另一方面,就像以色列学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说的那样,在市场化条件下,它也可能催生“生物等级制”,让有钱人的基因优秀,没钱人的基因低劣,社会的不平等从基因开始,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看法也并不像是危言耸听。
记者:我还想问问,人工智能对读者阅读会产生何种影响。就像你在文章里提到的,很多年前,“深蓝”干掉国际象棋霸主卡斯帕罗夫,去年“阿尔法狗”的升级版Master砍瓜切菜般地“血洗”围棋界。也许将来象棋、围棋界,上演的主要是人机对战的现象。不知道到那时,读者是不是还能体会到像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川端康成《名人》、阿城《棋王》等作品中描述的人人对弈的景象的绝妙之处。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学表现的领域,还将进一步遭到挤压?
韩少功:长袍马褂、大刀长矛早就过时了,但古典文学名著仍然可以让我们兴趣盎然,作家们也仍有写不完的新题材,包括历史题材,《甄嬛传》《芈月传》什么的。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即使是写原始部落的生活,写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前的生活,只要写好了,同样可能成为经典之作。说实话,由于有了大数据,作家们利用历史档案的能力大大增强,写历史题材倒可能更有方便之处了。
记者:我有时不免想,对于人类的未来,我们是不是过于悲观了?比如,你担心就业危机要是覆盖到适龄人口的99%,哪怕只覆盖其中一半,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构都会分崩离析?这样的忧虑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自我更新和调控的能力。打个比方吧,前些年我们都担心克隆人会带来伦理危机。但克隆人被有意识地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制止了。当然,这倒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空间,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千万别丢下我》,探讨的就是克隆人与正常的人之间的关系。
韩少功:我没看过这个作品,没什么看法。但我相信对生命的理解将要遇到重大挑战,那是肯定的。设想将来一部分人类不过是基因公司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享不享有同等的“人权”?毁坏这样的产品与毁坏一台电脑有什么区别?……人道主义的根基,真、善、美的根基,会不会从这一点开始出现动摇?当然,我从不对人类的未来悲观,始终相信自然和社会的自我调适能力。我只是觉得眼下很多文科生太不关心和了解科技,很多理科生则太迷信科技,在价值观问题上脑补不足,严重缺弦,几乎是一头扎进数理逻辑的一神教。这样的两头夹击之下,各种盲区叠加,知识界的状况倒是让人担心。
不应该把高科技单纯看成一种工具,可能更需要看到这些东西对人和人性的改变
记者:事实上,读完这篇文章后,我的另一个感慨是,中国作家普遍缺少像你这样的前瞻性思考,我们更多关注历史和现实,至于未来会怎样,那是科学家该干的事,跟作家写作没什么关系。当然近年来,随着科幻文学崛起,似乎有一些科技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写作中融入“未来”。但我们通常所说的严肃文学创作里,还是相对缺乏未来这样一个维度。在你看来,前瞻性思考对于作家写作来说有何重要性?
韩少功:我没有具体的科学专业背景,也从未打算写科幻作品,只是把科技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有点瞎琢磨而已。这种瞎琢磨也说不上“前瞻”,其实大多是针对现实当下的。比如微信等通讯工具改变了人际的空间关系,让远友变得很“近”,却让近邻变得很“远”,以至“相思”“怀远”等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已大大减少了。这就是现实。又比如电子虚拟世界使人们见识很广,信息量超大,但大多数“知道分子”的知识来自屏幕而不是亲历性实践,因此知识的质量和深度大打折扣,以至知识界主流前不久被全球金融危机、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一再打脸,暴露出知识与实际的严重脱节。这也是现实。光是看清眼下的这些事,也许就够我们忙活的了。
记者:如果联想到早年你提出了“文化寻根”,很多年后,你倒是对文化、文学的未来孜孜以求,这样大的一个跨度,会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穿越。我想问的是,这两者间是否有什么关系?你的这些思考有何一以贯之的地方?
韩少功:“寻根”不是当年问题的全部,只是媒体把那一部分声音放大了,就变得拉风抢眼了,造成了某种错觉。如果你看过我当年几乎同时写过的另一些文章,如《信息时代与文学》,就知道我的关注范围并无太多变化。
记者:这对我倒是一个提醒,你的思考即使在同时段里也是多方面的,读者可能关注被媒体放大的某一方面,却对其他方面造成了遮蔽。比如,你十年前就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深入探讨了文学与生态的关系问题,现在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你的这些前瞻性思考,也让我想到你的不少创作多少有乌托邦的色彩。但你也知道,中国文学,尤其是大陆文学比较少乌托邦色彩,即使有,也更多只是革命乌托邦、政治乌托邦的折射。严格说来,我们几乎没有乌托邦文学,也没什么反乌托邦文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比较缺少对于未来的想象所致?如果可能,不妨结合对人工智能的思考,试着给读者描绘一个中国文学的乌托邦。
韩少功:你这个想法不错,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力不从心。我倒是希望打破专业界限,有更多有科学专业背景的人来参与文学,改变一下文科从业群体的成分结构。我只是希望那些理科生多一些文、史、哲的素养,不要以为背得下几首唐诗宋词,看过了一堆美剧韩剧,就可以人文一把了。我说过,我不满意的,是眼下很多科幻片都不过是“《三侠五义》的高科技版,更愿意把想象力投向打打杀杀的激光狼牙棒和星际楚汉争”。不管这些作品出自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他们的知识体系看来都有缺陷,各有各的毛病。他们不应该把高科技单纯看成一种工具,可能更需要看到这些东西对人和人性的改变。
记者:回到文章开头,你谈及文学翻译。想到你早年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为何就不再翻译了?是不是你早就意识到翻译的局限,意识到翻译终会被替代,兴趣就随之转移了?有意思的是,文章有很多前沿思考,参照引用的却基本上是已译成中文的外文著作及资料。是不是说,现在很多资料都已经同步,不必像以前那样费心去外文里找寻、翻译了?
韩少功:人工智能肯定能大大提升翻译的效率和产能,但这是指一般的翻译,而文学翻译则是另一回事。正因为文学翻译是翻译中最接近价值观的一部分,是面对事物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因此很可能是机器翻译最大的难点,甚至是一大克星。优秀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reproduction,一种高价值和创造性的工作,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没法被机器人替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家们拒绝机器的帮助,就像我们眼下阅读和写作,其实早已受益于百度、维基百科、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智能化工具。人机之间的互渗、互动、互补已经是一种常态。
记者:文章最后谈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因为涉及一些过于玄奥的理论,虽然经过了你的演绎和转述,于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好理解。但你写到在捷裔美籍数学家和哲学家哥德尔的故乡,亦即捷克的布尔诺一条空阔无人的小街的街头,有人随意喷涂了一句“上帝就在这里,魔鬼就在这里”,倒是引发了我的兴趣。这么说吧,尼采预言,上帝已经死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像有人预言的那样人也“死”了。要真是这样,人怎么解决自己的信仰问题?
韩少功:兹事体大,只能以后再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上帝死了”是现代科学的第一个社会后果;至于“人”死不死,人文价值体系还要不要,真、善、美这一类东西还要不要,是科学接下来逼出来的另一个大悬问。如果信仰不是一个神学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知识的有效支撑,那么关心和了解新科技,就是应对新一轮挑战时必不可少的功课。换句话说,如果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那么所谓信仰就会重新落入神学之手——事实上,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宗教、迷信、邪教力量的大举回潮,居然在一个高科技时代大举回潮,正好证明了知识界的某种危机和无能。文科和理科双方恐怕都得对此负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