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史学革新运动是由法国年鉴学派发起的。这一学派因创办于1929年的《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注:该杂志四次改名,目前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他们主张用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以人类活动的整体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他们还主张史学研究要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合作。可以说,年鉴学派是“新史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影响深远。
近日,系统介绍这一学派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年》一书在中国问世。它的作者是80岁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他也是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和伊曼纽学院研究员。
“我像许许多多其他外国历史学家一样,受年鉴学派运动的启发。”专门研究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的彼得·伯克自认是年鉴学派的同路人,也一直关注着年鉴学派的命运。在书中,他把年鉴学派区分为三代学人: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创建者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第三代则包括乔治·杜比、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人。

彼得·伯克
围绕《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年》一书,近日,腾讯文化作者对彼得·伯克进行了邮件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如果只写布罗代尔一个人,不够“布罗代尔”
腾讯文化:这本新书的前身《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发表于1990年。你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下这本书的?
彼得·伯克:当时英国政体出版社邀请我写一本有关布罗代尔的书。这是他们“社会学思想家”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我回复称,如果只写布罗代尔一个人,不够“布罗代尔”,我希望能写写年鉴学派这整个群体。1989年这本书完成时,恰逢年鉴学派创建6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
令我难忘的是,1977年,我受邀参加了在美国宾厄姆顿召开的总结布罗代尔学术贡献的研讨会,并就英国对年鉴学派的接受情况发言。当时布罗代尔就坐在第一排!我的发言主题是“对法国史学革命的思考”。当时我开玩笑说:“我可不是埃德蒙·伯克的后裔。”布罗代尔也觉得这个玩笑很有趣。后来,在我写关于年鉴学派的这本书时,我就用“法国史学革命”作书名。
腾讯文化:根据你的经验,写成功的学派综述,需要关注哪些方面?要避免哪些容易犯的错误?
彼得·伯克:我们需要强调这个学派和其所处的更宽泛的外界环境的关系,学派内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比如他们是否都追随学派领导人,是否有异端,学派领导者是否听从追随者的建议。
我们需要避免给“学派”贴标签,仅凭表象做判断。比如在“当权”许久后,布罗代尔还认为自己是异端;拉维斯与瑟诺博司都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但年鉴学派并未太推崇他们,他们需要更了解他们的权威人物来认可和维护。
腾讯文化:年鉴学派像是一个大家庭:布罗代尔是勒华拉杜里的老师,费弗尔对待布罗代尔和芒德鲁像是对待自己的儿子……学派成员之间也经常存在亲属关系。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学术裙带关系”?在西方学术圈,人们对这种状态持什么态度?
彼得·伯克:我觉得“子承父业”并没有什么错啊!当然,他们通常很聪明,会选择不同的领域做研究,但如果在有其他更胜任的人选的情况下,只因为存在关系——无论是真正的亲属关系,还是象征性的家庭关系——而把这项工作给自己的“家人”,那我和其他西欧学者就会感到忧虑。
当然,我也不清楚除“家人”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布罗代尔也曾任命学生莫里斯·埃玛尔为法国巴黎人文科学之家的头。
腾讯文化:众所周知,布罗代尔的理想是续写一部综合的、无所不包的“总体史”,你认为他是否实现了这个愿望?
彼得·伯克:差不多吧。但我认为布罗代尔并没有很重视文化,即他所谓的“文明史”。尽管他在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等作品中对此涉及了一部分,但他错失了书写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文化交流的机会。
从1949年之后,布罗代尔的研究方式就备受质疑
腾讯文化:布罗代尔最大的贡献是提出用三层分立的运行模式(即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层)看历史,以及总体史的研究方法,但一些学者批评他的研究不够深刻和复杂。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彼得·伯克:我认为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足够复杂,他对能揭露事实的文件和资料有着敏感的嗅觉,但就历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而言,他可能缺乏必要的训练。
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怎么做计量研究。他或是和同事合作,或用别人的结论进行合成,比如《地中海》的第二版。
腾讯文化:布罗代尔不止一次地强调单个事件、单个人物,甚至重要人物在历史上并不那么重要,他认为事件史最为肤浅。年鉴学派也经常因不重视事件史被批评。但事实上,在写作中,年鉴学派都不可能规避对“事件”的书写。在你看来,年鉴学派笔下的事件写作有何主要特点?
彼得·伯克:要因人而异。马克·费罗写了《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社会史》《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弗朗索瓦·福雷和莫娜·奥祖夫都写过法国大革命史。
从新的角度书写事件的年鉴学派成员当属乔治·杜比,他的《布汶之战的传奇》就很有特点。他受约写一本书,叫“塑造了法国的那些岁月”,这原本是个很常规的主题,但他实际上写的却是后世如何看待这场战争,这就是从长远角度来审视一个事件对后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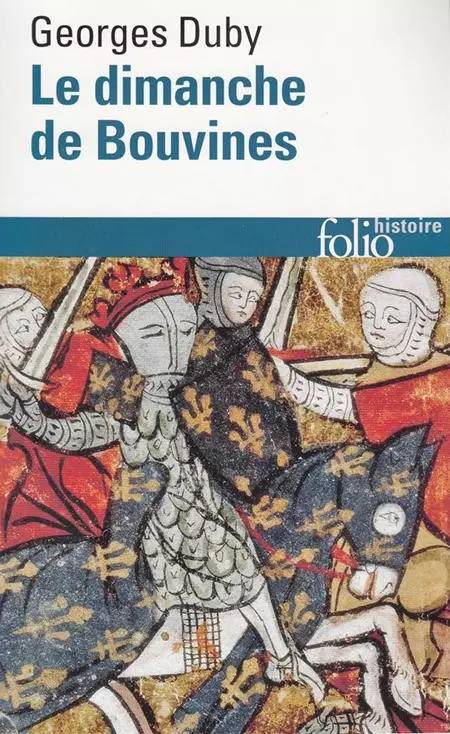
《布汶之战的传奇》法语版
腾讯文化:如果布罗代尔仍然在世,在今天的政治和事件背景下,你认为他会被怎样质疑?
彼得·伯克:从1949年之后,布罗代尔的研究方式就备受质疑,特别是受政治历史学者的质疑。质疑在今天依旧存在。
如果让我指出一种新类型的批评,我会说是“社会生态学”。比如布罗代尔的地理历史部分并没有讨论从古典时代开始的森林毁坏和水土流失,尽管这种情况在16世纪因为营造海军工程还恶化了。
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和马克思的“整体历史”区别不大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提到,布罗代尔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这一点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尤其明显。具体来说,他在哪些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彼得·伯克:主要在排斥经济决定论方面。布罗代尔更倾向于地理决定论或半决定论。他的观点有些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无论如何,他承认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政治和文化中的重要性。
腾讯文化:不光布罗代尔,其他一些年鉴学人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与此同时,布罗代尔又建议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距离。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莫里斯·阿居隆和米歇尔·伏维尔也被置于年鉴学派核心圈之外。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
彼得·伯克:很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也受到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是布罗代尔拒绝承认莫里斯·阿居隆和米歇尔·伏维尔是核心圈内的人,还是说后两者故意远离核心圈,我不是很清楚。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比如霍布斯鲍姆,是最先欢迎使用年鉴学派研究方式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在当时的史学界,这也是一种受欢迎的“人民路线”。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方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彼得·伯克:布罗代尔的总体史(Histoire totale)和马克思的整体历史(Gesamtgeschichte)并没有多大区别。在生前,布罗代尔最崇拜的在世历史学家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和维托尔德·库拉。
当代汉学家从年鉴学派那里学到了很多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较少提及年鉴学派的中国研究。多数年鉴学人对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和谢和耐的成就持何种态度?中国研究在年鉴学派眼中,是否仅算法国之外的一个“区域研究”?
彼得·伯克:年鉴学派非常重视区域研究, 无论是法国朗格多克这样的小区域,还是东南亚这样的大区域。
布罗代尔也很重视中国研究,他让汉学家白乐日和让·谢诺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其前身为巴黎高等实践学院)任要职。谢诺是法国共产党员,当时支持区域研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了异议,但布罗代尔坚持对他委以重任。布罗代尔没有敌视马克思主义。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年鉴学派对当代汉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彼得·伯克:我对汉学的了解不太多,所以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汉学家卜正民和伊懋可从年鉴学派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年鉴学派的学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学者王国斌一直很关注亚洲的布罗代尔主义者。
腾讯文化:有人评价你看到了年鉴学派争夺权力的那方面,比如你说“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两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只是集中介绍年鉴派的学术成就,很少涉及争权夺利的斗争。这是为什么?
彼得·伯克:成就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也是能让外人对年鉴学派产生兴趣的原因。我提到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不同观点、布罗代尔和芒德鲁之间的争执,但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详述。的确,这部分内容需要展开探讨。
腾讯文化:理查德·莫文·安德鲁(Richard Mowery Andrews)在其著作《年鉴学派的暗示》中指出:“尽管法国模式的区域研究对美国深具重要性,年鉴学人的著作几乎没有吸引北美史学家的兴趣”,你在书中援引了这一观点。这样的情况有所改变吗?
彼得·伯克:我记得安德鲁在1977年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不这样认为了。今天的环境史更加重视对区域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