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有追求的考古学家肯定是不满足于盆盆罐罐的研究的,我们的终极理想是透物见人,甚至探究古人的思想。中国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是兄弟学科,而它们作为研究手段,最终都应升华到大历史研究的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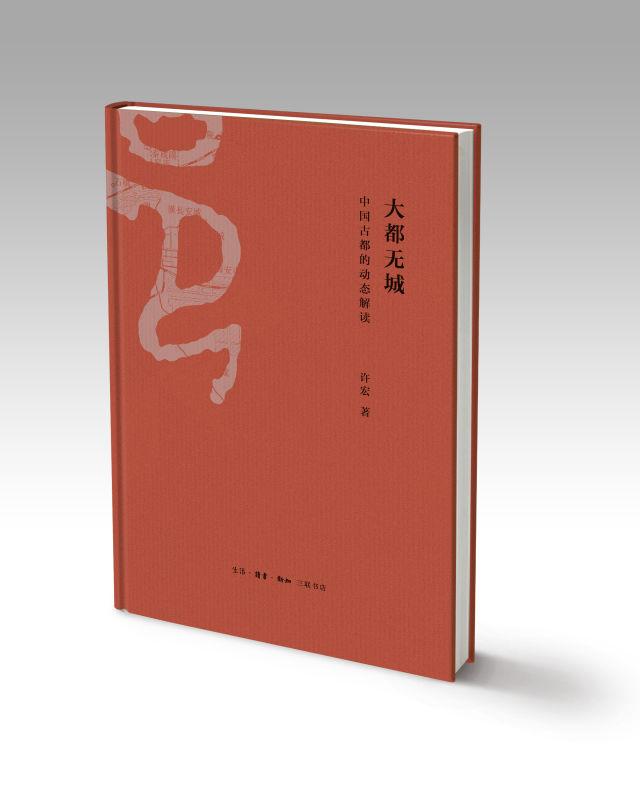
继《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之后,著名考古学者许宏继续他的以“考古学本位”说中国之旅,今年再度推出《大都无城》,考察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时代的都邑变迁,提出“大都无城”的观点,认为该都邑形态肇始于“二里头”时代,再度深化了“中原千年大转型”的结论。
这一颇具颠覆性的认识,引发公众的极大兴趣,自出版后,屡次登上媒体好书榜。“高冷”的考古学知识与公众的求知热情深度契合,使严谨的学术走出书斋,融入国民的智识,实现了另一种价值的飞跃。
今年底,《大都无城》入选腾讯·商报华文好书2016年度评委会特别奖,以表彰其在上述方面的突出成就,恰如评委刘苏里所说:“这是一部看似小型,但以其“大都无城(墙)”观点必将载入史册的大书。这一颠覆原有“无城不郭”共识的结论,既由扒梳前人零星叙述而概其成,亦是作者20年研究专业、审慎之总结。联系《何以中国》等作品,‘中原’政制于两千年前发生重大转型结论,亦呼之欲出。是中国考古学界重大研究进展。以“小书”面世,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以下是腾讯文化对许宏教授的专访:
腾讯文化:书名是“大都无城”,结构与“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类似,是否暗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即不设防的“都城”就是好的?
许宏:谈不上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与既往“无邑不城”的主流认识相比,我通过对考古现象的归纳和历史传统的辨识提出的“大都无城”的观点,至少是具有颠覆性的,书名相应地也该响亮些,是有这样的考虑。同时,“大都无城”也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去认识,这种认识当然是正面的、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都无城》的书名的确与“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道至简”等意境相近。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腾讯文化:您将开启“大都无城”时代的“二里头”定义为中国广域王权国家,依据的是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譬如城内内部功能分区强化,有保护统治者的封闭区域,以及其他遗址出土文物与“二里头”文物的联系等等。这种定义,似乎是参照了后世王朝国家都城以及组织方式给出的。这种建构是否会因忽视了别的可能性而与历史真实有距离?
许宏:正是秉持由已知推未知的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本人从已被公认的三代王朝的都邑内涵与社会结构特征向上推,指出只有距今3700年前后出现的二里头文明是这种广域王权国家的先导,许多制度的创建前无古人而下启来者。再往前,东亚大陆还是“满天星斗”的无中心的多元政体并存的时代,所以说作为“大都无城”之肇始的二里头都邑及其时代,开创了“有中心的多元”这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当然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和建构,但就考古学证据和推导理路而言,它比另外的代表哪种可能性的推论距历史真实更远呢?是二里头村落说,还是单线进化的5000年文明说?
腾讯文化:从“大都无城”时代的实用性城郭到汉魏以后礼仪性城郭,是否单线转换?为何会有这样的转换?
许宏:这个还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我在书中总结出的城郭齐备、都城大中轴线和严格的里坊制这三项,几乎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标配”,应该是皇权增强,集权国家礼制完善、都邑制度渐趋规范的反映吧。其中所显现的深层次的历史问题还很多很复杂。已有日本学者在读了《大都无城》之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般认为先秦秦汉具有较典型的华夏底色,而魏晋南北朝以降,北方族群走马灯似地入主中原,外来色彩浓厚,甚至可称为“胡汉文明”。但本人指出的“后大都无城”时代上述礼制建设的规范化行为,恰恰是肇始于这一时期的,完全超出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所谓常识性的认识。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有待进一步探究。

二里头遗址宫城东墙
腾讯文化:您屡次提到“大都无城”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如何理解这种“文化”的自信?
许宏:从考古学上观察,“大都无城”的时代,都是广域王权国家或初期帝国兴盛强大的时代,而非积贫积弱的时代,几无例外。从二里头到西周,中原王朝的基本特征是“国上之国”,王朝具有盟主的地位。《左传》记载春秋时代人有这样的话:“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明确表述了外线作战思想和讲信修睦的理念和气度,这是对西周时代及其以前“大都无城”状态的一个极好的诠释,相当于我们说人民军队是钢铁长城,根本不需要再筑个城圈来自保。冯时教授通过对古文字和文献的梳理,指出在夏、商及西周文明中,作为君王所在的京师之地,都是以不筑城墙的“邑”的形式出现的,意在宣示教化,无城之邑具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这已经从防御文化上升到政治文化的范畴。因此,可以认为“大都无城”是一种代表当时的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理念。“大都无城”所显现的文化自信,当然指的是广义的文化概念。
腾讯文化:考古学与历史学科的区别之一便是,前者重视考古出土材料,擅长对出土之物的解读,而后者更重视文献及其解读。考古学本位的解读与历史学本位的解读,您认为二者的区别在哪?考古出土的非文字性质的材料,在何种意义上能转化成“史料”?
许宏:其实你已经说清了他们的差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我们在完全没有传世文献的环境下做考古,那“考古学本位”就不是个问题,或者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是个具有丰厚文献和重史传统的国度,甲骨文之前的考古遗存出土后,最引起关注的是它们与文献所载国族是否能“对号入座”的问题,这代表了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主要研究取向。但后世追述性的文献材料早不过东周秦汉,所记内容又鱼龙混杂,所以歧见纷呈久议不决,就是很自然的事儿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本人在内的少数学者秉持“考古学本位”的研究方法,即不以后世文献为研究前提,而是先梳理考古材料,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做阐释历史的努力,疑则疑之,慎重整合,这可以说就是“考古学本位”的研究吧。传世文献、考古遗存、口述史、人类学与民族学材料等,本身就是各有千秋的史料。考古学材料转化为史料,当然需要考古人的阐释,它也具有或然性和相对性,多为推论和假说,是可以理解的。
腾讯文化:从您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到《大都无城》,这几本考古学小书内在的一以贯之的关怀是什么?
许宏:考古人写史,是我这几本小书的共同特征。有追求的考古学家肯定是不满足于盆盆罐罐的研究的,我们的终极理想是透物见人,甚至探究古人的思想。我个人认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是兄弟学科,而它们作为研究手段,最终都应升华到大历史研究的层面。本人的三本小书《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和《大都无城》都是在这一路向上的粗浅尝试。如果说《最早的中国》是关于二里头都邑的微观研究,那么《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就是中观研究,而《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可以说是宏观研究。下一步想写的《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就属于大宏观了,试图超越“中国”,从大历史的视角,梳理下东亚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与动向,届时请大家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