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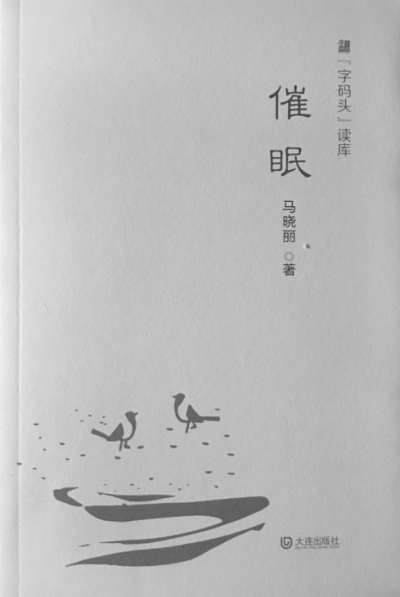
《催眠》,马晓丽著,大连出版社出版,29.00元
正是由于《楚河汉界》的受挫,才逼着我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省,对军事文学创作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才使我从狭隘的功利写作中清醒了。它至少给我带来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使我沉静下来,避免了因获奖而可能造成的错误的自我认定。二是使我对文学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2016年8月,军旅作家马晓丽的中篇小说《催眠》被改编为同名话剧,登陆人艺实验剧场。
这对马晓丽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新鲜体验。这部聚焦现代人心理健康的作品,搬上舞台后被赋予了格外鲜活的生命力。
在《楚河汉界》之后,马晓丽表达自己对长篇小说写作的感悟:就像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平时在生活中累积的大量想法,可以在这时系统地、集中地进行梳理,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贴着一个个生命轨迹去行走,会看到许多各不相同的生命现象,会带给你更多包容和理解,这些都会提升一个人的境界。而写作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境界的高下之分。
作家的精神修炼是长期的,贯穿于整个写作生命的过程中。时至今日马晓丽还在不断地从精神束缚中往外挣脱。挣脱,是这些年她在军事文学现场最常说的一个关键词。
中华读书报:在最初的写作如《夜》和《长大了》,被评论家称为是您创作的“少女期”,您自己如何评价?
马晓丽:那时的创作是很盲目的,没有想法,随意性强,碰到什么写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只是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这种冲动里既有对文学的热爱,有表达的愿望,也有名利的追求。创作早期这种名利追求是有益的,助燃了我的创作热情。我那时就与跟我一起获奖的人一样,沉醉其中,觉得小说没那么难,我写第一篇就获得了成功嘛。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跟著名作家对话座谈,让我得意洋洋地晕了很长时间。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文学为何物,根本不知道小说为何物。所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飘飘然地写了一些不知所云质量不高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您在200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舵链》,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获得全军的一等奖,引起广泛关注。
马晓丽:这个短篇之前,我开始对自己的语言产生了怀疑。之前,我受新闻写作和阅读翻译作品的影响,语言一直很板。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语言越来越感到厌恶,急需寻找一种令我的表达更舒服,更自然,更个性化的语言方式。现在想来,其实任何改变,都是从怀疑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当时自己还没意识到。写这篇小说时,我试着让自己放松,不再绷着,不再刻意修饰生活语言,结果发现笔下的文字和人物一下就活起来了,有了生气。这种改变令我很享受,就像打开了一扇门,连思维都变得自然流畅起来了。所以我想,语言与思维大概是二位一体的,也许语言的变化原本就来自于思维的变化。从这个短篇开始,我的小说语言有了新的变化,也为接下来我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中华读书报:《云端》好评颇多,这个作品是纯虚构吗?有无事实依据?恕我直言,阅读中感觉语言和叙述略有拖沓,您的写作,设计情节或人物,是否理念在前?
马晓丽:《云端》是迄今为止我自己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作品当然是虚构的,但任何虚构都必然会有现实的投射。写这篇小说的起因是我婆婆。我婆婆是个三八年入伍的老八路,有一次,她看到有些老干部家属的不文明行为时,悻悻地对我说了一句:太没有知识了,还不如我看管的那些国民党小老婆呢!她的这句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通过交谈我发现,我婆婆对“国民党小老婆们”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她鄙薄她们,因为她们是敌人;而另一方面,她又暗暗地欣赏她们,欣赏她们言行举止中透出的文化气息。我想知道,是什么使我婆婆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会时不时地超越阶级意识看待不同阵营的敌人。我婆婆不可能跟我探讨这些,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突然又冒出一句:我还从一个国民党小老婆裤裆里搜出了金条,被大会表扬了呢!我心头一震,在满脸自豪的婆婆后面,我看到了另一个女人,那个被婆婆称为国民党小老婆的女人。我突然很想知道,这样两个不同的女人之间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理念在前,但在开始下笔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们的走向和结局。
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确想让叙述缓慢一些,绵密一些,小资一些。我觉得这样会更女人,觉得这应该是一篇很女人的小说。
中华读书报:《云端》中两个女人涉及私密的对话,我觉得似乎不大能够理解。那个年代,包括她们的特殊身份——总觉得不大真实。我想知道的是,您如何看待虚构的合理性?
马晓丽: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不能理解女人之间的私密话题。也许您认为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那样的私密话题,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女人对私密话题的克制和释放都是一样的。就如同男人之间常在私下谈论女人一样,女人也会在适当的契机下谈论男人,包括谈论自己的身体感受。当然,契机很重要,即便她们的身份不同,但只要给了她们合适的契机,就会唤起她们探究身体和生命秘密的兴趣和热情。这是一种来自于生命本身的自然驱动力,是任何环境和外力都无法彻底遏制的。
说到虚构的合理性,我认为虚构通常都是建立在作家自觉的合理性上面的。当然,作家的自觉未必一定能与所有读者的他觉相吻合,在这里我的自觉与您的他觉显然就不吻合,这很正常。其实,您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建立在您的虚构基础上的。您虚构了一个那个年代的现实,以您虚构的现实来衡量,认为在那个年代,这两个不同身份的女人之间进行私密对话是不真实的。那么问题是,您的虚构是否就具有合理性呢?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获得鲁奖的《俄罗斯陆军腰带》吗?是否算得上您最好的短篇小说代表?
马晓丽: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是我最好的小说,我最好的小说还是《云端》。在《俄罗斯陆军腰带》中,我不得已地掩饰了一些内心中最真实的痛感。起初动念写这篇小说,缘于我亲眼所见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的一次事故。当时一架飞机从我们面前飞过后,突然摔落下来,在我们的视野中爆炸起火。我知道演习中发生意外事故是很正常的,让我感到不正常的是我们的反应。事故发生之后,我看到了两军对待事故的截然不同态度,这区别不在于不同的民族习惯,不在于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在于文化背景中的生命意识,在于对生命、对牺牲的人文态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其间的区别带给我、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痛感,但我无法直接表达。我写了很多花边似的两军区别,用来掩盖我最想说的,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区别。在笑着讲述那些有趣的两军故事时,我的心一直是痛的,痛得直想哭。所以,每当有人提到这篇小说对军队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命意识进行追问时,我都会心存愧疚和感激,愧疚自己的软弱,感激终究还是有人能径直抵达。
中华读书报:《白楼》和《覆水难收》中的主人公都是在权力角逐中失败的军人,他们多少有一点理想;《楚河汉界》也塑造了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军人。文坛对《楚河汉界》评价很高,但是并未能获得大奖。
马晓丽:《楚河汉界》是在评上全军最高奖后,被作为问题小说拿下来的。《楚河汉界》受挫之后,我个人的狭隘功利目的基本落空,这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所说的个人狭隘功利目的就是获奖、出名、立功、晋级等等既得利益。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很渴望得到这些既得利益的。幸运的是,我的目的没能达到。
我把这说成幸运,是因为正是由于《楚河汉界》的受挫,才逼着我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省,对军事文学创作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才使我在追问、反省和思考中从狭隘的功利写作中清醒了。它至少给我带来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使我沉静下来,避免了因获奖而可能造成的错误的自我认定。否则我会以这篇小说作为自己的军事文学创作的标杆。以我现在的眼光,已经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楚河汉界》中带有许多我多年精神捆绑的烙印,带有我文学意识和文学思维的诸多局限了;二是使我对文学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其实任何文学奖项都与文学本身无关,它既不是文学的目的,也不可能促进文学质量的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我们看重的文学奖项,无论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其实都是一种社会游戏。你可以去参与,但切不可当真,不可把这些东西当成文学追逐的目标。否则必然会陷入到狭隘的功利写作中了。其实挫折也是修炼,而且往往是更为有效的一种修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