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被认为是韩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近日来深参加“诗歌人间”活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专访
高银:深圳是诗歌的栖息地

▲高银在“诗歌人间”主题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韩国诗人高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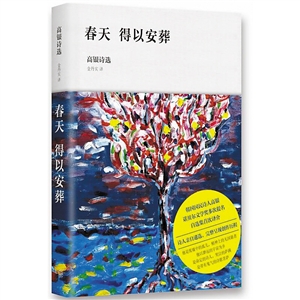
▲高银诗选《春天得以安葬》。

▲《喜马拉雅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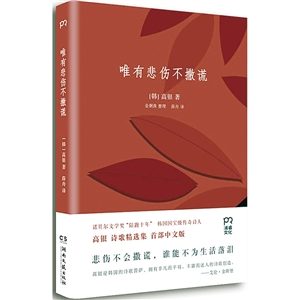
◀高银作品《唯有悲伤不撒谎》。

▲高银来深参加第十届“诗歌人间”主题活动。(主办方供图)
在韩国,诗人高银有着非一般的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他遭遇过战争,曾经入山出家,后又还俗,投身公共事业,建立图书馆,创办高等公民学校等。他的诗歌擅长捕捉一人一事一记忆,撞击出灵感的火花,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幽深的意境素描现实生活。作为韩国当代最著名的诗人,高银连续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韩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艾伦·金斯堡称赞他是“韩国的诗歌菩萨,拥有非凡而平易、丰富而迷人的诗歌创造”。近日,已届83岁高龄的高银受邀来深参加第十届“诗歌人间”主题活动,期间在翻译家金丹实的翻译帮助下,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专访。
深圳是诗歌出发的地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此次是先生您第一次到访深圳吗?
高银:所有的第一次,其实都是第二次。我并不是“第一次”到深圳来,在遥远的某个时候,另一个“我”曾经来过,所以此刻我在这里。我通过之前已经来过这里的另一个“我”早有耳闻,想知道更多,所以我来了,这次应该是“第二次”来。曾经有一个人,瞩目这个渔村,讲述了伟大的故事,“黑猫”和“白猫”,于是与此地发生永久的关联。如今这个时代,“黑虎”和“白虎”同在,“黑虎”在发出啸声,诗人的声音是对它的模仿,所以诗人发出的声音会越来越强而有力。诗,是遥远地方传来的难以辨认的声音,惟有听觉极为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得到它。与此同时,诗的音响又是足够宏大的,能让许许多多的人同时沐浴其中。深圳,正是弘大的诗音响起的地方,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它。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刚才诗意的表达为深圳这座城市赋予了诗歌的色彩。
高银:你说得对。深圳是诗歌出发的地方,也是诗歌栖息的地方。今年是新诗百年的纪念年份,也是深圳举办“诗歌人间”活动第十年,我想这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韩国诗人,一个俄罗斯诗人,加入了深圳的诗歌活动,也许暗示着深圳需要世界的诗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如果请您即兴赋诗一首,描述这两天在深圳所感受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气息,您会怎样写?
高银:今天看到了紫荆花,我第一次知道这种花是缘于朋友告诉我它是香港的区徽。在唐代,岭南地区曾出现禅宗六祖慧能。在此之前,中原没有把岭南认知为人类文明存在的地方,有人提出疑问:岭南人还能有佛性吗?慧能打碎这个偏见,给出一个响亮的回答:“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也许从那时开始,深圳这片土地就已是修悟之地了。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的长河积蓄坚忍的能量,它经得起漫长的等待。这片土地,一度是无名的渔村,进入当代之后,摇身一变,小渔村成为庞大人群会聚的大城市,我们今天也前来踏访。这就是历史给我们呈现的节奏。我这次来到深圳,仿似领略一种音乐。
“我的诗既是台风也是微风”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了解台湾已故诗人周梦蝶吗?您跟这位“苦僧诗人”的诗歌有某种相似性,都具有纯净灵动、禅性悠远的特点。
高银:在遥远的古代阿尔泰山脉北部,中国的内陆地区,栖息着一群人,他们拥有很长的叙事诗,最短的一首也要吟上一周,最长的要吟颂半年才结束。这说明其实中国之前就已经拥有宏大的叙事诗,可惜他们没有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因此输给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这个古老的叙事传统,传到了东亚地区,于是东亚的诗人们,也创作了需要一周甚至需要半年才吟诵完的叙事诗。按西方的观点,叙事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不认同。生命需要漫长的时间维度,当然也需要一种短促的瞬间。因此我写两行的短诗,写几千行的长诗。自然界的风有多种,有台风,又有春天的微风。我是两栖者,不偏不倚,我的诗,既是台风也是微风。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诗歌中的悲悯情怀主要是来源于青年成长时期因战争而带来的不幸遭遇吗?
高银:我生活的那个惨烈时代,人无论降生在什么地方,似乎注定要遭遇血腥,绝望让人们看不见前路。地球这颗行星到处有惨淡记忆,那不单单是属于我的苦难。世界在遭受“痛”的时候,我也感受着“痛”。这种“痛”,我们不应单纯地承受,积存心底,我们要设法消解它,从中生成一种新的体悟和价值。我相信,无论是诅咒,还是怨恨,都能化解,转化为友情,我向往悲伤能够化为灿烂喜悦的时代,我企盼这个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过去曾经历经的悲剧,在今天不再仅仅是悲剧。当然,我也不会忘却那些记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所以,您的诗歌有光芒。
高银:对啊,我今生梦想光芒。我接受过很多采访,但这样的提问是第一次。一道光芒在上方,但并非绚烂刺目,是光而不辉,中国的古典诗歌非常推崇这种价值,我希望能够践行这种美学价值。佛教有一种说法,称之为“寂光”。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一生有很多“传奇”,比如十年入山为僧。我还是很好奇,当时这段佛门生活经历给您的诗歌创作带来哪些启蒙?
高银:我当年出家修行的禅寺,有个“三日庵”,意即到了这里住上三天,人就会开悟。但过了五天、十天,我还是没有明白什么,我在那里待了十年后下山。
我至今没有开悟,现在索性不想再悟了。我希望一直处于未开的迷蒙状态。如今全世界都推崇所谓的智慧,但我不推崇,我并不想入流,未知才是我的乌托邦,智慧不是。我的现在和未来都是幽暗,我向往的是那幽暗的处所,而不是光芒的处所。然而我也祈愿,希望偶尔有一缕光照进我的梦乡,因为我想确认这世上的某个地方是有光亮的。但这光芒不属于我。
韩国新诗和中国新诗同时起步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所以,您的诗歌中有众生,有万物。
高银:是啊,我的心怎么可能只存放自己呢?只存下自己的,就不是心了。我是岸,我的心是汹涌的大海。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追随自己的心,亦步亦趋,走出的轨迹,就是我的人生道路,而走着走着,它终将以搁浅终结的吧。这个世界是有边界的,如果没有边界,世界就可能是地狱了。每个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这个边界的存在。换句话说,我的明天即是死亡。但是谈论死亡,会使我的妻子女儿感到悲伤,想到这点确实令我哀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生命跨在某座山峰之上。如果抛开这一点,对我而言,生和死之间是没有边界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听闻您从小在私塾习识汉字,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谈谈您最喜欢中国哪些诗人吗?
高银:中国是公元6世纪发明了第一口洪钟的国家,当敲响钟的时候,它发出的声是两种音色,这钟声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从那时开始就爱上中国,说起来已经不止千年,我还要再爱上万年。
我喜欢的中国诗人能够数9个,一位是李白,我也喜欢李贺、苏轼,我喜欢吃东坡肉。而现代的郭沫若,先是激情的诗人,后来是很好的学者。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今年中国新诗正好走过了百年历程,您怎样看待中国新诗百年的发展?
高银:韩国新诗和中国新诗几乎同时起步,日本则是早了十来年。走入现代,我们付出了失去古代的代价。新诗与古典的纽带发生断裂。好在这个“失去”,并非一去不返。貌似割裂,其实古典已融入我们的血脉里头。我想也许50年之后,古典会重新崛起,古典的力量会重新复苏的。我相信,古典会和数码文明同在,共同前行。( 魏沛娜/文 金丹实/翻译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