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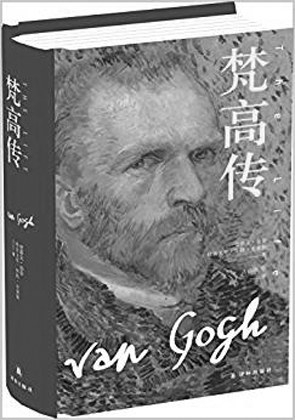
《梵高传》,[美]史蒂芬·奈菲、[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著,沈语冰等译,译林出版社出版,128.00元
读《梵高传》,会发现梵高的一生恰恰就是那样一个“是其所信”的过程。自爱上绘画开始,他的生命都只为了绘画这件事而燃烧。
史蒂芬·奈菲、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著的《梵高传》是一本充满了颠覆性的传记。接近900页的传记读下来,作为一个艺术的外行,我无法对其中的画作解读的部分作出评价,但对这本传记传递出的“梵高”新形象深感兴味:并非死于自杀而是他杀的梵高;不同于欧文·斯通写过的英雄主义色彩的梵高,也不同于民谣《Vincent》里唱过的那个充满神性的梵高;此外,《亲爱的提奥》虽然出自梵高之手,却无论如何只是梵高这一面的自白——《梵高传》最有价值的地方或在于,作者将梵高的生平、书信置于他的书信往来之流里去看待,因而给了我们一个更复杂也更血肉丰满的梵高。
读完这本传记,大概没有人会否认,除去“天才画家”的光环,生活中的梵高多多少少是一个古怪、自私、疯狂的人。尤其是在面对父亲多洛斯时,他几乎表现得像是一个十足的“逆子”。多洛斯无尽的付出,换来的是梵高的执拗和不知感恩,不断升级的争吵、咒骂将亲情的浓度不断稀释。多洛斯对这个儿子失望透顶,最后郁郁而终,梵高的妹妹直言不讳地说,“是文森特害死了自己的父亲。”我在读的时候想:如果我们普通人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个儿子或兄弟,我们还会不会像《Vin⁃cent》的歌词那样认为:“……thisworldwasnevermeantforone//asbeautifulasyou/”(这世界上不会再有什么//如你一般地美好)?这实在是很可疑的。
而从梵高与其弟弟提奥的关系方面去看待,这本传记显然是认为“提奥无私资助天才哥哥”故事的传奇性要大打折扣。在这个中产家庭里,提奥显然更符合父母与本阶层对他的期待。提奥从许多方面看都是梵高的反面:梵高“一意孤行”,提奥则懂得妥协;梵高无法适应社会,提奥则如鱼得水;梵高在家庭里是一个无度的索取者,提奥始终默默奉献……但即便委曲求全如提奥,对梵高也有厌烦的时候,这一点传记里写到好几处。提奥在梵高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他的疏远并非毫无原因。因为即便是对“亲爱的提奥”,梵高也并非坦诚相待,而是充满了疑虑和“算计”。该传记作者在书后的《资料来源说明》中指出:“他(文森特)利用敏感而棘手的问题作为要挟的利器:比如,威胁会采取一些影响兄弟情义或让家人尴尬的行为,从而迫使提奥拿出更多的钱;或者先主动提出某种不计后果的鲁莽做法,然后再将其弃之一边,这样来诱使提奥赞成他一直以来真正想做的事情……”“至少有那么几次,我们有非常具体的证据证实,文森特为他的信草拟了好几稿,有广泛的、基于合理推理的证据表明,这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尤其是当讨论的话题比较重要或敏感时。”
事实上,自结婚有了孩子之后,贫与病,梵高·文森特的索取……就不断折磨、压榨着提奥。某些时刻,看似牢固的兄弟情谊几乎是濒临破裂。在第三十七章《两条路》中,作者以精彩的叙事手法,一面叙述提奥兴高采烈打算与乔结婚,一面叙述梵高的一只耳朵被割下躺在医院的惨况,而提奥得知消息去探望,“在医院停留仅数小时之后”,提奥就离开了。这种对比式的场景切换,使人读了不由感慨梵高处境的孤独与悲凉。但由此也不难看出,提奥对于哥哥梵高长期以来的“压榨”“索取”,内心是极为不耐烦的。
毋庸置疑,考察梵高的一生,他无论是作为儿子,还是作为哥哥、朋友与情人……都谈不上通常所谓的承担与责任。他不是个孝顺的、尽责的儿子,也不是个体恤的哥哥,更非温柔、善解人意的情人……在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他的人生都绝对地以自我为中心,身边人若不能服从与成全,就只有对抗与牺牲。如他与妓女西恩的关系:起初他将西恩视为“一位天使”,认为她纯洁,温顺,甚至视她为“圣母玛利亚”,但很快又意识到她的“愚蠢”“粗俗”“心胸狭窄”……直到提奥以金钱威胁他——虽不乏些许道德上的自责,梵高还是最终与西恩分手。在这段关系中,可以看到梵高不仅容易将自己的主观认识强加于现实(从创作的角度,这甚至是一个优点,但不可否认,这对于“现实”本身并不公平),也没有能力对人对己负责。如他自己反省的:“我是害群之马,是一个品性恶劣的逃避责任者。”
通常人们认为梵高是一个圣徒式的画家,这不仅是由于他对于艺术的狂热献身,也由于他身上浓厚的布道情结——但是在传记作者看来,这种情结指向的并非是具体的他人,而是梵高自己内心的苦难体验。毋庸置疑,无论是《吃土豆的人》,还是《播种者》《沼泽中的两个女人》……在他那部分以底层人物为对象的画作里,都可以感受到梵高对“苦难”的某种情结。这看上去像是梵高具有某种今天所谓的“底层情结”与“底层关怀”。但是在《梵高传》中,作者指出:实际生活中,梵高并不能与“底层”和睦相处。如在矿区布道时,梵高认为矿工们“无知、缺乏教养、敏感多疑”。《梵高传》作者写道:“梵高对现实中身边的苦难熟视无睹,却对钟爱的书籍中描绘的受难景象饱含怜悯……他甚至承认自己更偏爱临摹书里或是画里受压迫的穷苦阶级,而不是现实中触手可及的劳苦大众。”这不禁使我想起在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读到的伊万对他弟弟阿辽沙讲的一番话:“我一向无法理解,怎么可能爱自己的邻人。依我看,恰恰对邻人是不可能爱的,只有对远一点的人或许还可能。……要爱一个人,必须让那个人躲起来;只要稍一露面——爱就没了。”梵高热爱苦难,但要说是热爱“邻人”,似乎只是世人的一种误解罢了。
由此,无论是从伦理角度考察梵高与家庭的关系,抑或是从绘画本身看待他对于“苦难”的理解,都极容易看到书中所呈现出的这个更复杂多面的梵高与我们熟知的那个梵高之间的差异。不仅使人要追问:是否艺术的本质就是一种粉饰?而“才华”可以抵消创作者在其它方面(性格乃至道德)的缺陷与问题?如普通读者今天很少会去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个不折不扣的赌徒;叔本华是个自负、暴躁、吝啬、自私的人;里尔克靠着不断写信取悦“有能力”的女性以获得生活接济;而奈保尔则虐待情妇、盼着妻子早死以娶新妇……更不会觉得他们的“问题”会令他们的成就失色。
从伦理角度去看待创作者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大概会陷入一个死胡同,毕竟作品被创作出来之后,就不再仅仅属于创作者本人。因此,不妨从存在论的角度去理解艺术的本质与创作者之间的关联——即便假定创作者的品性、本质关乎作品的品质,前提也是得存在一个恒定不变的品性/本质。然而,如存在主义哲学所认为的,“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就可以理解,通常所谓的“艺术粉饰现实”,或恰恰只是未臻最终“本真”状态的过程。也即在这种情形下,“粉饰”还未能够达到一种境界——将创作者整个地摄入到“成为”当中去,并且全身心地献给那个不断更新与确信着的生命追求。萨特有言:“由于我是我的可能,我是我所不是和不是我所是”;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艺如其人”,所谈论的无疑不应该是人或艺术的本质,而是人与艺术同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是其所信”。与“是其所信”相对的是“信其所是”。前者的“是”是“成为”,后面的“是”却是先验的认定。
读《梵高传》,会发现梵高的一生恰恰就是那样一个“是其所信”的过程。自爱上绘画开始,他的生命都只为了绘画这件事而燃烧。无论是贫、病,还是遭到亲人、朋友的打击与冷落,这个追求始终是压倒性的。但他无疑并没有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谁,而是通过不断摸索、大量练习,慢慢“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画家梵高。如果说,梵高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缺陷”乃至道德承担上的无能,并非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带有那么点“命定”(也即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性”)的意思;那么,他就是那种在“不可能”处努力寻求“可能”,而终归于“本真”的人。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难免要寻思:“是其所信”的人生,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不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对生活的牺牲,某些时候,也是对于“他者”的牺牲。牺牲亲情、爱情、友情……而去独自面对那个孤独的自我。人总是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人的自我完成如果是要用绝对的孤独去交换,那么无异于否弃了现实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因此,说梵高是一个“圣徒式的画家”并不为过,他是通过绘画而仰望、接近上帝的人。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具有宗教情怀、追求超越性的梵高,他也从未试图远离人群、拥抱绝对的孤独。相反,他几乎总是在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爱,而始终未能得到。他的绘画也好,文字也好,除去遗传的因素(梵高得的癫痫是遗传自家族病,提奥最终也进了精神病院),很大程度上就是此种“寻求”与“寻求不得”之间的落差、痛苦的表达。然而,如赫拉克利特所言,真正的和谐是一种“隐藏的和谐”,真正的和谐是通过挣扎、斗争才能获得的。实际上,通过绘画,梵高不仅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归于“本真”的方式,也是找到了一种与他者、世界联结的方式——通过绘画,他的孤独与苦难,已不再仅仅属于他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