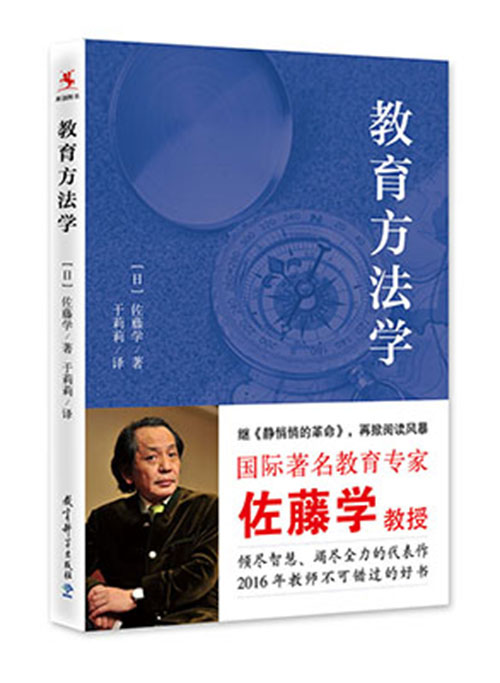 《教育方法学》 佐藤学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课程”究竟是什么呢?英美的“课程”这个词一般意味着“学习经验的总和”,是作为包括了教与学的活动、教与学的计划、实施与评价等所有环节的囊括性概念来使用的。 “课程”这个词源自古罗马战车竞赛的“跑道”一词,拉丁语的“跑(currere)”是其词源。原意为“跑道”的这个词,其后又衍生了“人生阅历”这一含义。即使在今天,英语中的“curriculum vitae”也不是指学校的课程而是指“履历书”。可以说,这种用法保留了作为人生阅历这一语义的使用痕迹。 “课程”这个词在宗教革命以后的大学教育中开始作为教育术语使用。其首次作为教育术语登场是在1582年荷兰的莱顿大学。当时宗教革命加强了教会与国王对大学的控制,因此教会与国王权力所控制的教育课程被揶揄为教授和学生们按照所定路线奔跑的赛马跑道,是包含着嘲弄和自嘲来使用“课程”这个词的。在“课程”这一术语中交织着“强制”这种语感,而这种语感是有一定历史根源的。 就这样,“课程”作为意指制度上所规定的学科课程的用语固定下来了,但是,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这个词实现了含义的转变。随着进步主义教育的成立与普及,教育行政所规定的教育内容与学校的教师所创造的教育内容被加以区别,教育行政所规定的教学大纲被称为“课程标准”,而把学校中由教师所创造,学生所经历、体验的教育内容的课程叫作“课程”。“学习经验的总和”这一“课程”定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可以说,“学习经验的总和”这一定义是将作为教育用语的“课程”与“课程”这一词的语源中“人生阅历”这一含义相结合后产生的概念。 在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经验与教育》等一连串著作中可以探寻到“学习经验的总和”这一概念的发展进程。杜威将教育定义为“经验的再构成”,但并不认为一切经验都是教育性的经验。杜威指出,在学校所组织的经验中既有促进儿童成长的“教育性经验”,也有同儿童的成长无关的“非教育性经验”,还有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反教育性经验”。杜威主张,学校所组织的经验,应当选择与学问性经验、校外的社会与产业、公共生活的伦理有连续性的经验。并指出,学校是通过保持与校外的社会、共同体间的连续性,来建构知性的、社会的、伦理的经验,从而成为肩负起为“民主主义社会”做准备这一使命的场所。而组织这种“教育性经验”(具有意义的经验),即是杜威所追求的“课程”。 作为“学习经验的总和”的“课程”概念,在20世纪 70年代后再次变得活跃起来。被称为“概念重建主义者”的教育学家们对“课程”进行了重新定义。他们对“过程—产出模型”的“课程”以生产性与效率性为基准,作为适应产业主义社会与消费社会的系统发挥作用进行了批判,并展开了基于学习者的经验重新界定课程的运动。在这个再定义运动中,“概念重建主义者”是以舒茨为首的现象社会学及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谱系的批判理论为理论基础。现象社会学揭示了日常生活现象是人们的主观集合意识所构成的现实,批判理论提出了阐明文化与社会意识的压抑和异化的现实,寻求批判意识觉醒的实践的主张。 “概念重建主义者”们都重新返回到“课程”的“学习经验”这一语源,发起了将已经被工程学化、技术化了的“课程”重新定义为人文性、社会性概念的挑战。例如,休伯纳是第一位倡导将课程现象作为师生的“个人日志(个人经验历程)”,用历史性的、社会性的、美学的、伦理性的语言加以描述的教育学家。休伯纳认为,课程在作为教育内容的程序及系统之前,是每个人在课堂中体验的、个性的、实存性的经验。并将“课程”设定为以“个人经历”经验为核心,包括了学科内容,还包含了教室空间构成与课时分配甚至学校建筑等全部学习环境的总括性概念。而主张以“自然的方法”推进课程实践与评价的麦克唐纳也认为,“课程”即是“学习经验”本身,主张应规避技术学、工程学意义上的开发与评价的人为性特征。 这样,过去作为“教学计划”用工程学、技术学的话语来表述的“课程”,现今转变为用政治学性、文学性、社会学性、美学语言对“学习经验”本身进行批评和创造的话语加以描述。“课程”这个词,正如其语源所示,是展现每一个个体经验轨迹的“学习经验的履历”。 但是,将“课程”概念完全解读为学生经验也是有一定片面性的。虽然课程问题的核心是每一名儿童的“学习经验”,但是,那些从制度上组织这种“学习经验”的教育课程的问题、有计划地组织教育内容的教学计划的问题、学校层面的教学计划与课程管理的问题,也还是与以往一样,都是需要具体审视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