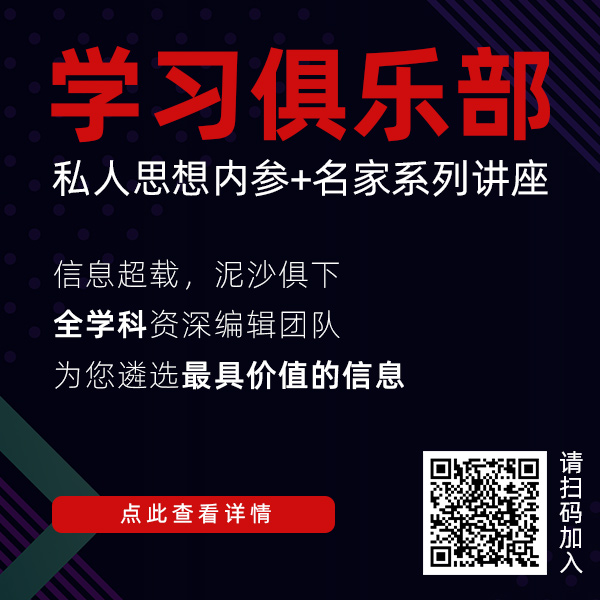 在朱复戡先生现存的一百多首诗词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白凤吟》《哀赤羽》和《雏雀吟》很值得注意。2006年,笔者曾撰《朱复戡先生的诗词》1一文,认为这三首古体诗“所选题材虽琐琐,内涵却很丰富”,“是朱老那段时间里感情生活的曲折反映”。当时限于篇幅和体例,未能展开论述,现再作此篇。 一 下面先把前两首诗录下,并略作疏解: 白凤吟(有序) 辛丑春节,欲登泰岱,不能携白凤俱,留之友家。友家一雄,纠纠昂昂,器宇不凡,洵良匹也。因赋白凤于归。 白凤出生东郊边,茕茕盈握啼宛啭。 江南词客独垂怜,愿掷杖钱易狷狷。 伶仃学步辞爹娘,不识亲生爹娘面。 缱绻相携来寒舍,殷勤抚育绕庭院。 呱呱待哺碎我心,今岁粮荒壑难填。 居停不饱尔亦饥,相对无言空馋涎! 忽忽丰满初长成,亭亭风姿立芳茜。 隔墙闻声谙謦欬,迎门跳舞学飞燕。 有事欲登泰岱颠,不能相扶上云殿。 无奈为尔谋归宿,堪欣雀屏已中选。 额手了却心中愿,成尔鹣鹣神仙眷。 今日于飞送于归,来朝螽斯庆螽衍。 凤兮凤兮得所栖,相忆何期重相见。 人生离合不胜情,万类悲欢徒依恋2! 序中的辛丑是1961年。据《朱复戡年表》3,他此年4月到泰安从事岱庙天贶殿宋代壁画的临摹和研究。故此序中的“欲登泰岱”,其实是说即将从济南移家泰安。“于归”语出《诗经》,指女子出嫁。 那应该是当年的春天,作者买回了这个弱小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产生了感情。但那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米珠薪桂,主人也难得一饱,哪儿有东西喂它?作者看着它饥饿的样子深感愧疚:“居停不饱尔亦饥,相对无言空馋涎”,两句写当时场面如在眼前,令人读后黯然神伤。 小鸡终于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丰满初长成”,是袭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在作者的心目中,这只雏鸡就是自己的女儿。它一身雪白的羽毛,高贵而纯洁;它风姿绰约,美丽而活泼地在草地上觅食,构成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他叫它白凤——白色的凤凰,他把它当成了家庭中的一员。白凤熟悉主人的声音,主人欣赏白凤的优美舞姿。他们之间甚至形成了心灵感应,主人的一声咳嗽,白凤就会立刻来到他的身边。 但人生聚合无常,他们要分别了。作者要到百里之外去另安新家,带白凤去显然并不现实。但他绝不忍心把它杀掉吃肉——别说在饥饿的年代,就是正常时期,这也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然而作者想都不会想。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她找一个漂亮的白马王子!他终于选中了朋友家一只漂亮的雄鸡——“雀屏中选”,正是选得佳婿的典故。对此他极为高兴,觉得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他把白凤送给人家,觉得就是送女儿出嫁,于是他郑重地写下这首可称为催妆诗的《白凤吟》,真诚祝福他的白凤婚姻幸福,早生贵子——“螽斯庆螽衍”也出自《诗经》,是祝颂子孙众多的意思。 他说:白凤啊,你现在总算有了归宿,但是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见面吗?在为你高兴的同时,我又是多么恋恋不舍!悲欢离合并非人类独有;万事万物都是情之所系,我的依恋也许是徒然的,但这真的令我无法承受啊! ——这就是《白凤吟》的内容。说白了,这诗写的就是把一只鸡送人的事。这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感情是真实的,决非无病呻吟。作者的“小题大作”,值得深入解读。 如果说《白凤吟》是个喜剧,《哀赤羽》就是一个悲剧。 哀赤羽(有序) 今岁得赤羽,号称“苏联红”,重达九斤。骁勇善斗,所向披靡;引吭一声,天下为白。餐以食,让诸雏;从不食,家中粟。山荆恶其晓啼惊梦,必欲宰之,甘其心快朶颐也,於戏忍已!诗以哀之。\r 去年送白凤,归途意悒悒。 凤去室兮空,环堵秋萧瑟。 今春来泰岱,触景念羽翼。 为慰寂寞情,到处托物色。 转辗得赤羽,纠昂殊英特。 晨唱满天红,昏栖两壁侧。 庭院战群雄,所向都败北。 引吭一高歌,闻风皆辟易。 出外护诸雏,归来让粟粒。 但饮西沟水,不吃东家食。 耿耿此丹心,未能邀欢悦, 天天复天天,忽忽逢生日。 山荆发逸兴,谓欲宴佳客, 怨其不生产,留之复何益! 更恶惊晓梦,恨之已切骨。 任性一快意,心肠硬如铁。 一举置俎上,顷刻双脚直。 嗟嗟一世雄,含冤抱恨卒! 江南呆书生,抢救已不及。 掷笔兴长叹,恻然泪欲滴。 诗开头先写失去白凤的郁郁不乐,用以衬托得到赤羽的兴奋。赤羽是一只气宇轩昂的大公鸡,它有一身漂亮的羽毛,威风凛凛,红冠金距,昂首阔步,雄视一切,像一个身披红色战袍的大将军。它每天以嘹亮的啼声驱散黑夜,迎来黎明;晚上它就安静地休息,绝不扰乱人们正常的生活。它勇敢无畏地捍卫正义,保护弱小,在这个院子里,任何企图挑战者在它面前都要丢盔卸甲,退避三舍。它还大公无私,勇于担当,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出外护诸雏,归来让粟粒。但饮西沟水,不吃东家食”——这里的“东家”在汉语中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主人家。那么“不吃东家食”就是为了节约主人的粮食,宁可自已在外觅食。也就是序中说的“从不食家中粟”。这在六十年代初期自然有特殊的意义。 读到这里,使人很自然地会想起汉代刘向在《新序》里所说的“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在朱复戡先生的笔下,赤羽岂止五德,它简直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圣贤和剑胆琴心的侠客。 然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女主人却对赤羽的诸多好处视若无睹,毫不欣赏。她所关注的只是它肥硕美味的胸脯和大腿上的肉!她要杀了它佐餐,以大快朵颐来庆贺自己的生日! 而且,她还有堂皇的理由:一是赤羽“不生产”,不会下蛋;二是它每天“惊晓梦”,影响了她的休息。真是欲置之罪,何患无辞。所以结局毫无悬念:“一举置俎上,顷刻双脚直。嗟嗟一世雄,含冤抱恨卒。” ——女主人当然不是一个残忍凶恶的人。谁都知道,饲养公鸡的目的就是吃它的肉,天经地义。赤羽被杀掉只是迟早的事,连制造罪名都没有必要,“含冤抱恨”更谈不到。 但是对作者而言,赤羽的死却是巨大的精神冲击。面对强势的女主人,他无任何道理可讲。除了洒一掬同情之泪和在诗中慨叹一番,他毫无办法。在《白凤吟》中,作者曾自称“江南词客”,那使人想起倜傥潇洒的名士;而在此诗中他自称是“江南呆书生”- -关键时刻毫无作为,他真正读懂了黄仲则名句:“百无一用是书生!”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美毁灭给你看,《哀赤羽》写的就是一个毁灭美的过程。作者欣赏美,礼赞美,却不能保护美,除了喊一声“于戏忍已”(啊,太残忍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二 《白凤吟》和《哀赤羽》,一个喜剧一个悲剧,堪称姊妹篇。朱复戡先生在相隔两年多的时间里写了这两首有关鸡的诗,使人诧异他对这种极普通的动物何以这样情有独钟;也使人想起古代文人的那些雅好,比方王羲之爱鹅,米颠爱石之类。但是,不能用文人的癖好来解释他对鸡的感情。鸡不是他心中的玩物,而是美好和圣洁的象征。在他的笔下,鸡是完全被人格化了的,具有人的情感和人的品质、操守。他对它们或者像对儿女一样温馨呵护,或者像对英雄一样景仰礼赞,以至一旦失去就万分依恋,悲愤不已。 朱复戡先生六十年代的爱鸡,应与他当时的人生际遇有关。 朱复戡先生在50岁以前可说是人生顺遂,事业成功。他幼有神童之誉,七岁在上海大世界作石鼓文对联,被康有为称为“天才”,吴昌硕许为“小畏友”。16岁出版印集,此后渐渐有盛名于当时中国艺术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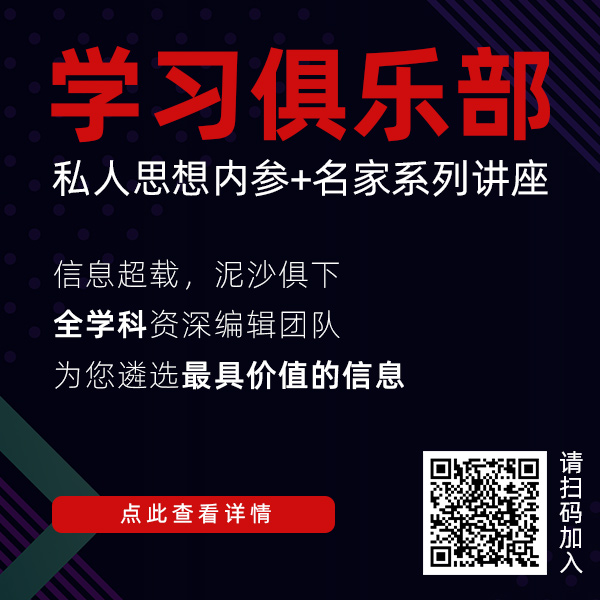 马公愚说他的篆刻是“别开蹊径,自成一家,实千年来一人而已”;张大千则说自己“漫游南北,数十年来所见近代名书画家……卓然开一代宗风者,唯朱君一人而已”。这些说法虽难免有溢美之嫌,也确可说明他的学术地位。 而关于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从他写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此前戴曾致信朱复戡,说蒋介石打算重用他,并劝他改一改年轻气盛的脾气。他的回信中说: 得书,承关念。知足下情,致感何可言。并殷殷以勿少年气盛相规劝,此良言也。但来书谓倘能改变作风蒋必重用,此何言也?!足下所谓作风,其实是我个性,个性天生,无法改造。足下曾记曩年大庆里时,静江、组安、庶堪、尔我常相集宴,当时有渠坐位否?乃一旦得志,便出狂语,安知五年后或无资格被我重用耶!削足适履,吾不为也4!…… 信中提到的“曩年”,是1921年前后,大庆里是张静江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住宅所在。张静江、谭延闿(组安)、杨庶堪,连同戴季陶,他们都在辛亥革命前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堪称是民国的元老级人物。朱复戡先生当时年甫弱冠,便以才智而被他们欣赏,成为忘年之交。而其时的蒋介石尚未发迹,大约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搞投机买卖。但八、九年后,即写此信时的1930年,蒋已是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海陆空三军总司令,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蒋为网罗人才而欲请朱复戡先生任政府秘书长,而他接信后不但没有表示感激涕零,反而在信中说出如此话语,充分显示出他辟易万夫兀傲不群的性格。 朱老的恩师是被称为近代浙江三杰之一的张美翊。张美翊发现年才十二岁的他天质非凡,着意培养,使他在文史金石书法诸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美翊一直认为,书法金石乃是技艺,如果没有道德学问的深广根基,技艺再好亦不过匠人而已。他致复戡先生信中屡说,“在家多看朱子《小学》第二册,以植做人根基。”“忽念少年人,得暇必须从事文学,使其志趣高尚,道德进步,庶免墮落。”“孝义忠悌礼义庸耻,八字万勿忘却”。等等5。综观朱老一生行迹,他确是达到了恩师所期望的“志趣高尚、道德进步、学问渊雅”的境界。所以,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书法篆刻界,朱复戡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圈内的艺术品评还是世俗社会的名声及润格,都已跻于上乘,甚至可称如日中天。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大事。朱复戡欣喜异常,称为“千古快事之一:数千年封建统治,到而今一脚踢翻。千古痛快事莫过于此!行见人民翻身,自己执政,我生何幸躬逢其盛!真所谓一跤跌进青云里,着实有点混陶陶也!”这几句随感,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感受,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啊!解放前夕,好友张大千曾邀?他一同出国,他以“中国的艺术活动应在中国,不宜在异域”为由而婉拒。但他一直醉心艺术心无旁鹜,对政治不感兴趣,解放后也没有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既没有到艺术院校做教授,也没到书画院专业搞创作,却阴差阳错地到了济南,成了展览馆的美术设计人员。 那是1958年,在全国上下大跃进的背景下,山东省政府要举办全省工业展览。因缺少相关人才,乃致函上海市文化局,商量借调几位美术设计人员到山东帮助工作。朱复戡先生时正赋闲,又向往齐鲁之邦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于是在文化局报了名。很快被批准,并由他为领队带数人到了济南。 到济南后,他除完成了工业展览馆的布展设计,还设计了农业展览馆,都获得很高的赞誉;又主持了全省中学美术教师及美术工作者的培训;又被请到北京军事博物馆搞主题性创作……省领导舒同、谭启龙等同志都对他十分重视。他所做的这些虽然也是美术工作,其实大多属于实用美术,与书法金石等纯传统艺术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他像绝大多数老知识分子一样,力图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不但沒有怨言,还表示出很高的兴趣。例如他曾写下《济南行》《四项指标大跃进》等诗,热情地讴歌当时形势。 两年后国家精简机构,展览馆停办,于是他被安排到省博物馆。他本是著名金石家,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成功考释了多件馆藏青铜器上的铭文。对他来说,博物馆是最理想的去处;而对省博物馆来说,他也是最急需的人才。然而却因当时名额控制甚严,他未能正式调入省博,于是他萌生了返回上海的想法。 为了留住朱复戡先生,省文化厅想出了一个办法:由省里提供一笔专用资金,让他带几个人到泰山下的岱庙去研究临摹壁画。省领导的意思是,这一临时性的工作既可以发挥他的专长,又使他未离开文化部门,待三两年后形势好转,还是可以正式调回省博物馆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进入文博单位的愿望终成子虚。他最后是以党外知名人士的名义,被安排到泰安市政协做了驻会委员6。直到退休,他都是政协的干部。 所以,在朱复戡先生看来,当时的他实际上已是被投闲置散。此时他年过花甲,身体多病,子女不在身边,多年故交也大半失去联系。更重要的是自己孜孜矻矻毕生追求的书法篆刻艺术,以及下过极大功夫的金石和古文字学问都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六十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学问即使还没成为应扫到垃圾堆里的毒草,至少也成为知音寥寥的阳春白雪。以他所达到的高深程度,在小小的泰安城也真难找到可供切磋的同道;所以,他此时的处境和心情,不但和当年在上海时无法同日而语,就是和来泰安之前的济南也不能相提并论。尽管作为省城下来的专家名人,人们尊敬他,领导也重视他,安排他住在赵尔巽故居赵家花园,在经济困难时期他的物质生活也得到特殊照顾,但他的内心却是十分空虛孤独的。在现实生活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他感到自己被抛到社会的边缘,除了偶然应人之托写写字刻刻印章外,他几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就这样索然地居住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小城,其心情的落漠可想而知。而他又是一个敏感多情的人,所以,白母鸡送人和红公鸡被杀,这样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会对他的心灵引起巨大震荡,使他投入大量的感情和笔墨。 这就是《白凤吟》和《哀赤羽》的创作背景。“翰墨难消真寂寞,幽衷频托小精灵”,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他当时精神状态的写照。 事实上,朱老并不是一个优柔脆弱的人。他的《咏泰山松》:“泰山有古松,探首望人龙;历尽千万劫,依然挺劲胸!”正是他精神气质的写照。他也不是一个热衷于名利和地位的人,这从他拒绝蒋介石的任命可以看出。他此时的孤独和寂寞,其实是在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失去专业追求之后的茫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那一代学人共有的精神状态。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此在文化艺术界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居住在泰安的朱老先生也适逢其会,那几年里他作为著名艺术家,多次被邀参加各种活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作题跋;参加在青岛举办点的全国名家国画交流展览会;赴哈尔滨参加黑龙江省文联和山东省文联合办的朱复戡、于希宁、陈维信作品联展,陆续为省美展、赴日本展等都提供了作品……那一段时间里,他精神愉快,创作热情空前高涨,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和自尊。 他作于1963年的《白头吟》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感情。这首七古长诗在回顾了自己的治学道路后说: 旧时未尝重艺人,艺人哪能免穷迫。 而今时代已变迁,百花齐放万民悦。 应将平生心得事,尽贡所学献祖国。 我为人人人为我,顿开茅塞天地阔7! 对党和国家的感激图报之情,溢于言表。 遗憾的是,大约从1964年的社教运动起,意识形态中“左”的倾向又开始出现,此后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把一切传统文化都视为“四旧”要彻底扫除打倒的“文化大革命”。 三 “文革”爆发后,朱复戡先生自然在劫难逃。他从赵家花园被赶到一个只有8平方米、潮湿阴暗的南屋里。南屋的下边是下水道,一到下雨,臭水就会溢上地面,而他居然还吟出过“临沟观泻瀑,枕壑听鸣湍”的句子,这充分表现了他为人的乐观豁达,随遇而安。十年“文革”中,除了运动初期的大批判,此后的大多数时候,朱老先生都是枯坐斗室,读书写字,与外界少有联系。 就是在这种生存环境中,他又写出了《雏雀吟》。 雏雀吟 院中落下小雏雀,毛羽未丰飞不得。 喂以粟浆紧闭嘴,看来离母难能活。 雏雀终夜哀哀鸣,母雀平明处处觅。 一见亲生在圉笼,跳来跳去无筹策。 天公不与慈禽便,大雨滂沱门外立。 遥对笼雏啼欲绝,满腔心事无从说。 忽然冒雨疾飞去,瞬霎衔来煎饼屑。 罔顾室中有主人,径趣笼口无惧色。 倥偬觅食倍艰辛,往返喂雏连旦夕。 一旦雏儿能自啄,两肩重负顿然释。 惶惶犹恐遭灾殃,刻刻难忘看羽翼。 笼内亭亭已长成,庭前跃跃示欢悦。 从兹一去竟茫茫,长使孤鸣空唧唧。 感叹飞禽骨肉情,哀思动我萱堂泣。 从知万类爹娘心,无不关心儿女切。 嗟我早丧白发亲,对之不觉青衫湿! 离娘雏雀渐依人,开出樊笼来座侧。 一指近前即跃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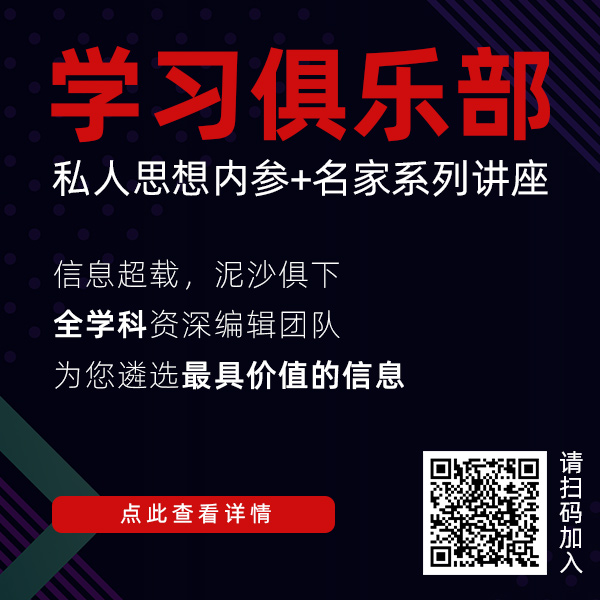 轻歌宛啭声凄恻。 翔空飞舞亦低徊,不落肩头便落膝。 小鸟依人两相欢,寒湿饥渴挂胸臆。 终朝相伴少亲朋,感尔病中慰寂寂。 春日悠悠夏日长,今年忽比往年热。 座如火炕汗如淋,室似蒸笼席似炙。 挥汗三更难入梦,开门一爽迎凉月。 凉风随月进纱窗,梦里浑忘门未阖。 寤寐忽闻坠物声,惊看弱肉被强食! 可怜小雀果猫腹,叹息祸福人莫测。 唯有小心重有失,但求无事不求吉。 如烟往事空长叹,堪笑书生何喋喋! 世路浮云到处同,春花秋月随时阅。 今朝母雀忽临门,四顾惘然意戚戚。 欲语无言相对看,锁魂咫尺黯然别。 回黄转绿等闲过,离合悲欢任所适。 几阵劲风吹落花,挥将箕帚扫黄叶。 但逢群雀集庭前,每兴遐思慈母忆。 人孰无娘我独哀,一生未解娘怜惜! 而今垂老得温馨,深感国恩雨露泽。 无限春光无限暖,思亲何似思红日! 诗一开头写作者发现了一只偶然从巢中掉下来的雏雀儿:它毛羽还没长全,不会飞,喂它东西也不吃,但作者还是把它捡起来放在笼子里。在“雏雀终夜哀哀鸣”的时候,母雀终于找到了它。母雀见到雏雀,又高兴又痛苦,它激动地跳上跳下,仿佛有千言万语却无法表达。这时天正下着滂沱大雨,它箭一样地飞到雨中为雏雀觅食,完全不顾风雨和室中有人的危险。经过母雀的精心饲养,雏雀终于渐渐恢复了健康。 小麻雀渐渐长大,母雀也来得少了,也许是它还要照顾其它孩子?小麻雀常常对空鸣叫,作者认为那是它在想念母亲。看到这些,作者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儿女。有时候会感伤得潸然泪落:“感叹飞禽骨肉情,哀思动我萱堂泣。从知万类爹娘心,无不关心儿女切。嗟我早丧白发亲,对之不觉青衫湿!” ——朱老现存作品中有两首以思亲为题材的诗,都写于1975年。《勉儿女》说:“吾既有儿复有女,如何冷落膝前清?只缘久作他乡客,未得常溫骨肉情。愿尔齐心挥力量,应须为国献生平。老夫虽耄不甘弱,争取犹思上北京。”《七十五岁生日》说:“行年七十五,犹作异乡人。生日自陶醉,举头星拱宸。芳邻惠寿面,盛意祝长春。遥望诸儿息,同心共此辰。”--后一首自咏自叹,真实感人;前一首现在看未免有矫情之嫌,其实也是当时的真实想法。从两首诗中我们不难读出作者内心的痛苦:生日本是亲人相聚的时候,但他这已七十五岁高龄的老翁,却孤身在外,连寿面都是邻居送来的。他夜不能寐,仰望浩渺天宇,唯见星辰闪烁。亲人不得见,未来不可期,此情此境,怎能不令他伤感? 这两首诗虽然写于其后,但对于理解《雏雀吟》的创作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如前文所述,寂寞和孤独是贯穿朱老这一人生阶段的基本情绪,他渴望亲情和友情,却因种种原因难以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感情放在这弱小的麻雀儿身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离娘雏雀渐依人,开出樊笼来座侧。一指近前即跃登,轻歌宛啭声凄侧。翔空飞舞亦低徊,不落肩头便落膝。小鸟依人两相欢,寒湿饥渴挂胸臆。终朝相伴少亲朋,感尔病中慰寂寂。”这一段写得如此真实细腻,平白如话,不须要再作解释,他和雏雀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已恍然如在目前。世上饲养鸟雀者多矣,饲养麻雀者还不多见;常被饲养的鹦鹉、八哥、画眉、百灵之类,或取其鸣叫宛转悦耳,或取其色彩艳丽悦目,或取其善学人语……这些优点麻雀都不具备。麻雀实在太平凡甚至太卑微了,但是它在作者最需要的时候偶然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这个不起眼的小生灵竟成为作者精神的寄托。填补了他感情的空虚,排解他了漫漫长夜的孤独,抚慰了他心灵和肉体的伤痛。 但是悲剧却又在不经意间忽然发生,可爱的雏雀竟葬身猫腹! 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天太热而未关屋门,给天敌留下可乘之机。作者住的那个低矮南屋,夏天的闷热可想而知。他有一首题为《苦夏》的诗,就是在那屋子里写的。其中说“气候高过量体表,汗珠湿透浑衣裳。饮茶解渴渴难止,挥扇取风风不凉”,正可以和本诗中的“座如火炕汗如淋,室似蒸笼席似炙。挥汗三更难入梦,开门一爽迎凉月”相互发明。屋这么小,天这么热,他怎能关上门睡觉?所以,那可怜的雏雀成为猫的盘中餐也实属事之必然。 小麻雀的死令作者深为感慨。他从祸福的难测,联系到自己的人生,六十多年的往事浮上心头,得出的结论是“唯有小心重有失,但求无事不求吉”——收拾起以往书生意气吧,甘心做一个谨小慎微的庸人,以静看世路浮云,等闲春花秋月来打发余生……可以说,一只雏雀的死,令作者产生了浓重的悲观情绪。 这个关于麻雀的故事本来已经结束,但事情总是一波三折,高潮又起。有一天,作者忽然发现那只久违了的母雀又来了!它东张西望,分明是来寻找孩子;它四顾惘然,发现孩子不见了。它难道有心灵感应的超自然能力,知道雏雀已不在世间了吗?看着它的黯然神伤,作者深受感动。麻雀虽小,它一样是有情感的,它们的用情之专一点也不亚于人类,甚或过之!即使回黄转绿,时间流逝,那感情永远也不会消失!从此以后,作者每当看到院子里成群的麻雀,就会想起这对麻雀母子,进而想起自己早已去世的母亲。发出“人孰无娘我独哀,一生未解娘怜惜”的嗟叹。 到此为止,这诗以七十多句的篇幅,不避繁琐地描写这只雏雀的生和死,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母之情。细致宛转,笔触含情,哀婉动人,可以说已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但作者意犹未尽,他最后又把母爱的主题进行了升华,写出了“而今垂老得温馨,深感国恩雨露泽。无限春光无限暖,思亲何似思红日!”作为结束。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也许会被认为是贴政治标签。其实对此应作具体的分析。一方面,在当时母爱是一个写作禁区,那时候主流的理论是一切爱都是有阶级性的,单纯宣扬母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应被批判。另一方面,这也表示朱复戡先生是真诚地相信服膺这套理论的。他要自觉地运用当时的理论武装自己,不断改造思想。这其实是当时绝大多数老知识分子的真实想法。这从上引《白头引》等诗中也可看出来8。 四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过,“诗人的思想和情感是分不开的,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人的感情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重要9。”这句话,也适用于对朱老这三首诗的解读。 前文曾对朱老六十年代初的孤独寂寞作过分析。在“文革”初期他创作《雏雀吟》的时候,这种孤独寂寞依然存在,并且还又增加了恐惧和迷茫,是对未来不可知的那种恐惧和迷茫。 在十里洋场生活了大半生的朱复戡先生,社会交往十分复杂。除文化艺术界名流学者外,从国民政府的高官,到青洪帮大佬;从前清的遗老遗少,到工商巨子、金融大亨,其中都有他的师长或朋友。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也相当复杂,他曾与帮派有很深关系,也曾参与证券交易所经商,又曾赴法国留学,在抗战时甚至一度成为劫匪金龙章的座上客。他的这些交游和经历,如果被那些或单纯无知或别有用心的红卫兵、造反派了解其中一小部分,他也许就会被关进监狱,被整得个死去活来。然而没有。即使在最混乱最疯狂的时候,他所得的罪名也不过是反动学术权威;他在那十年里经受的打击,与曾经的挚友徐朗西、李徵五他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揆其原因,实在是得益于他较早离开了上海和省城,离开了文化界和学术圈子,成了一个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由之身。这真是应了因祸得福那句俗话。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无法预测未来的。也许明天就会有人揭发他的“历史问题”,也许某个被整的人会牵连到他……,他性格中的豁达和乐观固然可以使他保持镇定平静,但如果说他的内心深处毫无恐惧忧虑,恐怕也不是事实。 ?1967年的夏天,正是社会上形势十分混乱的时候。这年六月六日,中央发出七条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10”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只雏雀的故事正是发生在此时。孤寂茫然中的朱先生从这件小事中得到灵感;或者说,他从雏雀的故事中发现,人的生命其实和那只雏雀没有什么不同,生存中有各种无法预测和防范的偶然性,到处都充满危险,可能在困境中被救起,也可能无意中葬身猫腹丢掉生命。在他亲眼目睹的这个过程中,最使他感动的是爱,母亲对子女那种不顾一切的爱。这种爱是不求回报的,毫无功利性,完全出自本能。这令作者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已的母亲。这,就是《雏雀吟》产生的过程。 相对于《白凤吟》和《哀赤羽》,《雏雀吟》的描写更加细致,叙述更有溫情。前两者有如童话和寓言般单纯明净,后者则更像一篇叙事诗或复调音乐,细节丰富,层次鲜明,步步推进,最后达到高潮。读《雏雀吟》,更容易体会到作者那颗敏感纤弱充满了爱又饱受伤痛的心。 朱复戡先生以他的真性情感染了读者。 真情,而不是矫情,是判别文学作品优劣的绝对标准。《文心雕龙》说,“人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朱先生写这三首诗,正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 朱老本来就是个天真烂漫的人。如前引致戴季陶信中的话:“足下所谓作风,其实是我个性,个性天生,无法改造!”再如前引对新中国建立时所说“千古痛快事莫过于此!”的欢呼,都是快人快语,其内心肺腑洞然可见。他的这种性格此生一以贯之。来山东前参加上海市文化局主办的美术工作者学习班以及各种活动,他发言往往随情任意,从不懂得考虑领导的好恶,虽然事后看那些发言大都是正确的,他还是得到了“不靠拢领导”,“善于诡辩”,“与政府讨价还价”等不好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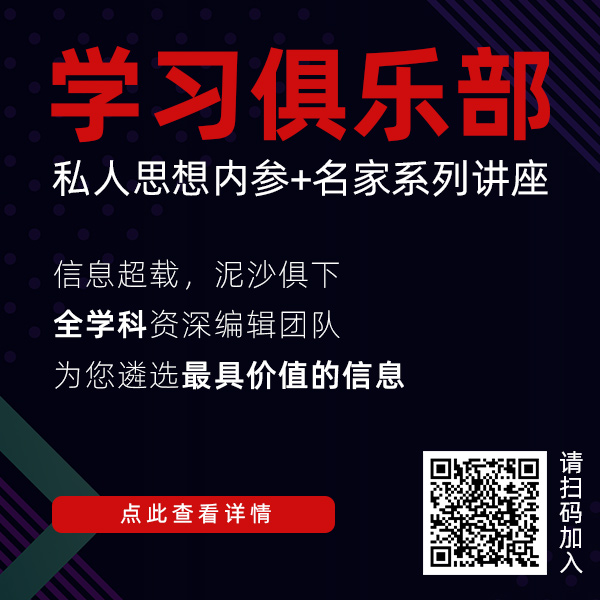 也成了他未能进入画院的原因。到泰安临摩天贶殿壁画,领导的本意是慢慢来,以待裁员高潮过去好安排他去博物馆,可他先是认为这壁画根本没有临摩复制的价值,后来勉强同意了,又不会慢腾腾磨洋工,以致领导都“暗笑他是个不知高低的江南呆书生”11。从这些事例上看,朱老确实没有通常世俗所谓的处世经验,书生气太浓。 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却是没有什么比真性情更重要的了。 但朱老又堪称是通古今之变的智者。他深知在时代巨变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未必都能尽如所愿。自己所能做的只能是知其雄,守其雌,静默以待。所以他既沒有怨天尤人,也没颓丧自废,而是像古代隐士那样的超然澹泊。偶有所感发之为诗,也不激不励,含蓄隽永,深得古人所说的温柔敦厚、哀而不怨之旨。《白凤吟》《哀赤羽》和《雏雀吟》就是这样。 如前所述,三首诗中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是缘于背后深厚的社会背景。而这些背景在诗中并没有作任何具体的表达。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今天的读者,能够通过相关资料了解作者的思想、态度,从而引起共鸣;如果抛开这些资料,人们还会被感染吗? 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好的作品从来都是以其本身的思想感情、形象意象、语言文字等要素征服读者。正如李商隐有很多作品曾引起后人对背景的种种猜测,千百年而无定论;但并不影响其诗本身的价值。《白凤吟》中那种儿童般的天真,《哀赤羽》里对美被毀灭的痛心疾首和无奈,《雏雀吟》对弱小生命的珍惜宝爱中所体现的对爱的咏叹礼赞,本身就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综上所述,朱复戡先生的这三首诗,以朴素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他处于孤独寂寞中的的喜怒哀乐。感人至深,是他丰富内心世界的外化,也是特殊历史时期不可多得的文学佳作。 朱老是幸运的,他终于迎来了河清海晏的新时代,在耄耋之年再创了事业的辉煌,十几年中积累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年虽迈却毫无衰颓之气,一大批书法、篆刻以及器物造型作品,整体风格愈加苍厚雄强。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 朱老无论是学养还是天质,都堪称人中龙凤。他韬光隐晦时期的人生经历,以及偶然触发而写出了这足以传世的杰作,实为理之必然。其价值和意义,一点也不亚于金石书法作品。 现在是各种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快餐文化空前发达的背景下,现代人几乎丧失了对古典趣味从容品读的能力,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简单粗陋,越来越功利化。现代人习惯了对作者按身份归类,习惯了格式化的思维方式,致使朱老(以及其他老派文人)的作品越来越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得不到欣赏和共鸣。这是令人遗憾的。 谨为此文,以纪念朱复戡先生诞生120周年。并希望以此微弱的声音,唤起社会对朱老诗作的关注。 注释: 1载《朱复戡艺术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出版。 2本文引朱复戡诗文,均见《朱复戡墨迹遗存·行草诗词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海岳双栖·朱复戡诗文选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出版。 3石羽、旷铗编,见上揭《朱复戡艺术研究论文集》。 4?手迹见《朱复戡墨迹遗存·行草书札卷》,3页。 5见《菉绮阁课徒书牍》各篇,笔者整理点注本。载《新美域》专刊,2008年出版。 6以上朱老生平参考侯学书《铁笔神童朱复戡传》,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出版。 7《白头吟》一诗,侯学书《铁笔神童朱复戡传》谓作于1963年。按,现在能见到的此诗先生手写稿至少有两种,文后自署一作“乙丑盛夏录旧作”,一作“己未冬录旧作”。乙丑是1985年,己未是1979年,皆云“旧作”,何时之作并未说明。而《海岳双栖-朱复戡诗文选集》此诗后编者注云:“此诗创作于1982年冬,1985年炎夏作了修改补充”,令人不解。今取侯说。 8笔者有机会见到一些朱复戡诗稿的复印件,发现现在印在书上的《雏雀吟》并不完整,后边还有二十多句被删掉了。编者这样处理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把删除部分抄在下边:“辉煌红日照心怀,灿烂宝书当镜尺。教诲谆谆明大义,恍知耿耿为民益。做人却是为他人,消极应须化积极。思想一通累赘除,结症累载一朝失。群英多助起沉疴,万寿无疆毛主席。病起出门策杖看,焕然万象人间易。神州建设向繁荣,世界人犹被压迫。念母哀雏微小事,疾风暴雨正蓬勃。惊看地覆天能翻,深愧心余力不及。但愿紧跟毛主席,口诛笔伐讨公敌。”按,这其中有“念母哀雏”四字,正是《雏雀吟》一诗的主旨。但作者认为这是“微小事”,即相对于国家、革命之类宏大叙事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又续写了这二十多句。我们今天用正常的标准看,这已经不是诗,只是押韵的口号,整齐化了的套话空话;但是不能否定,作者在当时是真诚的。只能认为这是时代的烙印。 9见《诗论》第十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2001年出版,204页。 10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154页。 11《铁笔神童朱复戡传》,82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