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高小宝的熊时代》 高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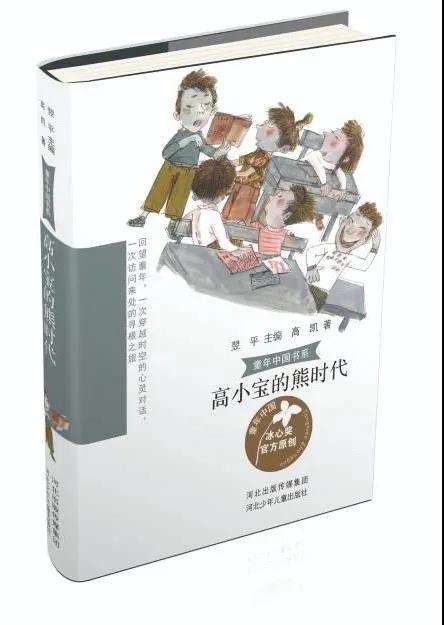 《高小宝的熊时代》 高小宝是小时候的我,去年在《高小宝的熊时代》一书里突然复活了。 该书出版以来,出版人一直在急切地为它寻找着更多的读者朋友。作为该书的作者和高小宝的原型,我比出版人还要急切。 失去的童年时代,对于接近耳顺之年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时光;尽管那是一个让“熊孩子”高小宝伤怀的灰暗年代,但因为其异常美好而让我流连忘返。 一个人只有老了,才会相信一些事情真的会一去不复返。我没有错过童年,也没有辜负童年,但我是长大之后才认识的童年。在回望童年的心路历程中,我不相信一个人的肉身会返老还童,但我相信一个人的精神是可以回归童年的。 其实,那些看似流逝的童年都在一个叫记忆的时空里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远去而非逝去。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条蜿蜒而来的河流,有下游,同时必然有中游和上游;下游存在,中游和上游必然也同时存在。一个人只要记忆之河没有断流,生命的河床就会涌动滔滔不息的波浪。 在一条生命之河的奔流中,我一直领着高小宝,或者说高小宝一直跟着我。也可以说,高小宝既像我的小伙伴又像我的一个孩子。也许,这才是童心未泯,这才是真正的返老还童。我的童年以人生记忆和文学记忆两种方式同时存在。一方面,我的童年是一根甩不掉的尾巴,仍然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说儿童时代是我的文学胎衣,那么关于童年的书写则是一根让我赖以活着的精神脐带。 我的“儿童文学”创作轨迹是这样的:发现童年,始于对童年的阅读;回顾童年,始于对童年的书写。而且,在人生的旅途中,因为前面的路都是黑的,唯有来路能看清楚,所以我的文学之路一直是瞻前顾后的。向前走,虽然心思重重,但背靠童年;向后看,尽管风雨兼程,但面朝童年。也就是说,童年是我的本来也是我的未来,而高小宝是我的全部。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此,我们这些经历沧海的书写者,时至今日只有暮年美好的回忆而无年轻时奢侈的向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也在书写童年,但我书写的是从前高小宝的童年经历,而不是当下任何一个孩子的生活。我一直以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我的“儿童的文学”才能老少咸宜。 这里,我必须挑明我对“儿童文学”一些固执的看法。实话说吧,我只承认“儿童的文学”,而不承认“儿童文学”。前者,首先强调的是文学,而由一个定语形成的偏正词组则明确了其主体必须是“儿童的”;后者,只是一个粗放的类别概念,适合文学评论家来理论,在个体的文学实践中并无意义。我不是在咬文嚼字,而是试图在细微之处厘清这样一个认识:在“儿童的文学”中,儿童与作者是同一个个体,作者是“儿童的”代言人;而在“儿童文学”认识领域,因为忽视了儿童的本位,作者与儿童则不存在这样一层至关重要的“血缘关系”。二者的区别从阅读作品时的口感和质感就能分辨出来。换言之,文学与儿童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DNA”是甄别“儿童的文学”和“儿童文学”的重要条件。和大家一样,我当然也赞成成人去为儿童写作,但成人必须写自己曾经的童年,把自己的童年告诉今天的孩子,而不是代替今天的孩子去思考和写作。这是因为,在当下的童年里,我们只有观察的权利,而没有体验的可能。常识告诉我们,只有来自切身体验富含情感的书写才是文学,凭借观察而无生命感受的浮面写作不是文学。 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所谓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内,所有的人必须按照生命的定律长大,而且长大后必须离开今天孩子的童年,把不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让出来,让童年真正的主人自己去创造自己的文学,让他们自己造就自己的作家。作家们需要做的,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细心周到地去做生活陪护或精神引领,创作、发现或者推荐优秀的文学,而不是格格不入地参与其中,把成人的那些伪幼稚伪天真伪幻想等强加给未成年人。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我们把儿童的本真还给“儿童的文学”,而且只有把我们自己曾经的童年呈现出来才能实现这一目的。我坚持认为,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守在自己的童年,即使是误入孩子的世界,做一个传播快乐的“圣诞老人”或一个“故事爷爷”足矣;真正的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世界同龄人之间或者成人童心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灵犀感应和精神传递。 一些人也许不相信,在现实生活中,我和儿子之间已经沟壑纵横,而我和高小宝之间至今没有一点“代沟”。我已经发现,儿子后来的叛逆行为甚至远走高飞,与当初我野蛮地闯入儿子的童年有关。我现在才知道,因为接受了圣神的天赋,一个人的童年是不可侵犯的,儿子的童年如此,高小宝的童年也是如此。要知道,儿童时代尽管是懵懂无知的,但却保存着一个人最率真的天性,圣洁而又坚硬,而这也是“儿童的文学”最根本的要素。 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孩子,优秀的“儿童的文学”,应该是品质和意义俱佳的精神来源。只要是健康有益的,“儿童的文学”对于他们就是一面镜子,甚至是童话里那一面神奇的魔镜,他们自然会从中看见许多获得许多。我们可以怀疑孩子的创造力,但不能怀疑孩子的模仿能力,即使是隔代的孩子,他们彼此之间也比和身边的成人之间亲近。模仿能力是创造能力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但要相信孩子,还要向孩子致敬。 需要申明的是,我绝对不否认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但优秀的儿童文学必须是高于教材的,而不是等同或低于教材;优秀的文学,的确应该是教科书,但必须是心灵的教科书。 不承认存在“儿童文学”,当然也否认“儿童文学作家”的存在。殊不知,在儿童文学的原野上,许多“儿童文学作家”都是没有灵魂的“稻草人”,一些已经老气横秋但却装模作样充当“儿童文学作家”的人总是让人心存疑惑,当然也包括那些在别人的童年赖着不走甚至不愿长大的青春型写作者。这些人精神可嘉,但其作为不敢恭维。 对于孩子,“老顽童”的文学,即使是仿真的,也不过是玩具而已。因为这一认知,我庆幸自己迄今为止没有误入歧途,没有困守“儿童文学”这一狭隘的文化区域。在我看来,文学就是文学,作家就是作家,根本没有其他妥协之说。而且,在吸收中外优秀儿童文学营养上我一直保持着警惕,对身边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边亲近一边疏离,乃至于在非常浮躁而功利的儿童文学界形单影只独享寂寞。因为这一原因,我的处境一直很是尴尬。在诗歌圈子,有人说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而在儿童文学圈子,有人又把我排除在“儿童文学”领域之外。我当然没有被悬空,而是脚踏实地。当童心成为精神坐标,我也非不伦不类,而是定力自在。对于以上两种看法,我都欣然接受,因为他们都是在肯定我:前者在说这老家伙还有童心,后者在夸这小子长大了。总之,我的童年书写,是我的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高小宝一直紧跟着我,但我绝对不想再回到小学校园甚或幼儿园里去。这是因为,童心绝非儿童文学的专利,而是人类一切艺术创造的根基和动力;“儿童的文学”也非儿童的专利,而是一个成人保持精神健康的营养大餐。总之,“儿童的文学”不是咿呀学语,而是一种“童言无忌”天真烂漫的童真言说。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去模仿伪造当下孩子的童年,只会再现自己曾经的童年。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但我在努力去成为优秀。在从一个孩子成为大人的过程中,大人们都是这样鼓励我的,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和高小宝。 本来,我是一个只写不说的人,但因为要完成这篇重要的约稿,我只好放开说了,不但说了,说的还都是一肚子真话。这也是“童言无忌”嘛,对事不对人,如果真说错了,权当是胡说八道。好在我不是在误导孩子,而是在甄别作家。也许,我所说的理论只适合指导我一个人的写作。 2019年9月,由翌平先生担纲主编并由河北少儿出版社一揽子推出的10卷“童年中国书系”,就是基于对“儿童文学”的一种新认知而集结起来的一个有难度的创意组合。荣幸的是,《高小宝的熊时代》不仅忝列其中,还得到编者的格外青睐。因为字数不多,书小小的轻轻的也厚厚的胖乎乎的,让人爱不释手。在我的个人著作中,其装帧设计是我迄今最喜欢的一本。让我更为高兴的是,英籍华裔作家张怀存还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已经将其翻译成了英文,年底将在伦敦出版。“熊孩子”高小宝带着我第一次远渡重洋,别提我有多高兴啦。 在这本由随笔和诗歌融合而成的童年自传中,我通过高小宝真实的童年故事,真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儿童的文学”和儿童时代的理解。诗教就是美育,是让我们引以为荣的文化传统。在《高小宝的熊时代》中,诗歌里的故事和故事里的诗歌,都是“熊孩子”高小宝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可以说,我把高小宝做过的坏事都写了进去。当然,这并非是一本坏书,而是一本老少咸宜开卷有益的好书。老者如我者可以看到自己远去的童年,而少者如高小宝者在成长的迷途中可以凭此辨识人生的路径。我坦诚地告诉读者,我对此书很自信,因为做坏事的高小宝后来没有成为坏人,相信读了它的人肯定也不会变坏。其实,我在这里推荐的不是一本书,而是在推荐一个人——我自己。 在这个“童年中国书系”的作者队列中,我欣喜地看到,还有人和我走在一条路上,大家和我有着相似的童年探险,彼此保持着同样的精神呼应。 不仅是在我们东方,在最近的阅读中,我意外地拾到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句话:“一个作家,绝不会与童年一刀两断。他会从中汲取一切。” 这位与我不期而遇的大作家,无意之间为我的观点做了精准的佐证。对这句箴言,我笃信不疑:一个作家果真如此,那无疑是自己斩断了自己的精神脐带。 起码,我和高小宝永远不会一刀两断。 (作者简介:高凯,1963年生,甘肃省合水县人。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甘肃省文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心灵的乡村》《纸茫茫》《乡愁时代》《高凯诗选》《童年书》《高小宝的熊时代》《拔河兮》《战石油》诗歌、随笔和报告文学十余部。诗文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甘肃省文艺突出贡献奖、敦煌文艺奖、首届闻一多诗歌大奖及《飞天》《芳草》《作品》《莽原》《大河》《六盘山》等刊物奖。)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