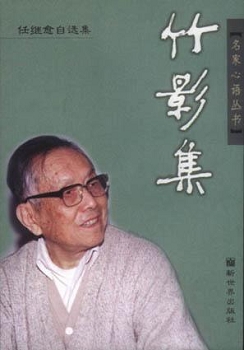 《竹影集》 任继愈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任继愈先生去世前后,我正在读他的随笔《竹影集》。据说,他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凤毛麟角”,这是就他的学问说的。受到过伟大领袖如此高评价的人文学者,也确实是凤毛麟角。据我所知,大概可与史学大师陈垣先后媲美,后者也曾被毛公钦定为“国宝”。对任公的学问,笔者虽对其“儒教说”,期期不以为然,却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这里,且就《竹影集》说点读后感。 《竹影集》书末收入他给女儿的信,家信最见真性情,其中1996年的一封信说: 近年来很多人吹捧某某专家,说他的学问高明,此人学有专长,应受到尊重。如果把他捧上天,奉为学习的楷模,后人无法逾越,这就过头了。此人有弱点,情绪不健康,缺乏刚健之气。此种专家不可没有,不能太多。好像一只秋天的蟋蟀,只发叹息,而不相信秋去春来。就这一点看,他的历史没有学透。 任公所说“学有专长”的“此人”,在家书底本中应该直书其名的,但公开出来有所不宜,便将真名隐去,而代以“某某专家”。那么,他究竟是谁呢?这是令人颇感兴味的。而够得上信里所说的“把他捧上天”,以至“后人无法逾越”等条件,大概也就钱锺书与陈寅恪(季羡林当时似乎还没捧到如此高度)。但据我的揣想与考证,不可能是钱锺书,而只能是陈寅恪。 1995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顿时把陈寅恪从窄小的史学冷圈子推向了大众的阅读圈,以致当时大陆的读书界与学术界大有“开谈不说陈寅恪,读尽诗书亦枉然”的味道。要说“吹捧”,陆键东此书继台湾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之后确有推毂扬波之功。 但仅仅举证“吹捧”的大环境,似乎还不能坐实任公所说的就是陈寅恪。好在有他的其他文章为旁证。《竹影集》里有一篇2000年回忆刘大年的文章,题为《史学家的品格》,有一段说到对陈氏的评价: 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陈寅恪,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尊重,晚年双目失明,在极左思潮笼罩下,心情悒郁,写成《柳如是别传》。刘大年同志充分肯定了陈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用几十万字考订柳如是的生活细节,此种研究方向不值得提倡。对陈寅恪一片赞扬声中,能提出此种评论,不啻一付清凉剂,难能可贵。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治学谨严,目空千古,一生服膺司马温公。司马光关心治道,主编《资治通鉴》。如能起温公于地下,《柳如是别传》必不会得到温公认同。 作为一个史学家,刘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之坚定,是众所周知的,任公的回忆文章强调的也正是这点。因而,任公借逝者之口对陈寅恪史学的褒贬,不啻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只消对读上引两段文字,这点不言自明。而“心情悒郁”,也是能与“情绪不健康,缺乏刚健之气”云云互为疏证的。区别仅仅在于,家信可以说得更坦率直白,更带情绪化,而公开的文章则措辞委婉,略带学理化。但任公家信中说的那只“只发叹息”的“秋天的蟋蟀”,指的是陈寅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有趣的是,《竹影集》还收入了任公为王永兴先生《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所作的序言。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的入室弟子,他自己说过“师从陈寅恪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弘扬光大乃师的学术也可谓不遗余力。他尽管年逾古稀,却不知老之将至,仍奋力撰述《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达四十余万言,这是他最后的专著,说成绝笔也不为过。他十分看重这部著作自不待言,特请任公作序,自然有借助其盛名的良苦用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