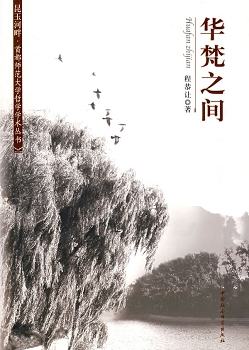 《华梵之间》 程恭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一版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学者在评论历史事件的时候,心口稍失检束,就容易发出一些“想当然耳”的言论,以思想上的“理当如是”,取代学术上的“事实如此”,以至于造成“一言而蔽千古不齐之事实”。自从“口述历史”、“访谈录”等类撰史形式流行之后,这个问题有往深处发展的趋势,虽研究有素发言谨慎的学者,也难以彻底戒除。苏晋仁、程恭让两位先生整理出版的周叔迦(1899-1970)遗作《清代佛教史料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0月第一版),收有一篇《纪念一代佛教文史大家周叔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苏晋仁先生访谈录》。这篇访谈录近已收进程恭让先生的论文集《华梵之间》(第207-233页),其内容固然十分丰富,却也难免杂染时代风气,掺入某些“想当然耳”之论。请看下面这两段话: 苏:当时三个以佛学研究著称的佛教居士中,竟无先生、清净居士二位似乎都未注意到敦煌卷子,唯有叔迦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成了日后中国佛教敦煌学方面的一位先驱者。之所以有这种区别,我想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学术兴趣十分广泛的缘故。当时他住在北京,敦煌残卷的大宗是在北京图书馆,而叔迦先生和负责整理残卷的陈援庵、赵万里等先生又很熟悉,所以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环境给了他这些机会。 程:除了您所讲的这些主观、客观方面的条件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深层的方面,叔迦先生个人对佛教思想史的看法可能影响了他对敦煌卷子价值的判断。比方说吧,如果当时让欧阳竟无、清净居士来看待这些敦煌卷子,他们可能认为残卷意义不大。并非因为是“残”卷,所以意义不大;假设是完整的卷子,被伯希和等人盗去的卷子,也意义不大。因为这些卷子大部分是中国佛教学者的著作,是在佛教“中国化”的气氛和思潮下写成的,所以照欧阳等人看来,其佛学价值几近于零。而叔迦先生就不会这样看问题。 苏、程二位先生的话,很容易让读者认为,法相唯识学南北两大家的欧阳竟无(1871-1943)和韩清净(1884-1949)从未注意到敦煌卷子,就是注意到了,他们也会认为残卷意义不大。照程先生的意思,南欧北韩不注意敦煌残经或者认为其意义不大的主要原因是,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是中国佛教学者的著作,是在佛教‘中国化’的气氛和思潮下写成的”,故而以南欧北韩“印度佛学本位”的眼光来看,敦煌残经的“佛学价值几近于零”。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苏、程两位先生,南欧北韩不仅注意到敦煌残经,而且南欧创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包括其前身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和北韩建立的北京三时学会还注意到某些残卷的价值和意义,曾经有选择地加以校勘刻印。敦煌卷子中虽有很多“中国化”程度很深的佛学著作,但也有不少“中国化”程度很浅的唐代玄奘一系的法相唯识学佚籍,引起南欧北韩注意的首先就是这批佛典。 在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1922)之前,欧阳渐就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组织自己的学生校刻过一部敦煌出土的法相唯识学要籍,即唐京师西明寺沙门昙旷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简称《百法义记》)。我托友人隆藏法师从北京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借出这部论疏,发现它还是周叔迦的堂兄周叔弢(名暹,1891-1984,史学家周一良的父亲)和周叔迦的长兄周明泰(1896-1994)等人捐资刻印的(参看《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黄山书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11-12页),书后有刊记曰: 孙多焌、周暹、周明泰合施银百五十圆,敬刻此《记》,连圈记字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九个,支校刻银百三十二圆,余银由流通处印书布施。 民国九年季春金陵刻经处识研究部刻 刊记前面还有欧阳弟子、唯识因明学专家邱檗(字晞明,一作晞运,江西宜黄人)写的校记: 《百法明门论》略陈唯识名义,大乘光《疏》释词稍简,基师《解》文复多缺佚。昙旷作《记》近出敦煌,周君叔弢钞得见饷,披读再三欣惬希有。基、光论述依据三藏,奘师受学胜军居士,再传窥师,因述《成唯识记》,义文渊海,初学面墙,得兹《论记》开明,慧光一线。惟《记》本衍缺,多所补削,犹恐伪漏,致滋疑惑,愿诸读者,靡尤再详。宜黄邱檗附识。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