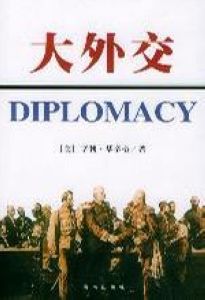 《大外交》 [美]亨利·基辛格著 顾淑馨译 海南出版社 1998年1月第一版 说起来,许多人也许不会相信,美国人常常说自己是“难以驾驭的人民”(unruly people)。其实,这不难理解。美国最初是由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构成的。他们不看重出身和背景,自主意识强,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和政府、他人分得清清楚楚,即使是争得面红耳赤、大动干戈,亦在所不惜。而且,他们又大多自视甚高,即使投票选总统,也喜欢投看上去不如自己聪明的人一票。所以,小布什这个综合素质中等偏下的人在2000年击败看上去很有学问的戈尔,显然不是偶然的,很能反映美国人“集体意识”的重要一面,即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的“反智主义”。不过,我们也不要小看了美国人。美国的历史也表明,美国人在追求个人自由和财富(即“美国梦”)的同时,也善于与人妥协,搞“平衡”,以求利益最大化。这可以说是美国人“集体意识”的另一面。为此,他们不惜抑制自己“反智主义”的冲动,网罗全世界的人才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远的不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就是最好的例证。 基辛格最擅长的是外交。即便是在美国,像他这样既有理论涵养和世界眼光,又有丰富“实战经验”和“不俗战绩”的外交家,也是凤毛麟角。不过,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已八十六岁高龄的他,仍然为近来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出谋划策,在《华盛顿邮报》(8月19日)上撰文“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他敏锐地发现,一旦美国为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而且中国经济把重点从出口转向扩大内需,那么随着双方市场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形成中的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为此,中美两国都必须为自己在世界新秩序中寻找恰当的定位。不过,在他看来,近来出现的“新冷战说”、“中国挑战霸权说”和“G2说”,都不符合双方、乃至世界的利益。他认为,最现实的做法是,中美两国要顺应全球事务的重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趋向,在中美紧密合作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太平洋体系,而且这一体系必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够让太平洋沿岸国家实现各自的抱负。为此,他还特别提醒美国,应该追求一种新的、既有别于霸权主义,又与其领导力相符的角色。 不难发现,在该文中,基辛格仍然秉承其“维持世界均势”的思路,可以视为其主要代表作《大外交》一书论点的自然延伸。《大外交》虽然正式发表于1994年,但却是基辛格一生思想的总结。今天重读此书时,我还特地把它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做了比较,说句不客气的话,后两人虽然不乏洞见,但是著作中充斥着“哲学大话”(也即“形而上学的假定”),看似搔到痒处,实则无法落到实处。前不久,格林斯潘终于说了一句大实话,小布什发起的“反恐战争”其实与“文明的冲突”无关,而是美国要牢牢掌控中东的石油。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清楚地表明,“历史”并未终结,美国的自由模式也非历史的终点。最近,戈尔巴乔夫说美国需要“重建”,话虽然有点刻薄,但是,以我在美国的考察经验来看,却也一针见血。且不说美国人的生活用品和许多中、低端商品都依靠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就是连接各地的长途汽车和铁路系统,误点也几成家常便饭,而且基础设施比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如。还有,仅根据我从美国报刊上收集的统计数据,在2008年6月我回国之前,美国因次贷危机而失去房屋的家庭就达四百多万户。那些失去房屋的人家,我亦曾访问过,他们大多搬到郊外很远的地方,临时搭建的住所,和我十多年前在国内见到的“工棚”有得一比。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