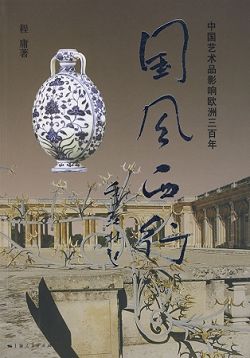 《国风西行》 程庸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第一版 曾经读到,一本法文的关于二十世纪的百科全书以如此暗讽的表述作为起句:“在二十世纪开端之时,当欧洲君主们环顾四周的时候,他们感到,世界大致运转得挺好,尤其是,这个世界是围绕着他们运转的。” 如今我们都已经知道随后一个世纪发生的进程。那么,在十九世纪之前呢?世界是一直都围绕欧洲君主们运转吗?按照欧美人当今喜欢的说法,自打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后,全球就被控制在西方世界的统治之下,至今达五百年之久。果然如此吗?欧亚大陆西陲的这些小国的国王、女王——他们当中有几位当上了皇帝——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究竟处在世界文明最繁盛的中心,还是二环、三环?程庸先生的《国风西行》一书最有意思之处或许就在于鼓动我们心生这样的疑问。 实际上,程庸所注意到的有趣现象,最好不要用“艺术”的眼光来加以注视,因为一旦如此的话,那些“中国风情”的物品往往只会让人难堪。记得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进入马德里王宫“查理三世起居室”的时候,一位现代建筑专业的女孩不禁脱口惊呼:“呀,也丑得太吓人了!”其实我们都吓了一跳,也许,是王宫内部为了保护文物而让光线过暗,影响了视觉效果吧。不过同一王宫内的“瓷器厅”和“吸烟室”却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找到开脱的借口。实际上,在前一天游览过阿兰布拉(按英文译音则为“阿尔罕布拉”)宫,随即穿行在这样一座彻底“欧洲格式”的王宫之中,真是让人感慨到无言。当然,可以说,“风貌”、“样式”之类与文化传统、民族风俗、审美习惯相联,不能以一种标准——比如中国士大夫文化——去强加切削,因此,“中国风情”恰恰证明了欧洲人的创造性。不过,对一个稍微感受过中国瓷器,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官窑精品的人来说,面对那些欧洲仿烧的软胎瓷之类,确实要不知所措,无法置评,因为实在太不在一个档次了。因此,一旦以技术指标所带来的美感——瓷器的美感很大程度上由技术制造——来衡量,中国人就会很困惑,不明白该怎样讨论欧洲的陶瓷制品。所以,欧洲人在历史上表现出的“中国趣味”实在还是主要地作为文明现象,作为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线索更为适宜。当然,分析欧洲人何以会在“中国风情”当中自我制造出这样一种奇怪的趣味,倒是一个很正经、很值得探讨的题目。至于中国这方面,则是表现出了无论欧洲人喜欢什么都能照单供货的商人本色。 据说,中国瓷器在欧洲曾经可以作为硬通货使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富小富之家都要在客厅里摆上一柜瓷器,只怕炫耀财势的目的居多,正应了萨克雷《名利场》里的调侃:“拿你来说,如果知道坐在你身边的客人有五十万镑财产,难道对他不另眼看待吗?”让人浮想联翩的是,恰恰在明代的中国,白银开始成为日常流通的手段,“西班牙帝国的兴起和衰落最好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考察”(《白银资本》第3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我们中国人对这样的观点固然要特别谨慎,不过,却也应该意识到,关于欧洲人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不能完全听从欧洲人的自述。感受到欧洲瓷器与中国陶瓷在很长时期于水平上的截然落差之后,欧洲的王宫以及贵族府邸内会流行以从中国进口的、毫无艺术性可言的、应该说很低廉的“制瓷工艺图”彩纸(“墙纸”)做厅内壁饰,也就不会显得仅仅是对“异国情调”的好奇了,或者说,那未必是一种带有优越感的猎奇行为。当然,1492年以来的所谓“欧洲”也并不是一大坨匀质的、僵化的团块,而是一个不断变动乃至激变的过程,因此,玛利亚·特蕾莎女王与茜茜王后虽然都对中国物品怀有兴趣,但二者投射于其上的欲望却可能截然相异。因此,在程庸不惮心血地将这些遗存于世的线索蒐集到一起之后,还该有更多的人将这一工作继续深入,对于其中每一例具体的呈现做个案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