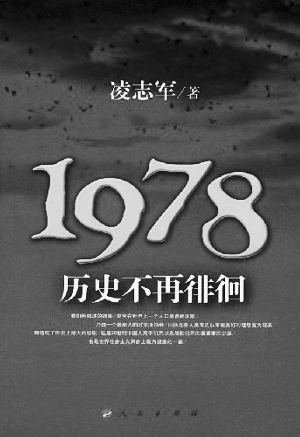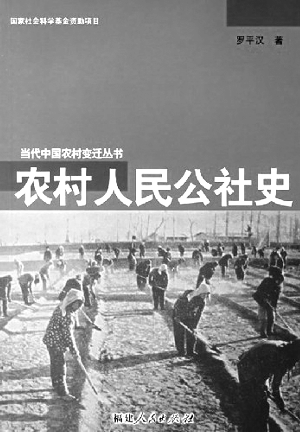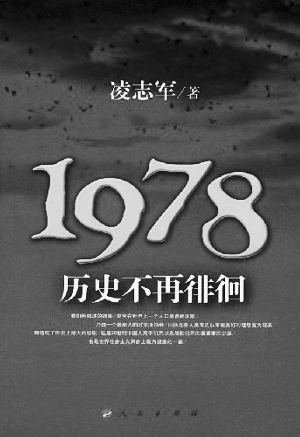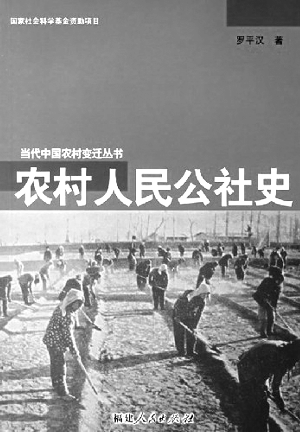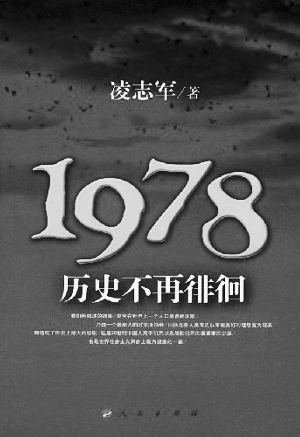
《1978,历史不再徘徊》 作者:凌志军 版本: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版 定价:1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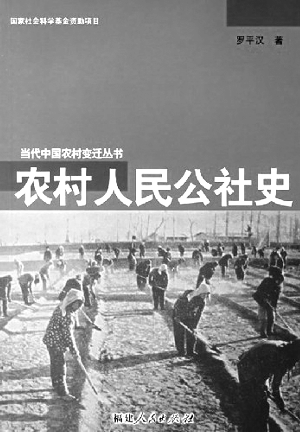
《农村人民公社史》作者:罗平汉版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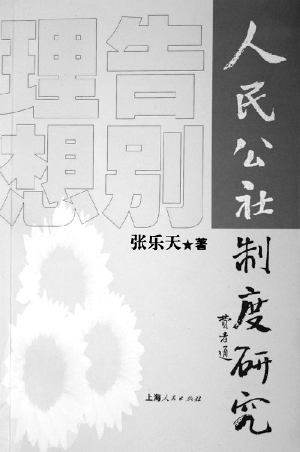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作者:张乐天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书评人 成刚
一本“问题图书”
父亲和母亲在我现在的年纪,分别担任生产队长和公社宣传干事,是当时中国六千万大小官员中的两位。我对人民公社的兴趣直接来自对父母那一代人命运的关切。汉娜·阿伦特说,马克思根据阶级斗争重写世界历史,他的初衷是要寻找一种方法,使那些被官方历史排除在外的人不被后人遗忘;人民公社的历史与中国阶级斗争的进程深度关联、树藤互依,生活在其中的多数人却似被历史遗弃,惟有一连串的路线纷争、意识形态运动被记载。中国百姓在1958—1984年间究竟占据何种位置?人民公社制度被“大包干”击溃后,他们的命运是否还受惯性支配?今天中国的命运与人民公社是否有关?
对那一段历史我们真的所知太少,老人们即便提及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也是怨天不尤人,将所有的疾苦统统归结到自然灾害。
“在我们国家,关于这一段历史现在看来也远远不够清晰。甚至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对于人民公社的故事也知之甚少,一些人甚至从未听说过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所发生的饥荒,以及这一饥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上一段引文是凌志军在其力作《1978,历史不再徘徊》的后记中所述,也是此书1997年初版后今天再版的原因。一本纵论二十多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悲剧性运动的著作,今日再版,深层次原因也许有二:一,中国农民的命运重获关注;二,人民公社的历史研究价值重新彰显,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不仅是具象的,也是隐喻的。这本书曾经被作为“问题图书”遭禁,继而又获新闻出版总署的优秀图书奖,一波三折,便披了几分神秘色彩,这固然与政治大环境的变换息息相关,也因为此书的难能可贵。
人民公社制度的社会理想
作者没有陷入资料堆不能自拔,他不满足于揭示真相,他边写边思考,通常以“我们国家行政的特质是……”为开头对人和事予以点评,深中肯綮。
人民公社制度的政治理想是消灭私有制,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来弱化社会基本单位家庭的功能,或者说人民公社其实是“分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它的实际目标不在经济方面,尽管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曾取得了经济成就、度过经济危机。它必须尽可能多地组织民众进入它的框架,推动和保持他们处于运动状态,因此,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初,许多地方出现威逼利诱加入公社的现象。人民公社的着眼点在政权或政治理想,这就天然地决定了它不能带领农民进入曾经许诺的乐园,在人民公社里的社员,其真实身份仅仅是个体的劳动力,由生产队对其进行生产资料的分配,而这些原本是由他们播种与收获的。群众的明里暗里的倒戈便是必然,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或出现危机,如六十年代初的饥荒。
陈永贵的浮沉是人民公社兴亡的缩影。他的发迹源于其与农民地位不相称的政治嗅觉,也不乏投机行径,当然主要得益于运动的需要,如果要全面解释初期他深受全国农民爱戴的原因,除了塑造的劳动模范学习榜样的金身,更因他是正在崛起的人民公社幸福社员的化身,他的存在就是一个承诺。陈永贵成功在于政治,失败也全归政治。农民对他的厌恶并非因他本人的行为。他所象征的人民公社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美好生活已成泡影,基本温饱也无法满足,不少地区出现了党员带领群众农闲时节流浪乞讨的尴尬局面,乞讨者也被明令禁绝,游街收监,定性为“攻击社会主义。”群众并不像俄国思想家巴枯宁的自我表白,“我不想成为我,我只想成为我们。”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他们只想成为丰衣足食的个体。人民公社的政治理想与中国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告别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制度带给中国的并非纯粹生产力方面的倒退。今天不少错误的社会观念与症状都可以在其中找出苗头,比如利用权力来打压异见、不加分辨的盲目崇拜,等等。全书最精彩部分之一是作者对腐败现象猖獗的解释,虽然共产党屡屡整肃气质,倡导廉洁,杀一儆百依然屡禁不止。“我们国家治理农民的重点,乃是将分散无矩的农户结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集体,所以种种侵犯农民家庭权利的行为,往往并不被视为非法,甚至还是维护集体利益所必须。”、“即使有干部敢于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也只是被看做个人品格的低劣所致,而非制度的积弊。”这一番见解之深,真让人豁然开朗。腐败这种沉疴旧疾,并非精神与道德规范能够纠正,特别是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
1984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隐喻——人民公社,一个源自欧文和康有为的乌托邦社会,一个信奉“精神变物质”的以道德和意识形态为根基的社会,一个意图抹掉家庭终被家庭埋葬的政治理想———触礁倾覆,在喜悦和喟叹中寞然退场,一个时代结束了。我目睹过不少它的遗迹,“大寨”、“公社”、“大跃进”等断续的标语依然存在于村里断续的围墙上,褪成绯红,像是某出悲壮的滑稽剧的宣传海报。我的这个比喻是否太过轻率?人民公社真的已经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吗?是否还有些问题我们忘记了回答,甚至从未提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