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八月狂想曲》是一部奉命之作,阅读之前,我曾经想,作者该如何处理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呢?毕竟,奥运和小说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但我看完小说以后,觉得徐坤处理得很好,她写得特别从容,这点是不容易的,因为有一个预设的命题在那儿,很多作家一写起来,往往就会迫不及待地往目的地跑,缺乏舒缓的东西,叙事太紧张,艺术性就会受到影响。但我发现,徐坤在小说中,一方面大量使用短句子,增加叙事的速度感,另一方面她又会用大段的抒情,甚至议论,来平衡叙事的节奏,这点,是很有意思的。 我对当下小说的不满,有一点,就是情节、叙事太紧张,不从容。很多人认为,小说是拒绝抒情,不能有议论的,但我觉得到了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小说怎么写都是对的。今天让小说的情节吸引力去和电视剧竞争,很难,那小说家还不如干脆后退,回到最简朴的小说写法中,放开写,这可能反而是小说的出路。所以,我欣赏徐坤的从容,她能处理大题材,面对大的社会问题,也有胆识去判断,敢于议论、抒情,不怕因此而影响阅读效果,这需要勇气。 另外,我特别看重徐坤小说里面所显露出来的那种专业的、实证的写作精神。尽管她对建筑这个专业不是研究得很深,但她还是做了很多专业、实证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不外行。现在,很少有作家愿意去做这种笨工夫了,他们往往习惯于在书房里做天马行空的想象,其实,要在这个时代出大作品,不花一点笨工夫是不行的。《八月狂想曲》里,作者对经济、社会、建筑,包括棚户区的生活,都做了不少实证性的描写,这就为作品构成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作家的想象有了一个根基,同时也获得了一种专业的高度。 《八月狂想曲》也让我意识到,现在的作家有一个如何重新面对自我的问题。从“五四”到现在,“自我”问题一直在折磨作家。有一段时间,这个自我被扩张成了一个公共的自我,这也就是丧失了自我。但这十几年来,自我被缩小、简化到了一个非常粗糙、狭窄的境地。我有时替很多作家感到惋惜,他们的才华、智慧老是纠缠在那些小情、小事上,很可惜。“五四”一代作家笔下的“自我”,还是有天和地,有他人的痛苦的,不只是自己闺房里的那一点事,但今天这个自我被简化到只剩下密室里的那一点事了。所以,自我的缩小,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困境,以至于很多作家不敢去碰大题材。《八月狂想曲》重新处理了这样的问题,徐坤试图在写一部远离她个人经验、能分享他人经验的作品,她不仅是在写一些私事,而是在写一个青春中国。这种写作上的重新出发令我敬佩。 现在的文学界中,恶毒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是温暖的、宽大的写作太少,能够让人感动的人物就更少了。这就要求作家要勇敢地重新书写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人生,一种有力量的、有精神厚度的人生。至少,徐坤是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当然,这部作品里一些地方可能处理得过于简单了一点,比如写台湾的亲戚来中国大陆这段,就过于漫画化了,太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情,不太像今天的两岸交流的人情现实。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对徐坤本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她已经通过这部作品,证明自己是一个有容量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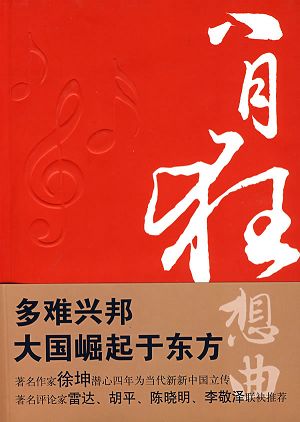 八月狂想曲,徐坤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