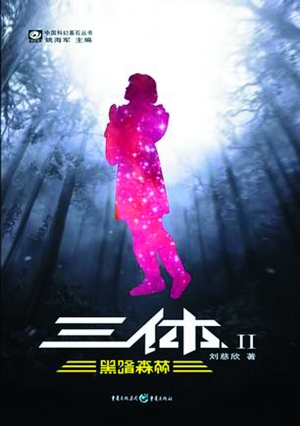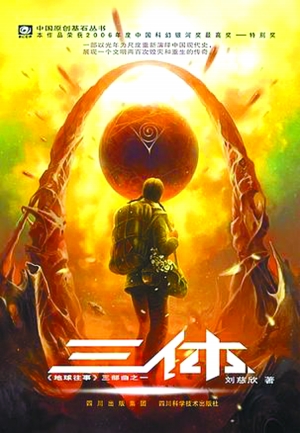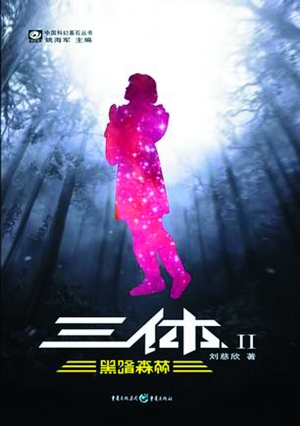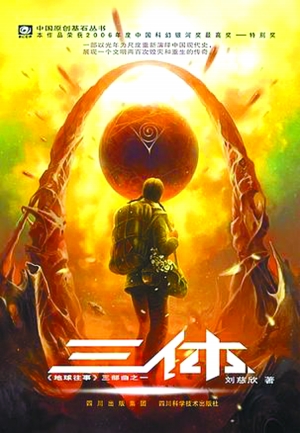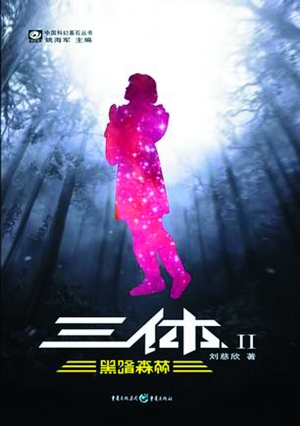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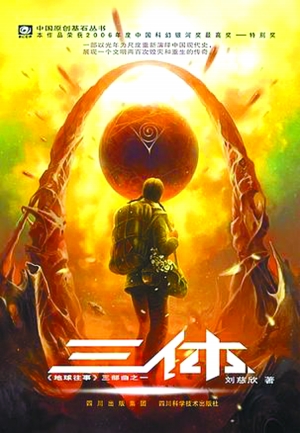
刘慈欣
祖籍河南,长于山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有很强的理工科背景。自1999年处女作《鲸歌》问世以来,刘慈欣已发表短篇科幻小说三十余篇、出版长篇科幻小说六部,并创下连续八年荣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纪录。其长篇力作《三体》开创《科幻世界》月刊连载原创作品之先河,一举成为2006年度最受关注、最畅销的科幻小说,《三体Ⅱ:黑暗森林》也因此被读者誉为“最值得期待的科幻小说”。
□书评人 屈畅
对技术的特殊敏感
《三体》为何物也?它乃是当今中国科幻界的第一人,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刘慈欣(被他的粉丝亲切地呼为“大刘”,而他的粉丝则自称为“磁铁”)的代表作,公正地说,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科幻小说中综合水平最高的一部,甚至超过了刚刚推出的它的续作《三体II:黑暗森林》。所谓“三体”,在天文学上是指研究三个可视为质点的天体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作用下的运动规律问题,以人类目前的研究水平,还无法算出其中的确切轨迹,只能求得一个近似,这也是本书的奥妙之所在。简单地说,请想象一位抛彩球的戏把子,他扔了三个球在空中接来接去,同时那些球又离不开他的手掌心,你盯着看一会儿,会觉得眼花缭乱吧?那么再进一步,请你把这三个球看成三颗太阳,把它们中间的那位戏子的脑袋看成地球,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颗“地球”上,随着周围的“太阳”不规则地运动,必然会出现各种惊人的灾害,什么恐龙危机,冰川封冻自是不在话下,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彻底崩溃,而后又随着环境的逐渐改善(三颗太阳回到相对平衡的位置上)而重新恢复。于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三体》就是以生活在这悲壮的三体星球上,一个毁灭又重生了两百次的文明为线索展开的。实际上,我上面所介绍的设定,仅仅是刘慈欣想像力的冰山一角,身为工程师的刘慈欣,对技术具有特殊的敏感,《三体》一书中到处能渗出奇思妙想。比方说地球上的人为了理解三体星人的生活,设计出一种全息网络游戏,游戏世界中的“文明”会不断进化,进化中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因为天灾而导致GAME OVER,然后游戏又重新开始,而这个游戏中的NPC全是周文王、牛顿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名人。这种游戏结合了现代网络游戏的模式,以可信的方式把三体人介绍到人类世界,像这样的构思,在这本书中是很多的。
对人的观察贫乏
遗憾的是,从这里开始,我就不免要谈到《三体》的弱点,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科幻为什么难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登堂入室。如上所述,《三体》在技术上的想象是超前的,对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的探讨刘慈欣做得非常充分,但与之相对的另一方面,对生活在这个背景下的人的观察,则贫乏到了简陋的地步。这个敏感与漠视之间的强烈反差,在我看来是中国科幻目前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
关于《三体》之写人记事,有一部分确是发自肺腑,大抵就是对“文革”时期种种倒行逆施的描述。刘慈欣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说对这种倾诉的渴望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怀念自己的青春,他们要鞭鞑所有耗费了他们青春的黑白不分,于是乎在感同身受的这点上表达得很真实。书中有火爆的“文革”场面,有活灵活现的领导人对与外星人接触办法的批示,乃至书中不堪忍受折磨的知识分子因绝望而向三体星发出求救信号,从而引发了星际战争———这许许多多的场面,哪怕放在世界科幻的大舞台上,也极其珍贵,可惜就可惜在,只要越出“文革”一步,突然之间,刘慈欣对人的观察和理解就陡然下降了几个档次,好像所有不存在于“文革”时期的人物都来自于《课堂内外》,变成了单面硬纸板,落差之大,令人愕然。
随手举例,《三体》一开头就是开会,防务会议,一开谈,来访的外方人员用英语津津有味地插话道:“TO BE OR NOT TO BE……”———当初看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在关乎存亡的会议上拽出中学生读物上的“名言”,夸张点讲,就好像联合国辩论时,中方代表突然来了一句中文:“别吵了,人之初,性本善也。”这真是一种笑不出来的黑色幽默。
科幻小说首先得是小说
纵观近二十年的世界科幻,哪怕就从我们最近能看到的诸如小说《米与盐的时代》、《给阿尔吉侬的花朵》、电影《变形金刚》、电视剧《太空堡垒卡拉狄加》、《天赐》等等之类而言,它们有的技术成分比较重,有的则神神怪怪、类似“奇幻”,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把对“人性”或“人”的观察放在中心。诚然,这些作品在西方也不是什么主流声音,但至少能得到公众的普遍承认,时不时还能冲到排行榜前列,这是关注点能抓住时代的脉搏。反观我们,科幻小说长久以来停留在科学普及的层面上,科幻是给看不懂艰深的书籍但又想培养学习兴趣的孩子以启发的东西———大多数家长正是这样想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科幻很可能也是给他们看的,科幻本身只是换了一个环境的现实生活,仍然可以像《激情燃烧的岁月》或《亮剑》一样演绎。当然,这里面有文化的限制,但我们的作家若不引以为戒,反而陶醉在论文式的技术阐述上,那被逐渐边际化又能怪谁呢?
国内的科幻迷喜欢作“硬科幻”与“软科幻”之争,其实“硬”也好,“软”也罢,科幻小说首先得是小说,一切小说成功的客观规律,都应当对科幻小说适用。刘慈欣本人曾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对中国的科幻事业表示了悲观情绪,实际上,尽管他自己的天赋不错,但如果继续像他现在这么干下去,又如何能不悲观呢?无论刘慈欣们是有意识地不去想还是无意识地陶醉于技术工程,事实摆在眼前,他们的心思没有花在对人的观察上,结果诞生的是一个头大身子小的畸形儿童,脑容量再大,也弥补不了四肢的缺失。
所以我的结论是,叫好不叫座,不是读书人的问题,而是创作上迄今没能警醒,刘慈欣尚且如此,比他档次稍低一些的作家可想而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