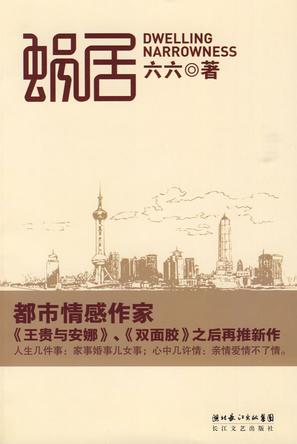 《蜗居》 六六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一版 (图片来源:资料图) 现在很多所谓小说家不过是在为剧本攒题材,小说早就过了季了,成了电视剧、电影的辅助品。如今已经见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苏童、莫言根本不跟导演同流合污但却引领其他艺术的小说创作了,有的只是开会讨论,然后动笔、接受意志、修改……然后影视作品和小说双赢。我不知道《蜗居》的制作过程,是作者对题材来了灵感创作的,还是编导、制片人发现了好题材,然后找人着笔形成文字作品,难以猜测,尽管小说在电视剧前写作完成,但作者本人就是编剧出身,实在很难说到底是哪个原因让她动笔的,写的时候脑子里是否已经在构思荧屏画面。 贫贱夫妻百事哀,《蜗居》想用大城市拼命挣扎的男女生活透视这个时代的卑微。为了一个房子,简单的目标,却要奉上一辈子的挣扎,这种怪事值得一百部当代题材的小说来表现。所以说这个时代实在是留给艺术家太多的灵感和题材了,而我们至今缺少那种直击现实痛痒处的作品,只能说是我们的作家太轻薄。为了房子,或者说为了在大城市立足而奔波生活耗尽自己的生命之烛,像海藻那样用身体、感情来换回那个虚无的目标,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什么为了幸福而去卑微地努力,而是我们实在太害怕不幸福了,这个时代造就了害怕不幸福、害怕贫穷的我们。只需简单对比一下即知,大多追求幸福而显得卑微的人,其实并非不幸,你能说海藻和小贝的爱情在遇见权势之前是不幸的吗?我们真的贫穷吗?也没有,只是我们一如既往地害怕贫穷而已。 这里的害怕贫穷被解读成爱好美好生活,我一点不觉得《蜗居》里有什么不得不的原因,以至于让“贪官”变得可爱。可怕的是毛尖老师在纠缠了一番官人如何获取爱情之后,得出了这样没谱的结论——“人民虽然不再害怕敌人,不再害怕贪官,但现阶段,似乎还没到为贪官盖被子的时候,否则建国后三十年,我们不遗余力打击的敌人,极有可能借尸还魂。”(《上海书评》2009年12月20日《人民不怕贪官》)动用如此激昂的语言干嘛呢,不像是在评论电视剧或者小说,而是在发表讲演,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诸多影片中展示的那样。我不觉得评论一部话题性的小说或者电视剧有必要端出人民和敌人来,还要造成对立面。人民是不怕敌人了,但多年不见的词汇在文章结尾如此喷涌而出,读者看着倒有点害怕了。宋思明当然不仅仅是个贪官,他也是个血肉之躯,我觉得作家恰好地挠到了人们对非百姓生活的一种幻想,高高在上的同时,也血肉丰满,他会爱,也会犯错误,而不是毛尖老师通篇阐释的什么贪官之爱。为什么一个眼瞎的人就不能四肢发达呢,我们还在用单一类型人物解释贪官的爱情,这实在是太过时了。 到底是审美,还是教育,在这个互联网通行了十年的现在,竟然还有人在为一部文艺作品无限放大其后者的功用。“在信仰和生活之间,我个人觉得,2009年应该尽可能拖住《潜伏》,让它继续在生活中放大发酵,这样,在看到《蜗居》中的宋秘书时,观众能更快地一眼认出,嘿,小样,甫志高嘛!”不就是一部茶余饭后的电视剧或者畅销小说嘛,至于又是放大又是发酵的吗?老师真是想多了。 链接 毛尖:人民不怕贪官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