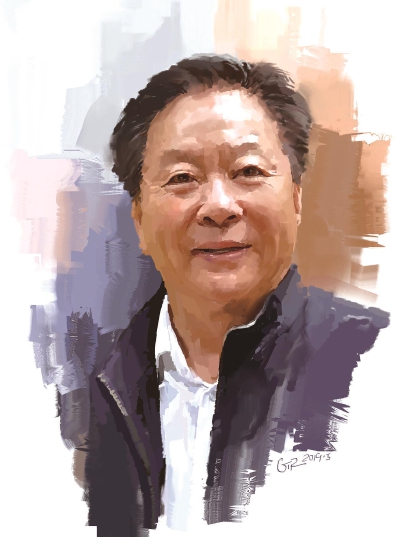 坐在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窗外一闪而过的,是大片初夏时节郁郁葱葱的稻田。从乡音、乡情、乡愁……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近些年,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见到了许多对于乡村生活的回望和缅怀。在不少人心里,乡村已然成为“回不去的故乡”。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吗? 触手可及的,是作家、国务院参事忽培元的长篇小说新作《乡村第一书记》,也是这次赴京采访的目的。不同于新闻体例,以小说方式切入这场正在广阔大地轰轰烈烈上演的精准脱贫攻坚战,以及以此为根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难,也难。说不难,虚构体裁的展现,作家可发挥的余地更大;难,一则因为“第一书记”之前在文学现场的描画不够,少有先例可循;二则以虚构写真实,如何让真意凸显,丰厚的生活积累重要,如何选材和落笔也重要。 到达的时候,正好是晚饭时间,因为路不熟,他特地关照友人来接我去他的工作室。 “忽老师这会儿也快从国务院下班了,走过来挺快,不远。”友人说。 “走过来?”我顿了一下。 “是啊,他每天下班都自己走到工作室来,就当锻炼身体嘛。看书写作,写两个小时毛笔字。” “天天都这样吗?”我忍不住问。 “嗯,一年365天,只要不在外出差,都这样。他的生活很简单。” 很快,我就见到了他本人。结果话还没说两句,他说,走,去楼下火锅店,一起吃个便饭。直到料碟摆开,眼前的火锅蒸腾起热气,筷头夹着菜,就这么面对面聊了起来,才有些释然。 眼前的忽培元,更像一位田园调查学者,温和质朴,白衬衫外面罩着件款式简单的深蓝夹克,携一个轻便的单肩挎包,随时准备出发去调研的样子。《乡村第一书记》中白朗和姜建国、姜怀安三代农村共产党员的形象,此时在他身上重叠了起来。 他从小在延安农村长大,18岁插队落户,19岁成为大队书记,就带领1000多名农民推行退耕还林、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修养猪场,以多种经营以改善当地生活条件。几十年来,从大队书记,到担任党政机关工作,直至如今任国务院参事,无论身在何处,他的心始终在“三农”问题上,他对于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走访也没有停止过。 某个层面上来说,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乡村第一书记》,虽是小说体裁,却拥有某种当下时代“教科书”的意义:作为“外来人”的乡村第一书记,如何开展工作,如何赢取民心?乡村发展,经济利益和环境维护孰轻孰重,是否存在共赢局面?包括宗族矛盾等在内的盘根错节的问题,症结在哪里,突破口又在哪里?对于这些,忽培元都有着自己的思考。从理念、思考到实际经验,使得这部虚构作品具有了强大的现实主义力量,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背后,又埋藏着无限涌动的暗流。 结束采访的第二天,在回上海的路上整理录音时,手机里一直跳动着各个群的新消息提醒。想起吃完饭后在工作室继续聊的时候,我们提到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在白朗以在微信群发言的方式陆续总结工作进展和得失时,总有不同的声音会跳出来冷嘲热讽,认为乡村衰败是无可挽回的趋势,振兴是一种徒劳。这种语调,在平日我们也曾遇到过。“写下这种分歧和争议,也是为了展现真实的某种声音。但我想说的是,发出这种声音,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乡村,对乡村没有感情。他们不了解乡村的意义,也不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难度和深度,能理解,但不应当。”忽培元说:“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就像一只鸟,年轻时候总想从巢里飞出去,飞得越远越好,后来又想飞回来,飞到它出生和成长的根源去休息、重新汲取力量。如果那个地方不在了,怎么办?” 脑海里回荡着他的这句质问时,耳边一阵轰鸣。一抬头,列车正在通过济南黄河大桥,土黄色的河水奔流而去,两岸广袤的土地被整齐的农田切割出规整几何条块,有几辆明黄色的农用车穿行忙碌,稍远的田头有三个戴草帽的农人,看不清手里拿着什么工具,只是站着,便古朴庄严。 “我是从土地里生长起来的,把真实的农村写出来,把农民的实际情况和想法写出来,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正如他的经历,忽培元的作品,也是从土地里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一种帮农民“说话”的愿望,始终驱使着他的写作。 记者: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你是黄土地的儿子。是什么让你在繁忙的工作之外一直坚持创作,写土地和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忽培元:我出生在延安农村,家庭很贫苦,小时候经常吃不饱穿不暖。陕北冬天的晚上又黑又长,我一直记得母亲让我们早早上床,在通铺上躺成一溜,然后细声细语地给我们讲故事。讲的其实也不算有情景的完整故事,都是平时她看到、听说的各种人、各种事。一边听、一边想,想故事还能怎么发展,人还能往哪去,这让我在还不知道文学是什么的时候,就埋下了种子。后来上学,“文革”期间翻墙去学校教室偷偷看禁书,看了很多书,又碰到一位很好的启蒙老师,教我怎么观察生活,怎么真正读懂书。另外,我的父亲忽聚田是陕西省水利学会副会长,身为陕北最早一批水利人,他身上体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真正的良心,和一心为国鞠躬尽瘁的精神,他的身体力行,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也让我懂得知识的力量能够让人受益终身,无论何时,都要多阅读、多思考、多动笔。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对文学的热爱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记者:你19岁时就曾任大队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5年,对“第一书记”的职务一定有着更切身的感受。 忽培元:我18岁插队落户在延安城南的川口县,第二年就被推选为大队书记。说实话,年轻啊,心里不是那么有底气,但也充满干劲,多学习,多尝试,找到适当的工作方式。其实在1975年,我就注意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了三年,比小岗村还早两年。那个大队1000多口人,2000多亩地,我划分成四个作业组,定地块、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产量,到年底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奖罚,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很不错,群众也满意。其实啊,后来派我到任何岗位上,我都干得游刃有余,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处理各种事宜,我最优先的考虑是搞清楚群众想干啥。他们的需求是不是合理,如果是合理的,我就想办法满足他们,既公正,又要讲道理。为人民服务,归根结底就是对群众的困难和疾苦负责,帮他们解决了实际问题,很多矛盾就迎刃而解。 记者:在你的许多文学作品里,都有这段插队时经历的印记。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你对于农民的理解和情感上的交融。 忽培元:我有很多诗歌是为农民而写,大量纪实文学中也有农民的身影。仔细想想,至今为止的五部小说作品也都是农村题材,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出生在延安的土窑里,从小在农村长大,遇到困难时期,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饿都捱过。插队后又和农民一起挥汗、一起劳作,在庄稼地里一起吃喝拉撒。关中称农民上地劳动为“做活”,而陕北则叫“受苦”,这种感情,只有共同经历过的人也许才会理解。农民是最淳朴的人,这些年里,对于农村怎么发展,本来就在探索中不断向前发展,也走过弯路,农民吃过苦,受过累。我和他们一样,是从土地里生长起来的,把真实的农村写出来,把农民的实际情况和想法写出来,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1977年写《土炕情话》,到《青春记事》《雪祭》《家风》,以及如今的《乡村第一书记》,我的这五部小说写的恰恰是上世纪70年代至今,每一个十年间农村发展中遇到的不同现实问题,也可以说是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农村一步步走来的艰难探索。 “时代在这里激流奔涌,文学更应当在这里发出具有感召力的响亮声音,写出平实故事下的思想潜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事业的发问:文学艺术究竟应当为谁创作、为谁立言?在《乡村第一书记》中,答案是清晰可见的: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记者:以“乡村第一书记”为名,小说主人公白朗可以说是近年来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年轻干部的典型,为什么会将笔墨着力于此? 忽培元:在后记中我曾提到,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提出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脱贫攻坚中的重要新角色,乡村第一书记开始走进人们视野。在我的走访中,曾遇到很多第一书记,对他们在工作中的事迹耳闻目见。 近了说,比如我所认识的一位驻扎甘肃偏远地区的第一书记,工作中全力以赴,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研究工作,经常和衣而睡,躺下还和同事商量事宜,忙碌到离家仅仅几十公里,却经常一两个月没空回去一趟。他所说的,所想的,都是这里正在进行的工程、那里正在建设的扶贫车间,哪一个地方,都少不了他,哪个地方,都有不断涌现的问题等着他处理。有时候他会和我说起他的痛苦和焦虑,那其实都已经成为工作常态下的“副作用”了。 实际情况是,这些年,数百万的乡村干部,无论是自觉自发的,还是派驻下去的,都在日以继夜地工作,每一个省都有因为过度劳累和意外而倒下的人,其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与故事。他们的工作状态、效率和与群众的深厚感情深深打动了我,加上这些年来记录的大量采访笔记,空的时候一边翻读,一边思考,具体的艺术形象,也就慢慢在心里成型了。 时代在这里激流奔涌,文学更应当在这里发出具有感召力的响亮声音,写出平实故事下的思想潜流。从对思想认识上的探讨,到基层存在的问题,比如某些党内腐败和“抱团”现象、蚕食群众利益等负面问题,小说都有深层次的揭示。可以说,《乡村第一书记》在写一位优秀“第一书记”的同时,我的出发点也是立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真实的状况、内心诉求,脚踏实地的真实的写作,而不是不切实际、流于表面地去写一些浮华的东西,作家应当有这样的追求和自觉性。 记者:小说主人公白朗身上,似乎也有你的影子。细读作品,其中很多地方,例如他对于旱厕改造、沼气的再利用,打井改善村里水源质量等举措,都是你以往工作积累的经验之谈,也使得作品中的这些细节格外真切、鲜活。 忽培元:写典型人物,还是要回到文学的规律上来,写你所熟悉的对象、熟悉的人物。白朗身上有一定的原型,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写的时候觉得格外亲切。文学、文艺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反应政治并非图解政治,更不能喊口号、概念化,而是应当通过这个时代能够立得起来的文学形象来折射和体现政治。 记者:在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一批“实干家”之外,“第一书记”的实际意义,是否更在于建立起有效的干部筛选、培养方式? 忽培元:这些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其中有很多年轻干部,就属于“三门干部”。“第一书记”的实际意义,也在于帮助这些干部迅速成长。 记者:何为“三门干部”? 忽培元:出家门、入大学门,出了大学门,直接又入机关门——三门嘛。年轻干部拥有学历,但学历和经历是两回事。经历、经验哪里来?对群众的感情哪里来?第一书记制度恰恰能将真金白银的优秀干部遴选出来。担任第一书记,需要完全以实绩和实效说话,没有一点可以掺假的地方。也有不少人思想基础不行,在深入一线工作后退却了,当了“逃兵”,这恰恰是筛选的结果。年轻干部需要锻炼——先“锻”、再“炼”,用锤子好好捶打,不断磨砺,通过这样途径培育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 记者:在白朗之外,我也注意到作品中出现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新人形象”。正如《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所言,对于这些形象的书写也为中国当代文学长廊增添了一组新的农民人物谱系。 忽培元:“新人”的确不止白朗这一个。比如书中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意识的村内企业家刘秦岭,以及村里其他四位复员军人,这些人在商业战场上摸爬滚打之后才意识到建设家乡义不容辞,毅然回村创业。这些人其实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的文化理念。还有“90后”的见习村医姜改改、支教女教师蔡金凤等,都是我们的新人。对小说来说,塑造个性鲜明、时代印记鲜明的新人,能够代表那一时代某阶层的人物,是第一位的。 (下转第5版)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中,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这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 在作品中,忽培元所提出的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问题:乡村振兴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光是科技、技术的引进,根源在于文化振兴。 记者:故事的发生地上牛湾也可被认为是“姜家村”,为何这样定名? 忽培元:上牛湾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位于秦岭东段的伏牛山,又处于南水北调的关键位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些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的发展理念在这里最能得到集中体现,不是以说教的形式,而是形象化、艺术化的体现。在这样一个地方,相对而言矛盾也较为集中。 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都是以传统文化滋养的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连续性、深厚性深入我们的骨髓。这样一个文化大国,放眼世界,没有其他既有经验可循。上牛湾是一个居住着姜太公后裔的村落,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脉非常深厚的地方、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在这里发生的事,值得我们探索。 记者:小说中在白朗开展前期工作时,他遇到的问题也是许多村庄的共同问题:年轻人都在外打工,连党员大会都没法召开。后来一场简朴而庄严的祭祖仪式,成为召回在外的村民的良策。这样的设置,是否有别有深意? 忽培元:中国农村的发展,也是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村落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宗族、社会体制的繁衍过程。乡村振兴的根在哪?我认为在于乡村文化的复兴。关于祭祖仪式,其实人类和动物的分野就在于人类会祭祀祖先,祭祀活动中蕴含着我们文明的根基。小说中这个部分聚焦于具有乡村文化标志性的祠堂,进行祭祖活动,也是将口口相传的宗族历史作为整个作品的文化背景来处理,始终贯穿其中。在这其中,所提出的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问题:文化振兴。乡村振兴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光是改变村貌、把现代科技引进来的问题。 记者:你曾数次强调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文化不能缺位,这其中,传统文化究竟立于怎样的地位? 忽培元:中华民族就像一棵大树,如何使这棵树更具活力?肯定不是治理一边,丢掉另一边。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如果树根发生了虫蛀、枯萎,那树梢不可能繁茂。乡村在整个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不是一个要不要振兴的问题,而是如何着眼的问题。同时,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中,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这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文化土壤根基复活了,乡村也会像一棵树一样,不仅不会枯死,还会把自己的资源延伸至城市里。比如我的家乡大荔县,近年来就以乡村建设发展的经验带动县城发展,现在整座县城环境优美,就像一座生态文化公园,从自行车赛、马拉松比赛到龙舟竞舟,每年承办几十场次国内外体育文化赛事,这就是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进程协调发展的良好案例。 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的文化不要断代,让我们文明的根基不要衰竭。中央一再强调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但在实际各个地方的落实中,也有糟粕、有封建礼教之类和传统文化并不匹配的东西在流传。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生命力的东西、属于中华文明高尚道德情操的东西继承和发扬光大,要将这个纳入到工作任务里头。文化的复兴和经济的振兴,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最怕的不是穷,而是没有精神支柱。家庭也好,民族也好,灵魂是不能缺失的。 “陕西作家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写出蕴含着生命力量的经典,这是一种文学的献身精神。” 黄土地上,作家与作品、与时代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强大联结,透过这些如今已是经典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是陕西作家对于时代的刻写。 记者: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些读来文字质朴乃至粗粝,语言和结构有时都不甚讲究,内里却蕴含着无尽精神力量的经典作品,往往出自于陕西作家的笔下。 忽培元:柳青写《创业史》,四稿的稿纸整整装满了一个皮箱;杜鹏程先后九易其稿、反复修改,才有后来的《保卫延安》;陈忠实以《白鹿原》作为“带进棺材的枕头书”;路遥的墓志铭刻写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恰是黄土地所代表的那种深沉、厚重的精神品格。 你看黄土高原的山,好像土堆一样不起眼,但掘开表面的土,内层全是坚硬的石头。内在厚重、坚定,外在宽容、淳朴,沟壑深刻。这种自然状态下,造成了陕西作家的写作品格。 我们陕西作家都是吃山药蛋(土豆)长大的,都是绿色食品,“无公害”的,所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也不奇怪。一提笔,就和农民种庄稼一样,一撅头一撅头挖实、挖到位,把种子放进去,踏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一种创作态度。靠的不是花哨,而是精神内涵,让人体会到生活的喜怒哀乐。 记者:所以对黄土地来说,一方水土育一方人这一说法,似乎最恰切不过。 忽培元:你看过《黄土地》没有?陈凯歌的电影。陕北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就像电影里的那种信天游,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也进入灵魂的深处,那是来自生命的呐喊。这部电影为什么动人,就在于它充满诗意,又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以真实、朴实,特别集中、强烈的细节、画面和简短语言,形象化地展示特定环境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希冀、追求。虽然并没有直接点明,却折射出我们要把这种生存状态下的民众唤起、让他们找到改变命运途径的一种使命和责任,也留下了很多想象空间。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恰恰是用形象自身背后的力量来呈现思想、哲理和诗意。这也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多思考。 记者:在作品的文化根基之外,你前面提到的这几位陕西作家关注的都不是小我,而是一种与时代共振的、在更广阔意义上的思考。 忽培元:他们的作品,已经被历史和读者证明为经典。而无论在哪个时代,经典必须具有时代意义,不是反映个人的小情小调,而是在更高境界、广阔视野上关注大时代的变迁,反应更多人的心灵震颤。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等,就以自身精神缺失,折射了时代悲剧,无论从选材、着眼点、作家事业上,鲁迅的作品最能反映时代命运,他的小说,放到今天来看仍具有深重意义。 同时,经典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按文学规律办事的结果,创作是个复杂的过程。但在技巧上,从思想概括力、人物塑造力、叙事和语言的驾驭能力和提炼能力等,均要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标准,才能使作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记者:他们留下的,也是一部部属于他们的生命之书。 忽培元:对。唯有严肃的创作态度,才能成就一部经典。柳青、杜鹏程也好,陈忠实、路遥也好,这些写就自己“生命之书”的陕西作家莫不如是。他们用生命去写作,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热情。他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写出蕴含着生命力量的经典,这是一种文学的献身精神。 “当下的文学中,崇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生活中没有崇高的追求,只有实惠的索取,这会将人的精神置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 当下的文学生态中,我们总是在问,创作为什么没有高峰。但是否也要问一下,我们心中,有没有高峰? 记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问题特别想向你了解。白朗这一形象,可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年轻党员干部形象。在一些人看来,即便是主旋律作品,为了表现人物的丰富性,或者说故事的戏剧性,会刻意制造一些人物的灰色面,这其中是否存在误区? 忽培元:正面人物的完美,不是说他们在生活中没有缺点,而是这些缺点不足挂齿,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人格和品格。事实上,我遇到的很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半信半疑”的态度是不可能支撑他们走得很远的。 会选择那样写的作家,根本没有实际进入过这样完全投入的工作氛围,也没有体验过被利己之外的理想所燃烧的那种幸福感,和那种百分之百对于工作的痴情会给人带来的更长久的满足感。他们没有进入过那种境界,于是想当然地觉得这样的境界不存在、不真实,只有掺着阴暗面来写的,才是真实的。他们觉得人性就是丑恶的,这其实是有意识地将人性降至动物属性的书写。人性是人所具备的精神活动,有利己性,更有利他性,文学不能为了真实展现利己性,而放弃对利他性的追求。共产党人的人性,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唯利是图,更不是低级趣味。那种觉得是人就必须有缺陷,缺陷就必须往“大”里写,这种刻意的“弱化”,其实往往才是不真实、是无力的。时代大潮弄潮,与象牙之塔雕虫,本就反映了不同的创作格局与艺术格调。就像毛主席曾经讲的,文艺创作要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今天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文学在文人圈子里,相互喝彩,孤芳自赏,其实就已经脱离了广大读者,即人民群众。只有往广阔天地、往时代深处走,作品才会拥有真正的力量和在人民心中长久的生命力。 记者:归根结底,真实自有其力量。 忽培元:这一点,我有亲身体会,也和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许多第一书记感同身受——虽然苦、虽然累,但与农民打交道,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那种获得感和情感上的被认可、被尊重,是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这种赤诚,我见得太多了。他们本就是纯粹的人,哪来故意将纯粹的人刻画得不纯粹的道理?从人物纯粹性,到思想纯粹性、文学纯粹性的缺失,对于今天的文学,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不在少数。利他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一种牺牲精神。很难做到,但是恰恰有人做到了。在他们身上,人性是崇高的情感、意愿、境界,是超越一般人的某种不可能的可能。这种难能可贵,才是值得和需要文学去展现的。 记者:这让我想到近年来对于文学艺术创作中崇高性的呼唤。 忽培元:文学需要呼唤崇高。当下的文学中,崇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生活中没有崇高的追求,只有实惠的索取,这会将人的精神置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激浊扬清、褒扬真善美绝非刻板的政治概念,本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在此意义上,文学创新绝不应当等同于标新立异,也不是简单背离创作规律,而是对美好事物、美好愿景的坚守,是在文学规律轨道上的不断朝前推进。决定各个时期文学是否有存在价值的,是是否真实生动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和变革的浪潮。真实永远有其价值。我们的当代文学,没有很好地树立正面创作的高峰,也许你今天这么写,是冒着被误解的压力的,但是仍要继续这么写,继续写下去。有良知的作家,一定要拿出货真价实、沉甸甸的“真颗子”。真米实曲,才是一个作家应该追求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