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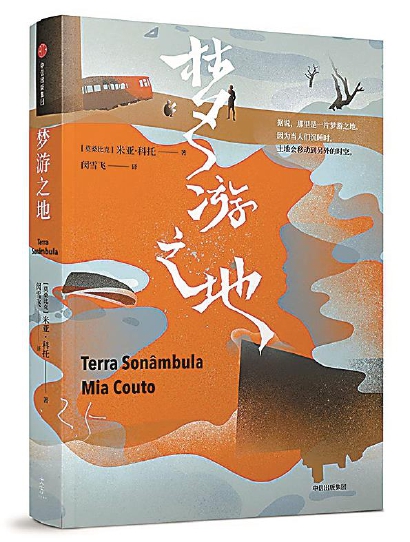 《梦游之地》[莫桑比克]米亚·科托闵雪飞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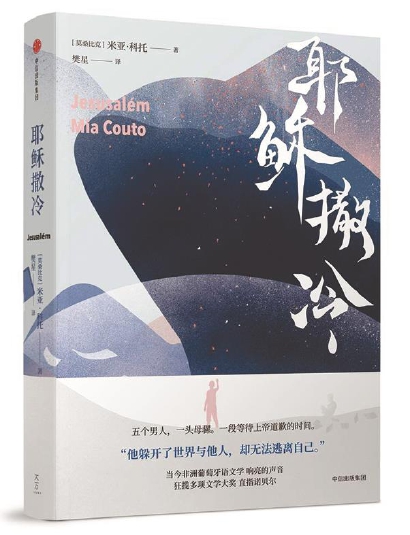 《耶稣撒冷》[莫桑比克]米亚·科托樊星译  《耶稣撒冷》[莫桑比克]米亚·科托樊星译 提到非洲文学,米亚·科托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尽管是当代葡语文坛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已经获得多项大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但在中国,米亚·科托并未被读者所熟知,非洲文学则更加遥远又陌生。 近日,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母狮的忏悔》《梦游之地》和《耶稣撒冷》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这是米亚·科托的作品第一次被引进中国。从这些作品中,或许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文学的非洲。 非洲对我来说就是写作本身 读书周刊:很多人认为,您成为一个作家,源自独特的人生经历,您的写作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米亚·科托:我的父亲是一个诗人,我的母亲是我所知道的人中讲故事讲得最好的。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去了莫桑比克,由于政治原因,没办法留在葡萄牙了,当然,他们就失去了家族和家园。所以,父母经常讲故事,为的是让我们消除那些距离感和失落感。在那一个个漫长的夜里,你才会知道诗歌和故事的价值。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开始做一个讲故事的人。 读书周刊:很多人都想不到一个对非洲描述得如此细腻的人,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非洲人。 米亚·科托:我小的时候,白人和黑人住得很近。这就意味着,从我家出来跨过马路,你就能听到来自不同文化的故事,我可以说土著人讲的非洲语,但这不代表我是分裂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拥有不同身份的人。 很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接到一个打到我家里的电话,我家在莫桑比克的首都郊外,打电话来的是一位刚果的老师,说他在教材中使用了我书中的内容。老师说他在课上对学生们说,米亚·科托是一个特别能够体现非洲性的作家,体现了他自己、他父母和他祖先的非洲性。我当时就很尴尬,也有点奇怪,因为我的父母和祖先都不是非洲人。这个人肯定搞错了,他并不认识我,我的书的法语译本中肯定是没有照片的,他以为我是黑人。他接着讲了很多,希望邀请我讲授怎么样保持写作中的非洲性。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那么轻易地给一个人的身份下定义是非常轻率的举动。即便我不是白人而是黑人,也并不一定要天然地跟非洲历史产生联系。莫桑比克有很多黑人作家更多是跟现代建立联系,而不是跟传统建立联系。 读书周刊:所以您曾说,人们会把作家定义为一种身份,可身份是多元的,我们其实都是游走在不同身份之间。 米亚·科托: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确定的标签,比如说非洲人、欧洲人、中国人,我们要忘掉这种标签。比如,有些欧洲人会说中国人怎么怎么样,而他实际上很可能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同样,其他国家的人也会讲非洲人怎么样,但也可能没有一个非洲的朋友。而在文学当中,就可以让我们建立起这么一个很具体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人,这样的一个非洲人,能够让我们和他一起交朋友,并且喜爱他们。 我既是白人又是非洲人;我是欧洲人与莫桑比克人的儿子;一位身处宗教世界的科学家;口语文学社会的写作者。我想连结这些截然不同的领域,因为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读书周刊:对很多人来说,非洲是一块模糊的大陆,让人们了解非洲是您写作的目标吗? 米亚·科托:人们想到非洲,就会想到这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但其实我们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多样性可能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所有的非洲人,为了证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独特的身份,都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历程。 有些人了解非洲是通过英国作家奈保尔的《河湾》,他在书中凸现了一个古老大陆在本土化与普遍化之间的艰难处境。我反复读了那本小说,奈保尔来到莫桑比克的时候我们还见了面。也有些人问我和奈保尔的区别,我觉得最主要的区别是奈保尔并不是非洲人,只是把非洲作为一个主题。对我来说,我是在非洲内部写作,非洲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议题、一个主题,而就是写作本身。 层层叠嶂下的沉默和寂静同样属于非洲文学的一部分 读书周刊:您在1992年就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探寻了殖民大陆身份认同的出路与可能,在文字中重建了莫桑比克整个国度。这本书出版后反响热烈,被称为20世纪最好的非洲小说之一,写作之初,您预料到了这样的成功吗? 米亚·科托:《梦游之地》讲述了莫桑比克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16年来,内战完全打垮了我们的经济,摧毁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被围困在那里,没有信念,没有能力重塑未来。痛苦和疑虑如此之多,找到希望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梦中。在战争结束后的日子里,复仇和和解是可以预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决定集体失忆,暴力的提醒被抛进了遗忘的深渊,我们知道这种遗忘是错误的。战争是无法忘记的,但我们想让战争忘记我们。 在这16年的冲突中,1800万人口中有100万死亡。但是战争的残酷性不仅仅是通过死亡人数来表现的,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坟墓的死者。战争的残酷是不可估量的,战争的进行使残酷成为不可估量的。暴力的意图是反对讲故事的艺术的:这种意图是要使我们失去人性。这种非人性化是以各种方式实现的。我们生活在一种绝对的孤独之中:与希望隔绝,无法把现在变成故事的宝库。我们都是孤独的,死者和生者。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故事。当下注定要被遗忘时,它才有价值。 《梦游之地》是唯一一本我写作时很痛苦的书。因为它是在战争中写成的,那时我自己也在绝望之中。几个月来,我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有朋友和同事在冲突中丧生,就好像他们来敲我失眠症的门,要我活在故事里,即使是谎言。战争的经历使我确信,还有比物质贫困更严重的其他匮乏。这些其他的苦难在所有国家蔓延,甚至波及那些自认为富有和有权力的人。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愿望是能够找回在那场内战中失去的人性。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构建造这种恐惧的时代,而文学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抵御这种恐惧。 读书周刊:从1992年的《梦游之地》,到2009年的《耶稣撒冷》和2012年的《母狮的忏悔》,您的非洲三部曲创作跨度长达20年,这期间,您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了吗? 米亚·科托:建议大家从《梦游之地》开始看,之后读《耶稣撒冷》,最后读《母狮的忏悔》。也就是说,按照小说的写作顺序,而不是在中国的出版顺序阅读,因为在《耶稣撒冷》中,相比《梦游之地》,我对于传统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耶稣撒冷是巨大的隐喻,象征一个父权制度失效的国家,充斥着肉眼可见的混乱与无序。在这本书中,我也质疑了莫桑比克的很多传统,尤其是对妇女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外力,或者说,外部文明的介入,来形成一种冲击与变革,消除传统中的压制的成分。 在《母狮的忏悔》中,我考虑了更多的女性权益。尽管莫桑比克的内战已经结束多年,国家实行了多党制,但是以主人公马里阿玛为代表的农村女性,依然承受着传统、父权与性暴力的压迫。女性依旧只具有功用性。倘若一位女性如马里阿玛一样不育,她便没有任何用处,甚至不被认为是女人。从这一部开始,社会边缘的女性开始成为我的写作母题。 读书周刊:作为用葡萄牙语写作的非洲作家,您创造性地将葡语与莫桑比克的民族性相结合,通过添加词缀、旧词合并等方式创造新词,使非洲口头语与欧洲葡语词汇相融合。在文学中,这种语言的创新意味着什么? 米亚·科托:葡萄牙语在来到非洲之前已经被其他语言给“污染”了一部分,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超过400年的时间里被摩尔人占领,所以很多葡语词汇的词源来自于阿拉伯语。自15、16世纪葡萄牙往非洲南部航海以来,非洲更南地区的语言也成为葡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葡语还受到另一个语言分支巴西的影响,而巴西的葡语又受到非洲黑奴的影响。所以葡语至今仍然是在活跃发展的语言,非洲有5个说葡语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语言都在不断地碰撞与交流中。 语言背后反映出一定的哲学和世界观。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能辅助我们去理解世界,运用不同的语言意味着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在莫桑比克,除了葡语之外,还有超过25种的非洲本土语言,不仅这些语言各不相同,其背后的哲学和世界观也都不一样。比如,我有时要去乡下调查,从事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工作,但在当地使用的非洲本土语言中,并没有确切的词对应“自然”和“环境”,也没有一种语言有对应“科学家”的词,这就需要一定的融合和创新。而在当地语言的表达中,他们称我为“白人的巫师”。 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我希望读者能触摸到语言文字层层叠嶂下面的沉默和寂静,这同样属于非洲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的一部分。 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写作但没法取代女性自己的声音 读书周刊:你很多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故事也都是在女性视角中展开,追寻女性的声音是如何在您身上发生的? 米亚·科托:我的家庭很小,只有5个人,父亲、母亲、三个孩子,母亲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女性存在。尽管如此,但她是这个家的支柱。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五六岁时,我就会坐在我们家厨房的地板上,听我的妈妈跟女邻居一边做饭一边聊天,我就觉得这个厨房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场所,不仅创造了食物,同时在她们的耳语、八卦中也创造了很多故事。我觉得在厨房地板上的这一场景是非常富有诗意的,因为这里有火、有水、有吃的,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元素。我本来可以说我的文学身份是在身为诗人的我父亲拥有的很多书柜那里开始的,在更文雅的地方开始的,但说实话,我作为诗人是在厨房这个地方开始的。当我开始写作,以女性视角写作时我想了很多,该怎么样才能够以她们的视角来想,而不仅仅是描写她们。我的对策是回到原初厨房里的声音,进而分离我内心的女性元素。 读书周刊:对于非洲文学来说,女性的声音更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米亚·科托:我的名字“米亚”,本身就是一个女性的名字。有时候我出国,别人都以为我是一个非洲女人。在女性身份问题上我有两面:首先是作为公民、作为社会人,我特别愿意为女性做更多的争取。在今天的莫桑比克,女性的地位比较低,仍然有很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行为,我不可能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所以我会去参与、推动提高女性地位的斗争。但从作家角度如何切入女性身份、了解女性问题我是有一些疑问的。作家没有职责,不一定要以政治参与者、政治活动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每当有人来跟我说,“您写的东西很像女性的声音”,我会把这当作很高的称赞。但我其实并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什么是女性写作、什么是男性写作,什么是女性的声音、什么是男性的声音,这个东西我还不是很清楚。 当我想到文学时,要保持男女二元性就不那么容易了。女性作家更倾向于写女性题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只能期待女性会写关于自己的文章,那就太可悲了。 与此同时,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莫桑比克女性作家,但也觉得有点遗憾,女性作家大部分主要关注女性生活和境遇,但并不一定要这样,这有点自我局限,如果女性作家能够有更广泛的主题会更好。尽管我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写作,但没办法取代女性自己的声音。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