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年初,《时间的形状:相对论史话》(简称《时间的形状》)横空出世,一位名叫汪诘的科普作家走入公众的视野。次年4月,《时间的形状》获得第八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直至今天,这本科普读物仍然被各大图书平台列为中国科普类图书的必读精品。2016年4月,汪诘在喜马拉雅FM开通电台频道,推出了原创科普类音频节目《科学有故事》,截至2018年4月,这档节目的播放量已达1070万次,订阅人数超过7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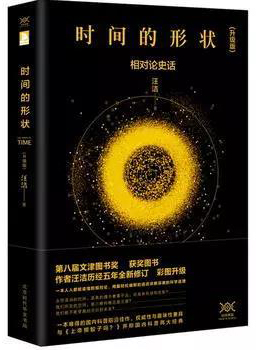 作为职业科普人中的领军人物,汪诘一直坚持着自己在节目发刊词中呼吁的——“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笔耕不辍、掷地有声地奋斗在科普工作的前沿阵地。 还原科学精神本身的节目才是隽永的 记者:你在2012年出版了科普书籍《时间的形状》,获得第八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6年你开始在喜马拉雅电台做音频科普节目。科普的多媒体途径很多,你当初为什么首选音频? 汪诘:其实这完全是机缘巧合。首先,喜马拉雅那段时间很火。第二,我周围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吴京平,他已经在上面做了一年多的节目,有很多粉丝,另外还有卓老板。当时我就有点技痒难耐。就想,我自己也写科普,他们能开我怎么不能开,所以我也就开了一个。 记者:一开始做音频节目,你是怎么确定节目选题的? 汪诘:这个对我来说特别简单,因为我本身就有已经出版的书《时间的形状》,而且当时我有一篇书稿已经写好了,就是我后来出的《星空的琴弦》,我刚好要做第二次修订,于是就把这本书先讲出来了。这样我也能收集意见,音频的好处就是实时反馈。所以我就一边修订我的稿子一边播节目,我的两本书《时间的形状》和《星空的琴弦》是同时播的。 记者:你的音频节目是由你一个人制作还是由一个团队运作的? 汪诘: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做,但是有很多人帮忙。因为有一些节目,比如说科幻广播剧之类的,需要积累听众了以后再让听众一起参与进来。我现在节目的片头片尾,也是我的听众——一个音乐制作人免费帮我做的。 记者:你觉得哪些内容是目前公众最感兴趣、互动最多的,或者是他们最需要被科普的? 汪诘:中医的这个话题互动就特别多,我算是做得少的了,不像卓老板经常谈这个,我会偶尔蜻蜓点水提一下,但是每当蜻蜓点水一下的时候,互动量就会特别大,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具有争议性,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一些跟社会前沿有关的,比如说区块链、AlphaGo的事情,这些跟热点有关的节目的互动量、评论量就会比较高。 但说实话,我自己并不喜欢这些节目,因为我做科普的目的就像节目片头说的——“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所以我自己喜欢的还是那些可以长久持续下去的,哪怕10年后来听都不过时的节目。能够还原科学精神本身的节目,才是隽永的,有生命力的。 像有些节目紧追热点,比如人工智能AlphaGo那期节目,是冲得很高,我平时一个节目5万~6万的播放量,那个节目60万的播放量。但是一年过去了你再去听那个节目,还有价值吗?没有。 但是《时间的形状》,这本书写出来到现在快10年了,依然有这么高的价值,去年豆瓣科普图书榜依然可以排到第四名,咪咕阅读的2017年十大数字阅读榜,《时间的形状》入选了科普类,出版类作品的十部里只有两部科普类作品,一部是《时间的形状》,另一部是《未来简史》。 记者:你的节目中常常会用到许多专业性的“硬知识”和数据,你如何确保这些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汪诘:分成两个阶段:我第一个阶段是业余做科普,就是2017年1月之前,这个阶段的严谨性不够,基本上是讲我以前的几本书。《时间的形状》第一版出来以后,又经过几次升级修订,错误是很多的,有的是听众指出的,有的是专家审稿指出的。那时候我带有一种玩票的心态,比如说我查一个数据,百度百科一看,这个数据我就写上去了。 自从2017年我成为一个职业科普人以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套职业操守,一共九条,我有一期节目也说了,叫《职业科普人为什么能生存》。其中讲到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就是我所引用的所有的数据和知识点必须有可靠的来源和出处。 什么叫可靠的来源和出处呢?百度百科肯定不是可靠的来源出处。我从2017年1月以后再也没有用过百度百科,因为那上面错误太多了,连维基百科在我眼里都不是可靠的出处。可靠的是维基百科引用的那些来源,比如说NASA的官网、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等。如果是新闻报道,我只用最主流媒体的。 第二个是所有的数据来源尽可能有两处印证我才信。我现在不能百分之百做到,因为有些数据它确实只有独一份的来源,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量的数据都是可以做到交叉印证了。 第三个是在碰到一些我没有把握的知识时,我会请专家帮我把关。我的微信里,有一个科学声音专家团,已经有50多个专家了,这些专家全都是各个领域的真正的专家,有中科院的研究员,有大学里的教授,全是博士以上学历,都是我在节目中征集过来的。科普的声音很弱,但门槛很高 记者:面对听众的质疑,或者是有争议的事情,你是怎么看待和应对的? 汪诘:分成两类,一类是指出我节目中的硬伤,就是知识点、数据的错误。这些是必须要认错的,科学本身就是一个纠错的过程,没有什么科普人写科普文章是不犯错的。 还有一类就是属于观念上的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比如说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碰撞,神秘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碰撞。这种观念上的碰撞,我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不含糊不打太极,因为我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普及科学精神,说白了就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我当然要和那种伪科学、神秘主义、各种各样的在我看来非科学的观念去做斗争了! 记者:你觉得目前音频科普的影响力足够大吗?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汪诘:说实话,我们“科学声音”那几个人,已经能成为科普音频领域的代表人物了。但是我们有多少听众?随便找一个大V或者明星,连他们一个零头都抵不上。我现在一期节目的全网播放量是10万左右,平均按每人播放1.5次,也就意味着有超过66000个人听过你的节目,66000个人放到咱们全中国来看算什么? 所以我觉得科普的声音还是很弱,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只是很多人没有感受到科学的魅力。简单说就是做科普的人还不够多,所以我才要搞“科学声音”这个组织,让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越来越多的人做这个事情,才能把全民热爱科学的氛围给调动起来。而且科学分成这么多门类和领域,天文、物理、数学、生命科学、健康,按年龄段也分为少儿和成人。这得需要有多少人一起从事?我个人只能做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记者:你觉得从事科普工作有什么门槛吗?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汪诘:有门槛,我觉得做这个事不是随便谁都能做的。 能够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本身就已经是科学素养高的人。即便你在其中,也只代表你有一些知识而已,真正的科学素养是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而真正有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人,我觉得更少。 此外,他得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热爱读书的人。他还要会写作,要耐得住寂寞,因为在2016年以前,像我这样职业做科普没办法养活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有几个人会愿意从事这一工作呢?现在是因为碰到一个知识付费的风口,大家愿意花钱买这种节目了,但还是只能养活很少的几个人。这就有一个悖论,如果你兼职做科普,做出来的节目质量肯定比不过全职做科普的。但是如果你全职做,马上就面临经济收入的压力问题,你怎么熬过第一年? 现在已经不像两年以前了,两年以前大家都是业余做科普,但现在已经有我们这样的职业科普人,听众的口味已经被提上来了,他们的眼光已经高了。你业余再做的话,很难保证每周都有高质量的节目。 抛砖引玉的“幸存者们 记者:你过往的经历对你的科普事业有怎样的影响? 汪诘:我大学是学科技英语的,毕业以后,我从事了十多年的软件开发工作。写程序特别需要条理化,特别需要讲究定量、定性。这十几年的程序员工作,培养了我这种严谨、客观、理性的行事风格和思维模式,所以这段工作经历对我现在做科普肯定是有帮助的。 另外就是我喜欢看书!而且我看的书不仅限于自然科学类,我还是文学爱好者。我很喜欢《红楼梦》,包括红学研究的著作。莫言、余华的所有书基本上我都看。我还是一个很喜欢文学创作的人,我现在写的科普作品,人家评论说不像一个科学家写出来的东西,像是在写小说。我觉得这种结合是我自己的一种风格,我会坚持下去。另外,我是一个美剧迷,我特别喜欢追美剧,这些美剧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在创作时会把我自己看过的一些美剧的元素融合进去。特别是《时间的形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它当成一部美剧来写,每章结尾的时候我一定要埋个“坑”,吸引读者继续读下一章。 记者:你的科普职业生涯中有哪些人对你有重要影响? 汪诘:我有一个精神导师,就是我在节目中经常提到的阿西莫夫。首先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阿西莫夫那本自传《人生舞台》。我看完《人生舞台》以后就有一种想法,我觉得阿西莫夫那样的人生就是我想要的人生。阿西莫夫平均每天写5000字,他不喜欢出门,很怕坐飞机,每天就宅在家里看书写作。他说希望自己死的那一天是倒在键盘上,鼻子夹在两个键之间。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太伟大了。而且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他对生活充满热爱,特别理性,也特别能演讲,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 其实我最欣赏阿西莫夫的一点即他是一个极端理性主义者,他和卡尔·萨根是美国理性主义的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所以他们的作品和我的三观特别合。可以说,我走上这条路也是受到了阿西莫夫的精神感召。 记者:你对音频科普的前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汪诘:从2016年9月开始,“知识付费”这个概念起来以后,出现了第一批能够真正热爱这个事情、又能够养活自己的人。这些人出来以后,接下去就会发生很奇妙的良性循环。 因为我们收入有了保障,而且我们是真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作品质量就会越来越好,会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过去中国的科普人只有两类,要么是业余做科普,要么就是体制内的。但是我觉得在体制内的职业科普人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内心原动力,而是各种机缘巧合被调到这个部门或者走上了这条职业道路。现在中国诞生了这么一个群体,虽然很小,但是它会越来越壮大,它会推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我对这个事是乐观的,我觉得走在前面的这些人已经在为后面的人慢慢趟开了一条路。 记者:你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大的挫折或困难? 汪诘:一方面是节目的价格卖不上去。科普类的受众人群还是太少,比如卓老板的节目算是卖得最好的了,但是经济类的、心理学类的动不动能卖到几十万份,而一个科普类的节目,卖得最好也就只有2.5万份。另外,它有没有一个瓶颈值呢?假设现在全中国大概有1%的人是听科普的,那这个1%最终能上升到5%或10%吗?它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这也是我正在纠结的事情。 另外,科普这个事情,它能否成为足以支撑商业公司做大做强的行业?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类似于得到或者喜马拉雅FM这样的平台,只做科普,最后能够像得到一样估值10亿美金,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因为谁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数据,调查到整个社会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东西往往有一种效应叫幸存者偏差,我们感觉自己播的节目好像很受欢迎,知道的人很多,喜欢的人也很多,但它其实是已经被筛选出来的。你平时在饭桌上,周围的朋友之中有几个人喜欢?很少。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潜质吗?我觉得只是没有被开发出来而已。 记者:你从事科普事业的这些年里,收获最大、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汪诘: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的读者和听众经常让我惊喜。举个例子,上次我们在北京演讲的时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别人搀扶着他过来,说他没有买票,慕名而来,我们有人问他是谁,他的助手就说,这是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时候我去做签售,就有正在世界名校攻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过来找我签名,说是受了我的影响才报考了物理专业,这种时候,我就会感到特别幸福。这样意外的惊喜多得数不过来。这些事情是让我觉得收获最大的。 采访者简介 张祎,北京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方向在读硕士。 姚利芬,文学博士,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现研究领域为科普科幻创作。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