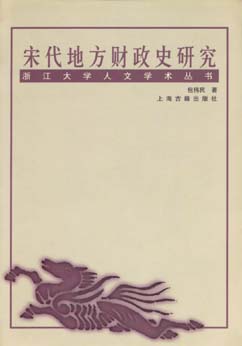 宋代财政史研究的重点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宋代是传统历史中第一个开始全面推行以两税法为标志的财产税的王朝,而且这个王朝其它的各种赋税也都不同程度地处在向财产税转化的过程之中。其二,自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瓦解、募兵制登上历史舞台,到宋代,国家正规军几乎完全由招募的雇佣军兵所构成,军队的数量超过百万,这就使得国家军费开支规模远超过唐代。所以也是从宋代开始,由于军费负担数倍于前代,财政在政务中的重要性提高了,真正构成了国家三大政务中的一支。其三,从唐代到宋代国家财政管理机构的演变,形成朝省户部与地方财政使职并存的局面。这三个方面,奠定了此后六七百年间财政史的基本格局。所以相对而言,以宋代财政史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具有更多的典型意义。 宋代财政史研究的重点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宋代是传统历史中第一个开始全面推行以两税法为标志的财产税的王朝,而且这个王朝其它的各种赋税也都不同程度地处在向财产税转化的过程之中。其二,自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瓦解、募兵制登上历史舞台,到宋代,国家正规军几乎完全由招募的雇佣军兵所构成,军队的数量超过百万,这就使得国家军费开支规模远超过唐代。所以也是从宋代开始,由于军费负担数倍于前代,财政在政务中的重要性提高了,真正构成了国家三大政务中的一支。其三,从唐代到宋代国家财政管理机构的演变,形成朝省户部与地方财政使职并存的局面。这三个方面,奠定了此后六七百年间财政史的基本格局。所以相对而言,以宋代财政史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具有更多的典型意义。包伟民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本着从论题出发,而非从宋代既有的财政制度出发,紧紧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这一中心,总体上既不求全,具体阐述则追求深入发挥。在地方财政史研究的具体结论基础之上,点到为止地归纳有关中国传统帝制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性的结论,不求发挥。书中值得关注的结论有如下几点: 第一,宋代地方财政基本奉行“以一路之资,供一路之费”即地方基本依赖本地财政收入、独立核算的理财精神。而当某一路分实在入不敷出时,中央更多采用的是直接调整其辖区的办法。以此形成了地方路级财政区。而宋代路级财政区的形成,无疑是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地方政区演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步骤。 第二,宋代国家财政的征收,每年由中央财政机关“计司”督责各路转运司应办,转运司责之州,州责之县,县则科敛于民。宋代财政之分配,沿袭唐代用名,称为上供、留州、送使,其实质为上供、地方经费,及桩存地方的三部分。上供部分开支国家军政费用,桩存部分以备非常之用,并且由中央计司通融均不同地方的财政。随着冗官、冗兵、冗费三冗局面的出现及迅速发展,宋代国家财政危机亦随之形成并不断加深。在这一局面下,宋代国家财政分配关系中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自上供为始”,即以服从中央财政开支所需为第一需要。这使得中央拔留地方的经费开支逐渐固定化,而中央从地方征调的财赋却持续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财政相对于中央,在路、州、县各级,形成了一种“阶层性集权”结构,每一阶层都尽可能地将下一级的财政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这一局面,使得宋代国家的财政控制系统呈现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内部无序的双重特性,使得国家的财政管理出现明显非制度化趋向。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承担了由各级官僚专制机构所带来的层层加码的沉重财政负担,从而严重妨碍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由此可见中央集权并不一定能带来秩序与效率。 第三,宋代赋税征收在税赋征调上常常不能循名责实、名实相符。这体现在两税税额的基本固定化与实际征收持续增长这一相对的两方面。为了不背上重敛虐民等恶名,拥有增税权力的中央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少增加新名目的科敛,但在实际上却用不停增加从地方调拔的方法,将税赋增收的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确保财政收入而不问其余的做法,为地方官吏法外征敛、残暴腐败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第四,从地方财政区域间不平衡问题来看,北方地区力役、科率等方面的重赋现象,构成了长期以来宋代全国经济中心南移趋势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第五,税赋征收阶级性不平等,历来都为研究者所重视。包伟民提出的新的见解是,从税赋征收的对象来看,国家主要征收的是有产阶级,而在实际征收中有产阶级以诡名挟佃或诡名挟户等方式将税赋责任转嫁给有产者下层及无产者。同时,以财产为基础的赋税公平征收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宋代出现了反复,这表现为征榷这一间接税实际仍以人丁为基础进行征收。政府和富豪通过种种制度和非制度化的手法,加重社会下层的税赋负担,增加了宋代税赋征收阶级性不平等性。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