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
郭熙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摘要:现代华人社会中称呼汉语的方式有许多种。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表明,“华语”“汉语”等不是简单的同指异名。这些称呼同异交错,功能各异,因时地而定。称呼汉语的方式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包括历时的不平衡和共时的不平衡),是历时演变和共时差异的不同层次因素叠加的结果,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它是社会认同多样性的结果,反过来说,也是社会认同建构的工具。 “华语”也是实体,是语言研究的对象。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将是多名并用,互相补充,这跟多样性的原则一致,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就汉语标准语而言,可以分为内称和遍称或跨境称,前者可称“国语”或“普通话”,后者称“华语”。 零 现代华人社会中称呼汉语的方式有许多种。主要有:(1)汉语;(2)普通话;(3)中文;(4)华语;(5)国语;(6)中国话;(7)?官话。这些称呼同异交错,因时地而定。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如何称呼汉语问题展开了不少讨论。在以往的讨论中,多数着眼于“正名”。近年来,随着各地华人社会交流越来越频繁,“华语”这一名称的使用越来越多,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各地“华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围绕着如何认识华语现象本身的讨论也已经开始。 笔者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华语”现象,并作了一些初步的梳理和分析工作。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是什么导致了现代汉语中称呼汉语方式的多样性?“华语”到底是“名”,还是“实”? 自从引入社会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之后,语言学界的相关研究一直有两个趋势。一是走向语言社会学,一是走向本体语言学,目前较为成功的是后者,而且主要是在方言研究领域(游汝杰 2005);但总的来说,以往的社会语言研究对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关注不够。本文假定导致称呼汉语方式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追寻,同时,也将就作为“实”的、同时也是学术术语的“华语”的研究展开一些讨论。
一
我们近年来重新关注现代汉语中称呼汉语的方式的原因之一是各地在称呼汉语上遇到了麻烦。我们曾经以媒体为例讨论过我们的尴尬(郭熙,2004),这种尴尬的局面在学术著作中也遇到了: 语言的通用性原则 ……主要收普通话(或台湾普通话,或华语)词语,基本不收方言词语。 …… (3)普通话和方言: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普通话、闽南语以及香港的粤语。 (汤志祥 2001:25) 我们断言作者的原稿不是这样,而且这一断言也得到了作者的证实。关于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因素,我们或许很快地可以得出结论,说是政治干预造成的。但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我们比较了《现代汉语词典》、《应用汉语词典》、《辞海》、《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文大辞典》(台湾)、《大辞典》(台湾)以及国家语委的官方网站《中国语言文字网》等关于相关名称的阐释,发现人们在这些名称关系上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不一致主要是集中在对“华语”的认识上。 《现代汉语词典》:指汉语。 《应用汉语词典》: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汉语 《中文大辞典》:国语也。 《中国大百科全书》、《大辞典》未收“华语”条,但前者在“汉语”条有如下的说明: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国家语委的官方网站“中国语言文字网”详细解读了“普通话”、“国语”和“华语”的关系: 这三种称说指的都是我国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中国的大陆称“普通话”,在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三种称说,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三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该网站还作了解释: “华语”是新加坡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在那里,这样称说汉语是恰当的。如果用“普通话”来称说汉语,它在表达同宗同源方面就不如“华语”那样强烈。如果用“国语”来称说汉语,就更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汉语不一定就是官方语言,或者并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显然,这种多样化的称呼方式是因为这些名称并不等值。 从《现代汉语词典》 “华语”条说“指汉语”到《应用汉语词典》说“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再到国家语委官方网站的“是新加坡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既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入,更反映了事物的实际变化。(郭熙,2004)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显然把“华语”和“汉语”等同起来了。《现代汉语词典》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二者的细微差异,《应用汉语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已经充分考虑了当今这些术语的实际差异。 围绕着这些不同的名称,学术界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的焦点是“正名”。讨论中,一些学者对 “普通话”这个名称提出了质疑(张拱贵等,1986;张德鑫,1992:38;江蓝生, 2005:1)。张拱贵、王维周(1986)指出“普通话”这个提法模糊,张德鑫则指出认为“普通话”先天不足,不得体。针对“普通话”名称问题,张拱贵、王维周(1986)、江蓝生(2005),朱曼华(2005)认为应该恢复“国语”的名称,而同样质疑“普通话”的张德鑫(1992:38)则认为用“国语不可取”。 应该说,“普通话”这个名称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例如,在汉语中,“ 话” 和“ 语” 是不等值的,的确容易误解为不包括书面语。侍建国(2003:14-15)详细分析了香港学校课程的“中文”和“普通话”概念与语言学意义上粤语和现代汉语的关系,指出普通话在香港只指它的语音形式。香港使用“普通话”的这一概念或许就是普通话名称所造成的。 陈重瑜(1986)认为,应该给华语一个法定的名称,她从5个方面阐述了使用“华语”这个名称的优越性:(1)表达功能;(2)历史渊源;(3)涵盖面和精确性;(4)超地缘;(5) 逐渐扩散的普遍性。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显然这只能解决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问题,并不适于处理和“汉语”的关系。张德鑫认为: “国语”不足取,“华语”也不会“魏晋吞蜀、吴”;“汉语”、“华语”会很好地“两条腿走路”,一主内,一对外,我国的民族共同语还是叫“汉语”,而“对外汉语教学”及“世界汉语教学”终将正式接纳甚至让位于“华语教学”。至于标准语在稍远的将来是否还称“普通话,现在还不能做什么结论。 显然,他把“汉语”和“华语”的所指等同起来了。但他又说: “华语”一词有点类似“英语”,这个名称的优点就在于共性和个性基本兼具。共性者,华语是中国所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新加坡等国外广大华人社会的共同语……虽然“华语”可替代“国语”,但不能完全取代“汉语”。“华语”是个通俗名称,“汉语”还是学术名称……(张德鑫 1992:38) 张的这些观点与郭良夫观点惊人的相似。郭良夫是这样说的: 一般情况下,“汉语”能换成“华语”,但是有时不能换成“华语”,例如“跟汉语同系的语言比较研究”这句话里的“汉语”,就不能换成“华语”。凡是能用“华语”的地方,都可以换用“汉语”;凡是能用“汉语”的地方,不一定能换用“华语”。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汉语”和“华语”同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汉语”可以用作学术名称,而“华语”不能用作学术名称,是一个通俗名称。(郭良夫:1985:98-107) 显然,照他们看来,“华语”和“汉语”只是“名”的问题而已。认为只是名称问题的应该不是少数,或许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对使用“华语”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参郭熙,2004)。 陆俭明(2005)建议建立“大华语”概念,和我们提出的“华语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 (郭熙,2004)基本上一致。他所说的“大华语”是: 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陆俭明:2005:3) 这已经表明,他认为“华语”是一种实在。我们认同这一看法。现在的问题是,“华语”的“实”是郭、张以后发展出来的,还是当时就存而因为某些原因被“遮蔽”了?这中间应该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
二
语言的确定并非依靠单一的语言标准。在确定语言的过程中,社会政治文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语言的命名也如此。一般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1.民族 汉语、朝鲜语、俄语、藏语、满语 2.国家 韩语、印度尼西亚语、吉尔吉斯语、中国话 [①] 、乌兹别克语 3.朝代 秦语、晋语、宋语、清语 4.其他 东干语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都会出现同一种语言有不同的名称的现象。 就历史上看,清语和满语是同一种语言,例如: 1)满官不射布靶、不谙清语者,均不得膺上考。(《清史稿·志八十六》) 2)嗣后八旗,总以清语骑射为务。(《晚清文选·民族的国民》) 3)上以清语为国家根本,而宗室贵胄至有不能语者,风俗攸关甚重。(清 昭槤 《啸亭杂录·宗室小考》) 就今天来说,朝鲜语和韩国语、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柯尔柯孜语和吉尔吉斯语、乌孜别克语和乌兹别克语也是所指相同,能指不同。 国家或朝代语言,会因民族认同的建构而成为民族语言。郑奠(1959)说: “汉语”这个词的意义,最初指的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 郭良夫(1985:98)则又指出,指称“汉语”有两种方式: (1)名称 秦语 汉语 晋语 宋语 (2)称述 秦言 汉言 晋言 宋言 这里实际上也反映了能指的多样化现象。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来说,这种区分的意义相当明显。但称述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的目标,就好像“国语”之类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目标一样。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在不同的能指中,“汉语”发展成了民族语言, [②] 而其它的能指如“秦语、晋语、宋语、清语”则成了历史词,或者成了某一种方言的名称。是什么力量或因素促使一种语言从国家语言走向民族语言?例如,汉语是如何从国家或朝代语言 [③] 发展成为民族语言的?同样,今天有这么多称呼汉语的方式,最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正名有用吗? 文献表明,汉代以后,在汉语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汉语的有两个名称,一个是“汉语”,一个是“华语”。 但总的来说,就历史而言,“华语”的使用量远远低于“汉语”。 到了清代,又多出了个“清语”,“汉语”和“清语”对应使用,甚至出现了“双语”活动,其间“华语”的使用一定更少。然而,另一方面,尽管清朝统治者把满语作为“国语”(清语) [④] ,汉语降为一种民族语言,但作为“清语”的满语在和汉语的竞争中失败了,“汉语”这个名称当然也就随着汉语的胜利而胜利。这样说来,民国时代应该是“汉语”大显身手的时代。然而,在我们看到的文献中,“汉语”这个词的使用率却非常低。这里说频率低,不是数据统计上的。全面确定“汉语”使用的比例需要一个断代语料库,出于种种原因,现在还做不到。下面我们想通过一些事例来支持我们的这种认识。 首先,1949年以前关于汉语研究的论著极少以“汉语”命名。 著作方面,在我们看到的著作中,以“汉语”命名的仅两例:一是张世禄译高本汉的《汉语词类》,商务印书馆,1937年;一是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王力的《中国语法纲要》、罗常培的《中国方音研究史》等书名都没有用“汉语”这个名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版时才分别改为《汉语语法纲要》和《汉语方音研究史》。 论文方面,我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8)《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进行了考察。在这部只收1900-1949年间中国语言学论文的迄今最完整的索引中,可以断定涉及“汉语”的论文题目仅有12个。这12个涉“汉”论文标题中,有3篇是书名直引,它们包括林焘和一作1948年分别在《燕京学报》和《大公报》(图书周刊)对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的介绍以及吕湘对赵元任、杨联升《(汉英)国语字典》的评介文章。剩余的9篇中,除了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1919)外,要么是谈古代汉语,要么是汉语和外语对举的时候。具体篇目如下:王静如《论古汉语之腭介音》(1941),邢公畹《论中古汉语元音之长短》(1945)、《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luk试释》(1948)、《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大名冠小名》(1949),高华年《论汉语借词与汉文化传播》(1944),王了一《论汉译地名人名的标准》,俞敏《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1949)。此外,还有3篇中的“汉”不知道是“汉语”还是“汉字”,也列出备考。它们是:毛汶《满文汉化考略》(1937)、郑德栋《论满汉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1948),聂崇歧《满官汉释》(1947)。 语言学者避开“汉语”这个名称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尽管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倾向性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其次,工具书中罕见“汉语”。 我们查阅了许多 工具书,发现1937年出版的《国语辞典》未见“汉语”和“华语”,而一些双语工具书中对Chinese中文解释也提供了类似的信息。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增订英华合解词汇》(A Moder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翁良等编)中Chinese条义项②下有“中华语言、中华文字、汉文”的对译,未见“汉语”一词。 这种情况大概较早时候已经开始了。新加坡 张从兴 先生藏有《增订华英字汇集成》一册,其中对Chinese的解释是:中国人,华人,汉人,中国话。这本《增订华英字汇集成》出版于清光绪年间,作者邝翰光,具体年份因脱页已无法知道。从序言看,该书是作者在其父邝容阶所编《华英字典》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今者思迪前光,故将此书杂字类,并英语类,概增粤音,以补先君所未备。”《华英字典》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根据该图书馆提供的信息,《华英字典》1884年由上海点石斋印刷,申报馆发行。 [⑤] 由于邝翰光并未对其父所编词典的主体部分进行删改,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出,那个时间用“汉语”称呼汉语并不常见。 第三,还有一些旁证。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的序也可以作为民国时期人们不大用“汉语”的一个旁证。原文较长,这里摘引几句密切相关的: 这部书的中文书名《中国话的文法》,刚好代表咱们所要研究的语言的体裁。 另外还有一个很自然的书名是中国口语语法(李荣就把我的《国语入门》第二章翻成《北京口语语法》)。 现在常用的“汉语语法”是两个词的词组,每一个词都很科学而且明确,但是除了在语言学讨论会里用得到以外,实际上都不说的。 赵元任的这部著作出版于1968年,可见,即使到了这个时间,他认为“汉语”还是不多用的。而事实上,这个时间,中国大陆“汉语”已经是频率极高的词了。王力、罗常培的著作再版改名就是典型的例证。这是后话。 1980年赵元任在为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写的中文版序中又说: 丁邦新同事寄来了一份他翻译成中文的我《中国话的文法》的序跟序论,寄信叫我写一序。我看了一看他翻译的两篇东西觉得写的完全合乎我说话的口气,一点没有那些“汉语语法”一类的专门名词的气味,所以我虽然没有看完全书的译文,可以相信一定会合乎我所希望看见的中文的“中国话的文法”,我就放心等着了。 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留美分会副秘书长朱曼华(2005)的一份关于使用“国语”建议中的一段话也可以作为旁证: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Hanyu”[汉语]从来就不是国际社会认可的我国国语的对应词,联合国一直沿用Chinese[“中文”/“中国语言文字”也被称为华文/华语];可见“汉语”这二字主要在我们大陆内地有其特定的内涵,以区别于其它民族的语言,而对外来讲,本来就没有其自身特定的语言学意义。 [⑥] 我们这里更关心的是原因。在我们看来,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1)国语运动的兴起,它使得“国语”作为汉语的称述语大得其道;(2)“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它有意识地在建构一种新的民族认同(1937年的《国语辞典》已经出现了“华族”一词),从而淡化了“汉语”的使用。当然,从上面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汉语”的淡出似乎从清末就开始了。这也应该与新的国家理念和思潮有关。 台湾教育当局《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2005版)对“汉语”的解释是: 中国话,汉藏语系中的一个语言。包括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等七种主要方言。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在民国时代,“国语”的使用达到了顶峰,但“华语”也仍在使用。我们曾经举过老舍使用“华语”的例子(郭熙,2004),林语堂在他的作品中也多次使用“华语”。在我们看到的材料中,老舍也使用“中文”和“国语”: 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里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老舍自传第9章) 学校也很好。学生们都会听国语,大多数也能讲得很好。他们差不多都很活泼,因为下课后便不大穿衣,身上就黑黑的,健康色儿。他们都很爱中国,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老舍自传第10章) 这表明,当时这些词语都在用。应该说,在我们调查的文献中,这个时期像老舍这样交替使用“华语”等不同称呼汉语的方式的作家是罕见的。这可能与老舍的经历和阅历有关。在新加坡,他使用“国语”,因为那里进行的是中国的侨民教育;谈到英国和德国,他使用“华语”或“中文”。老舍用语细致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给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称呼汉语的方式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三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国语”被“普通话”所取代,“汉语”的使用也扶摇直上。在我们看来,“汉语”的广泛使用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根据我们对《人民日报》的调查, 1949年10月1日 以前,用“汉语”的文章仅有一篇,而有趣的是,它也和50年前傅斯年的文章一样,是一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即陆志韦《关于拼音文字的方案的意见》 [⑦] : 本文所要说的,只关乎一种拼音方案的能通行不能。除非万不得已,不讨论语音学,音韵学,跟汉语的历史那些个。 这篇巧合的文章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傅斯年和陆志韦使用“汉语”是表述方便上的考虑,它也使我们进一步作出推断,这个时期极少数的学者使用“汉语”这个名称纯粹是学术上的考虑。 1949年以后,除了文革期间报纸被政治内容所覆盖而导致“汉语”量下降外,“汉语”的使用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普通话”一词的使用的情况也大体相似。 无论使用“汉语”这个词是出于何种背景,它的使用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体现了语言上的民族平等意识,避免了语言上的大汉族主义,为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二是推动了各民族语言的本体研究和语言间关系的研究,使得我国各民族语言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国语”这个名称1949年以后持续使用了一段时间。特别值得记录的是,1957年5月14日以后,除了作为历史词,“国语”不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和“汉语”、“普通话”相比,“华语”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一直处于劣势,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尤其如此。它虽然还见诸词典,一些场合作为简称还在使用,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俄华词典》、《英华大词典》 [⑧] ,但总的情况是日渐式微。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对180万字现代汉语语料的统计结果中,我们没有找到“华语”一词。 而《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是1967.10.1—1977.9.30十年中间,未能见到一例“华语”。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时期“华语”已经“死”了。 下面表一是不同名称使用数量上的变化的数据和相应的图示。 表一:《人民日报》上使用“汉语”、“普通话”、“华语”变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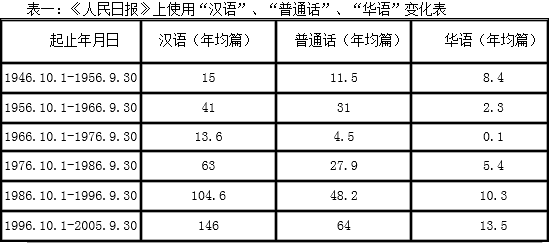 需要另外说明的是,我们曾在 2004-1-20 晚20:20时用google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的结果,互联网上各种网站使用“华语”一词的资料共59.2万项,使用“汉语”的是46.4万项。2006年8月17日下午16时,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得到的结果是:华语1260万项,汉语1140万项。我们还对2004年调查结果中“华语”和“汉语”前置的前10个词语进行了跟踪。下面表二和表三是相关的数据。 表二:2004年“华语”前置的前10个词语跟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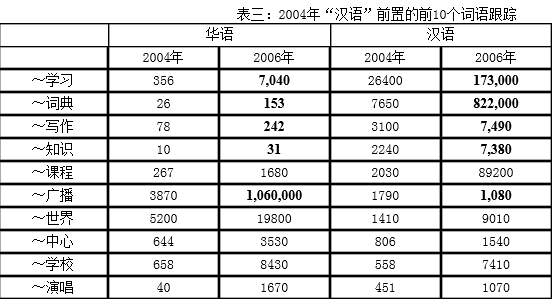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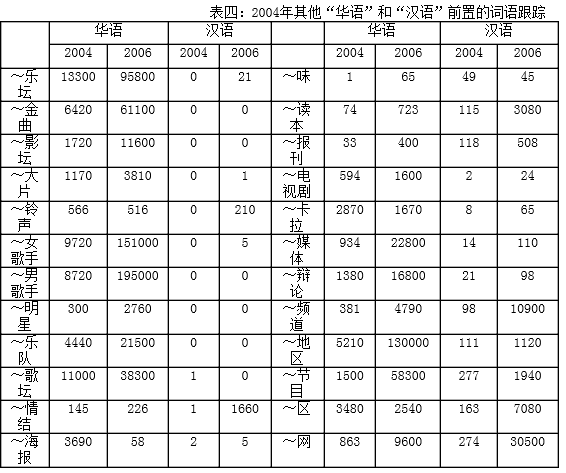 就整个华人社会而言,“华语”使用统计数量的增加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1)海外华人社会的华族意识;(2)台湾当局取消“国语”,改称“华语”;(3)跨国跨境的华人社会需要一个能够涵盖华人共同语的称呼方式。我们曾就此做过如下分析: 语言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其要素也在为适应交际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既然“汉语”这个名称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就必须有一个替补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一个传统上已经存在的,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广泛使用的“华语”应该是一个理想的选择。(郭熙,2004) 从历时的角度看,尽管称呼汉语的不同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所出现,但出现率即使用率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存在。即使是“国语”,尽管1957年以后国内主流媒体不再使用,但近年来国内互联网上并不乏用例。 如果再从地域上考虑,这些名称的分布分也不均衡。关于这一点,目前还缺乏详尽的资料,下面把已经了解到的主要情况略作说明。 “华语”——主要用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方言(如粤语、闽南话等)相对; “中文”——主要用于美国(也用“汉语”、“华语”、普通话)、日本、中国香港 [⑨] ; “汉语”——中国大陆以外,主要用于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这些地方也用“华语”。 “国语”——主要用于我国台湾地区,现在正式场合改用“华语”,但民间仍多用“国语”; “普通话”——中国大陆以外主要用于海外新一代华人侨民和移民,已经形成了“普通话社区”,香港也用,但只限于指口头标准语。 “中国话”----各地在非正式情况下都有使用。 总之,称呼汉语的方式仍然存在着不同形式,其中走强的仍是“华语”和“汉语”。
四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普通话”、“国语”、“汉语”、“中文”、“华语”、“中国话”等所反映出的称呼汉语的方式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包括历时的不平衡和共时的不平衡),是历时演变和共时差异的不同层次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对与之相关的“国”“华”“汉”“中”等字头的词的考察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⑩] 显然,以往的研究只注意了不同名称间的共时差异,忽略了这些不同的语言项目自身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英语和阿拉伯语不是这样?不管它们走到哪里,也不管它们处于什么时代,都是English或Arabic。或许我们可以用我们有“正名”的传统来解释,但我们又要问,为什么又有不同的“正名”呢?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正名”解释为政治干预。的确,从“国语”、“汉语”和“华语”等的沉浮,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干预的力量。然而,我们还必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干预?其社会基础是什么? 社会语言学研究表明,在语言竞争中,一些语言特别具有竞争力,其中有政治竞争力、经济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等(邹嘉彦等,2001)。这种理论我们可以用来解释上面说到的英语和阿拉伯语的情况。英语之所以走遍世界不改名姓与其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强势地位有关,阿拉伯语做到这一点则是依靠其宗教文化的力量。这一理论也可以解释“汉语”何以从国家语言走向民族语言、世代相传,而其他朝代语言名称如“秦语”“晋语”“清语”之类则一代而终。 然而,我们今天从称呼汉语方式的多样性所看到的是社会认同建构的力量。语言和认同的关系是当今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往考察称呼汉语方式的研究中,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能指本身,忽略了不同所指的“认同”价值;我们过多地注意了传统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源远流长及其稳定性,而忽略了这种认同的社会性。作为一种集体行为,社会认同是客观社会存在与个体意识作用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可塑性,它是有条件的(包括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事实表明,“汉语”、“华语”、“国语”等关系复杂,功能多样,交叉而不包容。因此,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必然是多名并用,互相补充。这是社会认同多样性的结果,跟多样性的原则一致,更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反过来说,它们也是社会认同建构的工具。社会认同常常与社会某些方面的导向有关,历史上的各种认同的建构都没有离开这种引导。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在谈到民族认同时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于一种文化原料——族裔核心。它是通过一些共有的象征符号、语言、神话和历史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容易改变。而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指出,民族和民族认同是历史性发展的社会建构。和其他集体认同一样,民族认同有它们的建筑师、企业家和建造者。它们由人民、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国家的政治意愿所创造,是精英分子发动的一项计划工程。康索亚洛·克鲁兹(ConsueloCruz)则指出民族国家政府常常通过教育、象征符号和一系列的话语系统,说服其民众加强对本民族的认同,从而使本民族获得一种历史感和共同命运意识。(见李明明,2005) 历史上的许多民族,在“汉语”的标志下,融合为“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国语”在民国时期得到大力的彰显,是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产物,而“汉语”在民国时期的下降,应该是“国语”遮蔽的结果。1949年以后,由于官方民族语言政策的引导,“汉语”大行其道,“国语”退避三舍,而海外华人社会则又因为认同的原因,重新建构“华族”,使“华语”在一定的区域大放异彩。中国的改革开放强化了大陆“华语基地”地位,给“华语”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华语”也将成为全世界华人认同的纽带,为一个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的 “华族”的建构和认同添砖加瓦。 “汉语”“华语”等汉语称呼方式的讨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命名本身。华语也不再是一种通俗名称,它已经进入学术领域,成了我们的研究对象。除了结合这些称呼方式考察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外,这些不同名称的使用都带来了研究观念的改变。“汉语”的使用促进了语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我们相信“华语”的提出也同样会有新的进展。我们不应只关注名称,更应关心实质。关于引入“华语”概念到汉语研究中的学术价值,笔者已经进行过初步的讨论(郭熙,2006b),这里还想指出,近年来,国际区域性语言研究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提出了跨境语言研究(戴庆厦,1993)、区域语言学(张裕宏,1976)、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等概念并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世界英语研究还出版了World Englishes杂志(英、美由Blackwell 出版)、English Today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English World- wide (阿姆斯特丹和费城出版)。 我们相信,从全球华语的角度研究汉语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最后,我们再回到命名上来。在各种称呼汉语的方式中,“华语”今天已经获得了全新的地位::它既不等于“汉语”,也不等于“普通话”,它是华人的共同语,是特殊的标准语;它不再是“通俗”的名称,也不再为中国人所独有。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普通话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取得了华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汉语的标准语可以分为内称和遍称或跨境称,前者可称“国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使用了“国家通用语言”这个概念,其简称形式正好是“国语”)或“普通话”,后者称“华语”,例如《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网;在外语(主要是英语)中,为区别于原来的Chinese和Mandarin,可以考虑直接用音译Huayu,事实上,教育部语信司和暨南大学共建的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已经采用Center for Overseas Huayu Research作为英文译名。 参考文献(正文或脚注已经注明来源的文献及相关工具数不再列入) 陈重瑜1986《“华语”——华人的共同语》,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21期)。7-14页。 戴庆厦 1993 《跨境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郭熙 2004 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2期,第56-65、75页。 郭熙 2006a 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语文研究》,第1期,第13-17页。 郭熙 2006b 论华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第22-28页。 郭熙 2002 《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见《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33-39页。 郭良夫 1985 《从“汉语”名称论汉语词汇史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98-107页) 江蓝生 2005 《建议把“普通话”名称恢复为“国语”》,《语文信息》第8期,第1页。 李明明2005 欧盟区域认同的社会建构.南开学报. (5)8-14页。 陆俭明 2005 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汉语教学学刊》,第1-4页。 侍建国 2003《普通话语音》,语文教育荣誉学识课程“现代汉语”用书,香港教育学院。 汤志祥 2001《当代汉语社区词汇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复旦大学出版社。 汪惠迪 1985《新加坡华语,走自己的路!——读 卢绍昌 先生<华语论集>》,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16期,19-24页。 汪惠迪 1999《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联邦出版社(新加坡)。 游汝杰 2005 社会语言学与汉语方言学的新阶段,见刘丹青主编《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张从兴(2003)《华人、华语的定义问题》,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4期,19-25页。 张德鑫1992 《从“雅言”到“华语” 一寻根探源话名号》,《汉语学习》第5期,第33-38页。 张拱贵、王维周 1986《“普通话”,还是“国语”?》,《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21期,第10-14页。 张裕宏 1976 区域语言学与东亚,1975-1976华语研究中心学术演讲汇录,新加坡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编印。 郑奠 1959《汉语词汇史随笔》,《中国语文》第6期。 邹嘉彦、游汝杰 2001 《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载《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1期,商务印书馆出版) -------------------------------------------------------------------------------- [①] 就书面能指形式而言,还有一个“中国语”,是日本语,与我们的讨论无关。 [②] 不仅汉语取得了胜利,伴随着“汉”的其他词语也取得了自己的地位。例如“汉子”。 [③] 朝代语言实质上是国家语言,只是从历史的进程看,它是朝代的。 [④] 《榆巢杂识》下卷:“每岁经筵进讲,例春、秋仲月举行。近以秋狝木兰,惟行于春仲。凡进讲先书次经,书与经各先清次汉。每讲官一巡毕,即发御论一通,则以清、汉语分讲。”这应该是比较早的“双语”用例了。 [⑤] 此处的资料是张从兴先生提供的。 [⑥] 中国留学联谊会欧美同学会网站 [⑦] 《人民日报》 1949年9月6 日第 5 版。 [⑧] 《现汉》诸版把“俄华词典”中的“华”解释为“汉(语)”。 [⑨] 在美国,“中文”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香港的“中文”仅指书面语。 [⑩] 限于篇幅 ,这方面的考察将以另外的专题发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