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红与黑》的故事
|
|
|
|
|
|

电影《红与黑》(法国1954年版)剧照
南京译林出版社是我的《红与黑》中译本的东家,据说此书颇受欢迎,我很高兴,因为我的工作获得了读者和同行的认可。
记得我曾经
说过,我译《红与黑》,从1991年底到1993年初,前后用了五个月。斯丹达尔1829年10月动了写《于连》的念头,1830年春天开笔,到了5月才定名为《红与黑》,7月下旬匆匆完稿,前后估计用了五个月。写作用了五个月,翻译也用了五个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当然,巧合中亦有分别:在斯丹达尔,那五个月是连续的;在我,则截然分作两段。然而,我的所谓“五个月”绝非只是撕去了日历上的150张纸。
这150张纸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30年前,即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红与黑》是我喜欢的一本书,尤其是看了钱拉·菲利普主演的电影后,于连·索黑尔的清纯的形象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以个人的才能反抗社会的不公,最后以不妥协的态度拒绝统治阶级的收买,令我非常感动,我想起了陈胜的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能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吧,那时我十六七岁,他的两次恋爱经历竟然没有给我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我像初见德·瑞那夫人的胆怯腼腆的于连一样,进了大学,我这才知道,这本书曾经对我的学长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多少人为了它而当上了右派分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如此,在反对白专道路的运动中,我还是冒出了一句“于连是值得同情的”,而险些跌进某君的圈套。事情是这样的:一家报纸的负责人来校主持座谈会,让谈谈对《红与黑》的看法,参加的人都是学生,我在会上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座谈会主持人马上来了兴致,忙问:“这位同学的观点很有意思,请继续说说。”我没有“继续”,只是惊讶:为什么别人没有和我一样的观点?我说“某君的圈套”,可能言重了,可是我当时确实感到,如果“继续说说”,后果可能不妙。因言获罪,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二年级的寒假,我跟头把式地读起了原文的《红与黑》,记得是莫斯科版的,封面是一把红色的长剑和一袭黑色的道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红与黑》的观点也起了变化,我更加关注最后十章,即入狱后于连的思想和行为。入狱后的于连从追求“成功”的梦幻和迷误中走了出来,不再把时间用在推“飞黄腾达”那块必定要从顶峰上滚落下来的巨石了。斯丹达尔说:“有才智的人,应该获得他绝对必须的东西,才能不依赖任何人;然而,如果这种保证已经获得,他还把时间用在增加财富上,那他就是一个可怜虫。”于连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但是他毕竟当了两个月的“有才智的人”。所以,“追求”中的于连是失败的,而醒悟了的于连是幸福的。人生的幸福在于我们对幸福的理解:从事最平凡的工作的人可能是幸福的,而身居高位、万人景仰的人可能是不幸的;幸福不关乎出身、财富和地位。我认为,这是《红与黑》的题词“献给幸福的少数人”的含义。这样的观点居然暗合了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勒内·吉拉尔的观点:“斯丹达尔说,我们不幸福,原因是我们虚荣。”(见罗芄译《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虚荣,说的是我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幸”,而舍弃的往往是“幸福”,荣华富贵成了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此是后话。可以说,我无意中为翻译《红与黑》准备了30年。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机会终于来了,就在距我入大学30年后的一天,1991年7月初,我去粉子胡同二炮招待所看望韩沪麟先生,他是南京译林出版社的编辑,为组稿来北京出差。他组稿的计划之一是为《红与黑》寻找一位译者,他说:“或者是你,或者你推荐一位。”作为学长,沪麟兄究竟看中了我什么?我此前总共只出版了《夜森林》、《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和《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三本书,他还不一定全都看过,而《红与黑》已有的版本的译者都是资深翻译家,有再出一个新译本的必要吗?我是合格的译者吗?须知,那时候译者对复译的态度是很慎重的,对翻译的对象是很尊重的。虽然我已不再年轻,但是对复译这样一本书,还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兹事体大,我没有立刻答应,但心中的确十分感动,我毕竟还是一个初入译界的新手。对于一个喜欢《红与黑》并且可能已经在心里翻译过不止一遍的人来说,有人请他向读者贡献一部他心目中的《红与黑》,不啻一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机会。当然,翻译并非我的主业,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如何挤出时间来翻译一本四十多万字的书,也是我犹豫的原因。然而,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几天之后,我就答应了沪麟兄,但是交稿的时间定在1993年春节前后,即一年半之后。1991年10月,我与译林出版社签定了出版合同。我没有料到的是,复译后来成了一股“热”,甚至激起了某些人为某个《红与黑》译本争席位排座次的热情。
很快,我就译出了六章,分别寄给了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和当时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的梁展先生,看看他们的反映。一个年事略长,一个尚属年轻,一个是法文同行,一个是中文系的新秀,如果能得到他们的首肯,无疑将大大增强我的信心。不出所料,他们都给予我热情的鼓励。说实在的,我对自己的翻译还是满自信的,但是,一个人的自信究竟还要得到别人的回应。1992年的春天,我花了两个多月的工夫,译出了《红与黑》的上卷,然而这一卷初稿一搁就搁了将近一年。眼看着“1993年春节前后”的“后”就要到了,下卷的译事还未开始,我决心拿出时间一鼓作气地完成下卷。果然,从1993年2月1日开始,到1993年4月10日,我就完成了全书,包括下卷的翻译及上卷的整理工作。那一年我正好50岁,精力充沛,一天四千字,连续两个月,似乎也未见疲态。我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学电脑,其实所谓“学”,不过是“用”而已,所以,就技术而言,我的电脑不过是一架打字机罢了,除了打字,而且是智能全拼ABC,其余一概了了。不过,我的稿子还是手写的。除了翻译之外,我还写了一篇《谁是少数幸福的人》,作为代译者序。这篇序有一点新意,得到了沪麟兄的激赏,他在电话中连呼“过瘾”,至于译文如何,那就只待读者的反应了。其实,我更为关心的是,法文圈内的评价。一般认为,我的译文更简洁,更符合斯丹达尔的风格。我还不至于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地步,“简洁”二字,于我足矣。
《红与黑》的翻译,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形容词或修饰语的泛滥,四字成语的使用,文句的抑扬顿挫,人物心理的无节制的夸张,对话的文雅与直白,译文语言的归化(或称“纯粹的中文”),等等,归根结底一句话,即译文的风格问题。一言以蔽之,《红与黑》的风格乃是简洁,即中国人论到书法时说的一句话:“书到瘦硬方通神”。具体的说,要于枯瘦中见出丰腴,于沉静中见出轻灵,于凝练中见出活泼。我用“简”、“枯”二字概括斯丹达尔的风格,褒者可以称之为“简洁”和“枯涩”(这里的枯涩与流畅相对立,多为大作家所欣赏,如波德莱尔和茅盾),贬者可称之为“简单”和“枯燥”。无论是褒还是贬,都脱不了“简”和“枯”两个字。我虽然“在心里不止一遍地翻译过”《红与黑》,可是要把四十多万字一句一句地落在纸上,那就是两回事了。有一个大家都说滥了的传说:斯丹达尔每于写作之前都要读一两页《民法》,取其简洁明了、洗尽铅华的词句和语气,以控制自己的笔触。为了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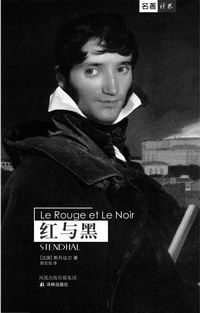 洁,我尽量去除可有可无的修饰语,如遇雪就不称“皑皑”,甚至连白都不要;遇雨则或大雨或小雨,而不必“滂沱”或“霏霏”;遇到女人身上的物件就不称“玉臂”、“酥胸”、“纤手”、“秀足”之类。斯丹达尔本人就说过:“不说马而说骏马,此为虚伪也。”但是,这样的主张我自己也不能贯彻到底,我的译本《红与黑》出版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在我的译文中竟然也出现了“秀足”一词!在该书的第76页上,赫然出现了“秀足”:“这样的位置,大白天,我们的主人公却认为可以把靴子伸过去踩德·莱纳夫人的秀足……”原文是“presser le joli pied de Mme.de Renal”,用了“秀足”,也说得过去,可是在我心里却过不去,如果有机会再版的话,我一定要改过来,改成“好看的脚”。我认为,“秀足”不脱旧小说的滥调,而“好看的脚”,则更具质感。总之,《红与黑》的翻译所涉及的问题很多,此处不能细说,我同意沪麟兄的意见:“倘若译者或是出版社为弥补旧译的某些缺憾,或是认为自己的译本另有特色,可以给读者全面了解原著提供方便,或是让读者得到另一种审美享受,那么译本再多,也一定是各有特色,瑕瑜互见,互补长短的,有什么不好呢?”我主张直译,相信“信、达、雅”,不过我是以“文学性”解“雅”的。所谓文学性,即该雅则雅,该俗则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一切以贴近原文的风格为要。总是不能惟妙惟肖,也要做到庶几不差。我反对“翻译是一种美化的艺术”的说法。以“简洁”一词赞或贬我的译本,我欣然受之,一部45万字的小说,我给卸掉了5万字,得一“简洁”的评语,足矣,夫复何求? 洁,我尽量去除可有可无的修饰语,如遇雪就不称“皑皑”,甚至连白都不要;遇雨则或大雨或小雨,而不必“滂沱”或“霏霏”;遇到女人身上的物件就不称“玉臂”、“酥胸”、“纤手”、“秀足”之类。斯丹达尔本人就说过:“不说马而说骏马,此为虚伪也。”但是,这样的主张我自己也不能贯彻到底,我的译本《红与黑》出版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在我的译文中竟然也出现了“秀足”一词!在该书的第76页上,赫然出现了“秀足”:“这样的位置,大白天,我们的主人公却认为可以把靴子伸过去踩德·莱纳夫人的秀足……”原文是“presser le joli pied de Mme.de Renal”,用了“秀足”,也说得过去,可是在我心里却过不去,如果有机会再版的话,我一定要改过来,改成“好看的脚”。我认为,“秀足”不脱旧小说的滥调,而“好看的脚”,则更具质感。总之,《红与黑》的翻译所涉及的问题很多,此处不能细说,我同意沪麟兄的意见:“倘若译者或是出版社为弥补旧译的某些缺憾,或是认为自己的译本另有特色,可以给读者全面了解原著提供方便,或是让读者得到另一种审美享受,那么译本再多,也一定是各有特色,瑕瑜互见,互补长短的,有什么不好呢?”我主张直译,相信“信、达、雅”,不过我是以“文学性”解“雅”的。所谓文学性,即该雅则雅,该俗则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一切以贴近原文的风格为要。总是不能惟妙惟肖,也要做到庶几不差。我反对“翻译是一种美化的艺术”的说法。以“简洁”一词赞或贬我的译本,我欣然受之,一部45万字的小说,我给卸掉了5万字,得一“简洁”的评语,足矣,夫复何求?
我要感谢译林出版社,感谢韩沪麟先生,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为国人贡献当代某个中国人所理解的《红与黑》译本。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红与黑》,也不存在一个中国化的《红与黑》,只存在一个定格在叫做郭宏安的译者笔下的《红与黑》。当然,《红与黑》还可以定格在叫别的名字的译者的笔下。事实上,这样的《红与黑》,据说有二十几个。
|
原载:《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