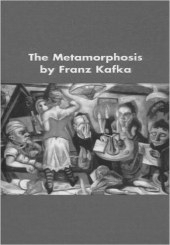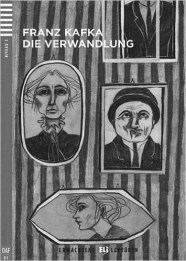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卡夫卡《变形记》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它被翻译成上百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除《变形记》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外,它的“副文本”同样值得关注。对绘画艺术兴趣浓厚的卡夫卡,曾创作过多种风格的画作,并且十分注重文学作品的装帧印刷效果,特别是封面设计效果。因此《变形记》封面从1915年初版单行本开始,就陷入了“作者意志”与“设计者意志”纷争的漩涡之中。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变形记》封面更是经历了复杂多元的演变过程,几乎每种新版本的问世,都伴随着新封面设计的出现。回顾《变形记》版本封面的发展史,有利于我们从“文本外”出发,全面地了解不同时代人们对于《变形记》的不同认识和理解。 法国著名文论家热奈特(GérardGenette)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标题、前言、跋、插图、封面等副文本因素共同构成了文本的叙述框架(《热奈特论文集》,2001),副文本犹如一道深入了解作品、进入作品的“门槛”,是通向文本的必经入口,是个过渡地带。(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2012)其中,封面画作为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本内容呈互动关系:文本内容从根本上决定着封面画的设计取向,封面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文本主旨、作者创作意图以及出版商的发行要求,同时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心理预设。既是“业余作家”又是“业余画家”的卡夫卡深谙封面画的重要性,于是在他的《变形记》初版单行本付梓之际,给莱比锡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写了这样一封信:“尊敬的先生:您最近来信说,奥托玛尔·施塔克将为《变形记》设计封面。我产生了小小的恐惧。但就我从《拿破仑》上对这位艺术家的认识而言,这种恐惧也许是多余的,我是说,由于施塔克真的要动笔了,于是我想到这样的问题,他会不会去画那个甲虫本身?别画那个,千万别画那个!我不是想限制他的权力范围,而仅仅是根据我对这个故事显然是更深的理解提出请求的。这个甲虫本身是不可画出的。即使作为远景也不行。如果这样的意图并不存在,因而我的请求变得可笑——那倒巴不得。若能转告并强调我的请求,我将十分感谢。假如允许我对插图提建议,那么我会选择诸如这样的画面:父母和商务代理人站在关闭的门前,或者更好的是,父母和妹妹在灯光明亮的房间里,而通向一片黑暗的旁边的那个房间的门敞开着。——1915年10月25日于布拉格”(《卡夫卡全集》,第六卷,2000) 但是,施塔克却为《变形记》设计的封面画与之却有些出入。仔细来看,“施塔克最终设计的封面上虽然没有虫子,但他是否采纳了卡夫卡的两个具体建议却很难说……画面上是一个青年,在他的背后,两扇门既没有全部‘敞开’,也没有全然‘关闭’,而是开了一扇,关了一扇;在‘一片黑暗’的门外(假定青年在‘门内’)看不到有父母和妹妹,这个青年倒是在‘灯光明亮’的房间内(姑且如此认定),因为地面有他留下的清晰的影子。”(赵山奎:《卡夫卡〈变形记〉的封面画——一个传记性插曲》,2015)。显然,卡夫卡对《变形记》封面设计的“干预意志”与其说是得到了部分回应,不如说是遭遇了设计者的某种“背叛”。而施塔克笔下的这幅封面画在捷克、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流传甚广,被视为《变形记》最权威的封面画而反复使用。此后在更多国家出现的不同《变形记》版本中,这种“卡夫卡干预意志”所发挥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变形记》日译本和汉译本先后问世,但这些版本封面上既没有卡夫卡坚决否定的“甲虫本身”,也未展现“父母和商务代理人”或“父母和妹妹”的行动,而是出现了卡夫卡自己的身影。 这两幅封面画都以卡夫卡为表现中心,而不涉及任何反映或阐释《变形记》文本内容的因素。1952年的日文版以卡夫卡生前最后一张照片为背景,辅以黑色德文字母FRANZ KAFKA和DIE VER⁃WANDLUNG,日文“变身”二字刻于卡夫卡肖像额部,似乎在传达“变身的卡夫卡”之意。1969年台湾版《蜕变》由金溟若转译自辻瑝的日译本,同样采用卡夫卡最后的照片,着重突出他深邃的眼睛,塑造出卡夫卡冷峻、孤独的形象。在这幅照片的底部,由绿、紫、蓝、黄四种颜色构成不同色块,拼出一个“十字架”图像,卡夫卡居于中心,他作为“文学的基督”形象跃然纸上。 《变形记》是卡夫卡小说中较早译介到国外的作品,选取卡夫卡肖像作为译本封面,一方面可以使读者更直观地认识这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封面画先入为主的倾向,为读者提供了更宽广的想象空间。 20世纪70年代的这两幅封面画如卡夫卡所愿,出现了“父母”形象,并且有选择性地展示了《变形记》的故事情节。印度版封面画中人物较多,妹妹站在客厅中央,对着父母说话,她的小提琴被扔在地上;三个房客围坐一起,在烛光下看报,其中一人掩面不语,似乎发现了不妙之处;父亲坐在长椅上,直视着房客身后突然出现的褐色怪虫,表情严肃甚至有些愤怒。这幅画生动地还原了变形后的格里高尔听到琴声后鲁莽闯入客厅的情景。 1974年西班牙版封面画则有意遵循卡夫卡的建议,使“父母”(没有“商务代理人”)站在一扇“门”前,不过这扇“门”不是关闭的,而是微微打开的;从父母影子的方向判断,房内有光亮射出,这又与卡夫卡希望房内一片黑暗的意愿背道而驰。众所周知,“门”是卡夫卡小说世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无论是《变形记》,还是《法的门前》,抑或是《诉讼》,卡夫卡笔下的每一道“门”都蕴涵着极为深刻的意义,这些“门”的每一次开/关都在不同程度上暗示/预示着主人公命运的改变。对于突然“被变形”的格里高尔来说,门里门外,是两个截然不同/通的世界,这也是卡夫卡对自己家庭体验的表现——他与父母之间永远隔着一道无法消失的“门”。 这两种《变形记》版本直接将小说情景画于封面页上,极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可以加深读者对文本的印象。 尽管卡夫卡坚定地认为《变形记》中的甲虫本身是“不可画出”的,但后来的许多封面设计者仍致力于表现这只甲虫形象。在中国,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佳作丛书》系列,其中《变形记》封面上是一个孤独的男人轮廓,对着一个既像窗户又像门的图案,最上方是一只黑色的多腿甲虫。这寥寥几笔所刻画出的虫子虽不具代表性,但由于这是中国较早公开发行的《变形记》单行本,直接影响了《变形记》汉译本封面的设计走向,此后越来越多的“甲虫”出现在《变形记》汉译本封面页上。 在西班牙,1991年的《变形记》封面画巧妙地糅合了多种元素,组装成一只复杂无比的怪虫——一张苍白的人脸上,两根又粗又长的触须十分醒目。这只怪虫以蛇身为颈,以多星瓢虫的壳为背,背壳间又伸展着一对黑白相间的蝴蝶翅膀,整个身体由多条细腿支撑起来,似乎要往前爬行。独具一格的多元拼贴使这只怪虫既恶心又惊人,虽然明显违背了卡夫卡“千万别画”那个甲虫的意愿,但它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将读者深深吸引。设计者的构思堪比卡夫卡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不过如此极端怪异的组合似乎与卡夫卡笔下的甲虫相去太远。 另有两幅《变形记》封面画突出“变脸”主题,极具表现主义色彩。1989年法国版的封面画是一张极度扭曲变形的脸,这张脸似人非人,似虫非虫,似鸟非鸟,丑陋无比。画中男人的表情充满沮丧与绝望,双眼里流露出无助的失落,象征着格里高尔对于变形遭遇的无能和无奈。1993年的版本则直接以著名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代表作《呐喊》为封面图。蒙克曾如此回忆《呐喊》的灵感来源:“我和朋友一起去散步,太阳快要落山时,突然间,天空变得血一样的红,一阵忧伤涌上心头,深蓝色的海湾和城市,是血与火的空间。朋友相继前行,我独自站在那里,突然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和战栗,大自然中仿佛传来一声震撼宇宙的呐喊。”这样的经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卡夫卡常常感受到的恐惧感和担忧感,将这幅画作为《变形记》的封面,可谓实现了表现主义文学与表现主义绘画艺术的完美合体。 在后来另一个法国版的封面画上,空荡晦暗的房间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床边,埋头哭泣,他的背影显得十分孤寂。这对于《变形记》的初读者而言,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2005年的德国版,又是一张复杂的组合图形,一只倒立的寒鸦张开翅膀缠绕在一个男人头上,寒鸦之眼正好对应成为男人的眼睛;两瓣虫壳夹在男人左耳上,它的一条细腿伸进男人嘴角,另一条则伸入男人颈内;另一只甲虫则像领结一样系于西装革履的男人胸前。这幅画将寒鸦、卡夫卡和甲虫混搭在一起,是《变形记》封面画的又一经典之作。 2012年德国出版的《变形记》封面以素描画表现父母和妹妹的形象——父亲是刻画的重点,他头戴圆帽,双眉紧锁,目光向上,并紧咬双唇,十分强势专横;母亲消瘦无比,眼窝深陷,神情冷漠;妹妹的侧脸也有几分沮丧和难过;右上方应该是一幅“格里高尔(或卡夫卡)”的半身像,却只见西装不见脸(寓意“消失的儿子”或“消失的哥哥”)。2013年意大利版的封面“彻底背叛”了卡夫卡的意愿,将一只倒挂在屋顶的巨大甲虫作为近景,远景则是“父母和妹妹”,他们三人相互依偎着,站在门口望着这个吓人的怪物。 《变形记》中最残忍的莫过于父亲用苹果疯狂“轰炸”格里高尔的行为,这一场景也在多幅封面画中得以展现。2004年的西班牙语译本封面上就是一只背部被苹果砸中的甲虫(它的脸与卡夫卡的脸十分相似),它那许多条可怜的细腿艰难地撑着受伤的身体。2014年的封面画则直接再现了格里高尔“被轰炸”的过程,房内床上、地板上都有“苹果炸弹”,一只巨大的黑色甲虫无比恐慌地躲在床底,而门外身着黑衣的父亲依然手持苹果,似乎还要朝格里高尔砸来。若将《变形记》作为一部表现主义的小说来看,卡夫卡对于“父子关系”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强悍的父亲残暴地伤害孱弱的儿子,“苹果”是他的武器。《圣经·旧约》中亚当和夏娃因偷食苹果而犯“原罪”,被赶出伊甸园;格里高尔因遭遇苹果轰炸而导致了最后的死亡,“苹果”在这里所具有的隐喻性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近年来,台湾地区涌现出多种《变形记》译本,这些译本封面的设计者也力求创新,将人像与甲虫躯壳相结合是其最大亮点。2013年李豫译本的封面画上,一个青年男子的左半身和一只甲虫的右半壳相结合,而2014年彤雅立译本封面图则索性用半只甲虫代替卡夫卡的左脸,突出“半人半虫”的“变形”意味。 新时期的《变形记》封面画一如既往地突出“变形”主题:2014年,一本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封面将“变形记”的英文字母“META⁃MORPHOSIS”拆分后加以艺术化,13个字母拼成一个抽象的甲虫轮廓;2015年德国版本封面上,一只蜜蜂似的巨大昆虫从一个赤裸的人体中飞出;同年的西班牙语译本上,一个三头七臂、胡须茂密的怪人以扎马步的姿势立在墙角,三张脸表情各异,又都充满恐慌和惊诧;2016年葡萄牙语译本封面上则是一只黑白条纹的怪虫匍匐在地,它细长的触须试图去触碰高高站立的妹妹,却遭到了拒绝。 总之,一个世纪以来,《变形记》版本封面经历了丰富的演变过程,主要围绕“作者意图干预——作者形象展现——再现故事情节——刻画甲虫形象——表现主义倾向——后现代化拼贴”这些理念而发展变化。《变形记》文本改变了世界文学风格,其副文本——封面画也参与了世界绘画风格的转型。从“卡夫卡式文学”衍生出“卡夫卡式封面”,这恐怕是卡夫卡生前不曾预料到的。至于“格里高尔到底变成了一个怎样的存在物?”,这个“世纪之问”恐怕拒绝固定答案。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设计者笔下就有一千个《变形记》封面及一千个格里高尔,而这或许也是卡夫卡提醒施塔克“千万别画”那个甲虫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伴随着《变形记》封面画的显性演变,《变形记》文本意义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诸多隐性的改变。在这一隐一显的对照中,“卡夫卡意志”始终若隐若现,“卡夫卡干预”似有若无,“卡夫卡式理解”愈加扑朔迷离。于是,怀着破解封面画谜题的初衷而从“文本外”走来的我们,很快就又进入了更深更复杂的“文本内迷宫”。 被《变形记》文本深深吸引的还有许多艺术家,台湾著名导演、演员、舞蹈家吴兴国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吴兴国根据《变形记》推出创新京剧《蜕变》,他结合中国京剧的戏服、脸谱、雉翎以及昆曲的唱腔和舞蹈,完美地将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与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糅为一体,将“甲虫”形象活灵活现地置于观众面前,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也使卡夫卡笔下的“变形”更具东方意味。或许,这就是“卡夫卡的变形”,也即卡夫卡的魅力所在吧。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7年01月04日1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