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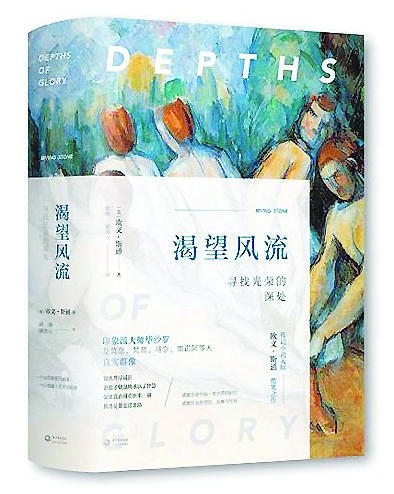
“没多大工夫,他就通过了海关的检查,提着那两只旅行皮包沿码头朝布洛涅车站走去。”欧文·斯通在《渴望风流》的开篇写下这句话,让我想起了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开场白。可是,没有一句能像《渴望风流》的这句一样深深打动我。因为那让我想起了我的过往,时间回到五年前,当我第一次毅然决然地从湖北小城来到北京的时光。真是没多大工夫,我就通过了西站的出口,提着行李包一个人融入人海茫茫。
几乎同样的年纪,一代印象派大师卡米耶·毕沙罗离开圣托马斯来到艺术之都巴黎拜师学艺,25岁的青春,满身意气风华,眼前的巴黎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梦。在最强壮的人生里,怀抱梦想,也许是这世上再美好不过的事了。尽管毕沙罗的身后还有一堵堵围墙——母亲拉舍尔对他从事艺术事业的强力反对,父亲对他子承父业做一介商人的期许。
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去追随自己的心——“思想和精神的饥渴比肚子的饥渴还要强烈。”
安东·梅尔比、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雅各布森、皮埃特……他在巴黎求索的路上并不孤独,有那么多的伙伴欣赏他,支持他,更重要的是,给他精神上的慰藉,即使在最初的困顿日子,也不至于像个穷艺术家一样潦倒,而是体面地在自己的画室中自由地铺展图画,随心所欲地去到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地方作画。
生活待毕沙罗是不错的,至少,他比梵高幸运,幸运的不仅仅是他有一个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支柱,还有一段冲破藩篱的甜蜜爱情。只是,不知当他在陷入那段无可自拔的爱恋中时是否还记得他第一次拜访柯罗时,临走前柯罗嘱咐他的那句话:“还有一件事,把这话当作一个老人的忠告吧。千万不要结婚,你要走的道路太长太艰难,家庭的负担和责任沉重得很,会妨碍你完成自己的工作。”在家庭与爱情之间,他当然选择后者,即使他爱母亲,爱绘画,即使一切都变得无法调和了。
他的一生注定会有两场战争,一场与他的母亲,那个直到生命弥留之际都未彻底放下偏见,与他的妻子朱莉握手言和的倔强而固执的母亲。即使在他们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也只是非常不情愿地来到他们的住所,待了屈指可数的五天时间,且始终无法正视这个曾经的佣人,如今是儿媳的角色。
毕沙罗的另一场战争,是与沙龙的对抗,与权威的对抗。1874年,他的好友莫奈振奋地向他提议,与其受制于保守顽固的沙龙,不如自我解放,搞一个巴提纽尔独立派的画展。这与总是被沙龙拒之门外的毕沙罗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这群人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呼朋引伴,着手一个为期十年的无名艺术家协会。
有人赞同,就有人反驳。爱德华·马奈和吉耶梅就送来了嘲笑和暗讽。但这声势依然势不可当,莫奈、西斯莱、德加、雷诺阿、塞尚、布丹……这一群为献身艺术的人,拥有着如他们的画作般旺盛而炙热的生命力,他们殚精竭虑追求新的光色效果,新的绘画笔触,真诚地寻找美与现实的结合,他们逆势而往,旌旗猎猎,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征程。
结果却并不如人意,几次展览,他们都失败了,还招致恶劣的抨击和谩骂,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燃烧赤忱,为艺术史上一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的名称“印象派”而举杯庆贺。
书的结尾,年届古稀的毕沙罗走进1900年“伟大世纪博览会”的大厅,回想到1855年的万国博览会,25岁的自己,一个双眼澄澈、赤手空拳的青年,站在从全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像银河系那样多的绘画面前,惊慌失措,如同被雷电击中,一股颤栗感袭遍全身。如今,他目光淡定,超然回望过去的一幕幕,为能自信成为其中的一员,不知走了多少路。但就像他所说:“如果我必须重新来一遍,我还是要走这条路……”
《爱乐之城》中米娅对塞巴斯蒂安说:“人们会因为你的音乐热情而来,人们喜欢见到充满激情的人,他们会记起遗忘的东西。”
嗯,感谢这本书带给我们关于艺术家的苦难与辉煌,以及他们给我们的像疯子般的热情。
(《渴望风流》 [美] 欧文·斯通/著,刘绯、褚律元/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