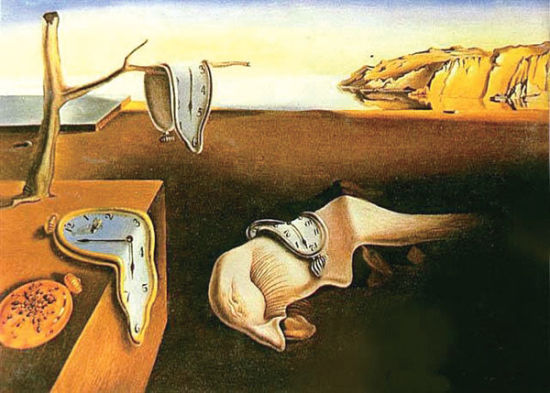
先锋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可谓风生水起,声震一时,几乎到了无人不谈文学,谈文学必谈先锋的地步。19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在经历了一个文学荒芜的年代之后,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阅读、接受生机。“纯文学”的理念畅销一时,彻底击溃了以往的先验理念决定论。而先锋文学就是“纯文学”思潮结出的一枚无比惊艳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硕果。洪峰、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一个个耀眼的名字在时代读者的心中闪烁。1993年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的同学就开始了对先锋作家作品的模仿性写作。我曾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余华的作品,买来余华的小说,整天把余华挂在嘴边。后来余华不写小说了,我就读余华的音乐随笔,同样激动无比。记得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与一位踢足球的球友交流余华,他很不屑地问我,读过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吗?读过“鲜血梅花”吗?我才意识到,还有人比我更痴迷余华。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接受, 一部作品就能让作家名扬天下的文学黄金时代,一个先锋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 事实上,余华就是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世人知晓,尤其是为家乡海盐县人所知。余华的《现实一种》《鲜血梅花》显现出一种惊人的、血腥的“冷”与“酷”。同时代的洪峰、马原、孙甘露、格非、叶兆言等,则显出一种强烈的语言形式试验的味道,尤以马原的“叙事圈套”为人所熟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这是马原在《虚构》开头的话。“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几乎成为马原的文学“名片”,为研究者频频引用。洪峰在其先锋文学作品《瀚海》中,这样开头:“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诗意的理解。我不是没进行努力,只是发现那样做的结果总是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我的结论是也只能是:生活就是生活,一切就是一切。这就决定了我的故事很难讲述——没有诗意。而诗意对于故事和人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之所以还要讲它,却正是出于这种没来由的自信——”事实上,无论是马原、洪峰,还是其他先锋派作家都有进行语言形式实验的强烈追求,特别是对叙事学理论的迷恋。“我”不仅作为叙述人身份参与故事的讲述,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与其中一分子,而且还时不时地跳出来,力图“解构”故事,以制造故事叙述的语言迷宫。先锋文学的语言形式实验及其创新性探索,不仅进一步加速了以往陈旧文学理念的瓦解,而且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建构、“纯文学”理念的艺术本体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先锋文学,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座重要丰碑,是继创造社、“新感觉派文学”等具有异域文学之风的、具有强烈而自觉语言形式追求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艺术形式实验。这对于“文以载道”理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学而言,无疑是一次极为珍贵的语言文体大解放、大探索,其意义和价值不仅显现于今天,更将深远辐射于未来的中国文学。 物极必反。先锋文学在1980年代后期逐渐陷入了语言形式实验和叙事迷宫的文字陷阱而无力自拔。余华的一些以数字命名人物形象的小说和孙甘露创作的《褐色鸟群》等先锋文学,在体现较强形式试验气息的同时,也出现了意义建构和读者接受的困境。因此,应对困境,寻找生机,就成了先锋作家的新命题。先锋文学迎来了新的创作转机。余华的《活着》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典型,是先锋文学从语言形式实验困境中走出来,向中国古代叙事传统回归的成功作品。余华一方面从血腥的暴力叙事中走出来,不再书写“鲜血梅花”,不再做故作高深的文字游戏,而是在简洁、质朴、流畅的叙述中,讲述一个个人性温暖的故事。当然,这里面依然处处显现着原来的“先锋文学”的“血雨腥风”,但已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转化和升华,凝结为一种历史的风霜,一种人性与制度之恶。在历史的风霜深处,在人性之恶的另一侧,余华书写出了人性深处的至爱与温暖,一种抗衡命运的“活着”。不仅余华如此, 格非、叶兆言、苏童的小说在延续先锋文学格调的同时,也出现了向中国传统叙事风格的回归迹象和某种新历史主义的叙事风格特征。而有的作家,如洪峰、马原等则出现了先锋作品无以为继、创作中断的现象。 非常有意味的是,本来文坛上都以为先锋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先锋文学的创作已经终结了,但是新世纪以来,原来的先锋文学作家,纷纷拿出了新的重要的作品,再一次向文坛展示了这一代人的顽强生命力,宣告先锋文学并没有终结,先锋作家依然充满着旺盛的创作活力。余华的《兄弟》几乎是一鸣惊人,之后是同样广受非议的《第七天》。苏童《米》之后,推出《河岸》《黄雀记》,格非则推出《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的“江南三部曲”,马原则有大部头的《牛鬼蛇神》,一时间,纷纷现身于文坛,可谓是“前度先锋今又来”。实际上,余华的回归,并不是很顺利,而是经受着来自自我主体内部的创作转型的困惑和来自外部读者、批评家的强烈质疑。应该看到,余华在新世纪出版的长篇小说《兄弟》和《第七天》,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叙述风格,同时具有了更多的来自当下多元紊乱现实的芜杂气息,是有着很强的批判色彩的,部分段落依然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但是,文学毕竟不是现实的模仿,更不是现实的亦步亦趋,文学需要的依然是余华所倡导的“想象力”,是从床单变成“魔毯”的灵动艺术飞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格非在“江南三部曲”的艺术成功,获得不同年龄段读者和批评家的喜爱。尤其是《人面桃花》里面对中国百年来,乃至是人类“乌托邦”、理想国、大同世界的深刻历史反思,与主人公汹涌澎湃的情欲交织在一起,塑造了集革命崇高理想、急剧变动的社会力量、深不可测的历史命运与个人流动的本能欲望于一体的复杂个体存在,体现出人性、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深度精神意蕴。苏童的《河岸》在延续以往枫杨树系列主题及其少年形象建构的同时,也开始新的探索,即在“河”与“岸”之间的夹缝中书写出了一切都是“空屁”的“新历史主义”精神深度;《黄雀记》则再度回到了少年情感记忆的叙述主体中来,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犯罪情感记忆成为两个少年和一个少女一生挥之不去的精神梦魇,演绎出了一出出惊心的生命舞蹈。丢魂,成为小说许多主人公的精神问题所在,如何招魂就成为小说人物所有行为逻辑的核心秘密所在。苏童以这种隐秘的方式呈现出了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问题所在,这是一个丢魂的时代,如何寻找灵魂、如何安放灵魂是我们共同探寻的时代精神问题。马原的《牛鬼蛇神》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其对先锋的“长袖善舞”,虚虚实实塑造了许多灵异的传奇故事,中间穿插着现实人物之间生死相依的生命情谊,体现了马原对新世纪文化语境下先锋叙事的深刻思索和熟稔运用。正是这些新世纪先锋文学作品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先锋文学的新活力。 先锋文学的魅力与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这些先锋作家的创作上,而且还体现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先锋文学理念、先锋文学精神,延续为新一波的先锋文学创作。我姑且称之为后先锋文学。所谓后先锋文学,是指在80年代先锋文学影响下的中国“70后”作家的先锋文学。正如开始我提到的先锋文学在1990年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刚刚开始起步的“70后”作家,几乎都是从模仿先锋文学开始起步的。最早出场的“70后”美女作家群中的东北作家金仁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或许准确地说,金仁顺的早期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先锋作家的精神理念,创作出了具有金仁顺自己独特个人精神风格的后先锋文学作品,如《名叫马和》《松树镇》《五月六日》,都具有类似于余华般冷酷和难以捉摸的叙述迷宫的精神气质。“马和是在大街上发现另一个马和的”,在某种意义上逼近了余华和马原。可贵的是,金仁顺的先锋叙事同时注入了来自自我生命体验的精神意识,这一特点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春香传》中得以延续。“70后”作家刘玉栋、李骏虎、陈家桥、李浩、范玮、东紫等都创作过先锋文学。刘玉栋在90年代的创作曾经有一个左冲右突的尝试期,其创作的《傻女苏锦》《绿衣》《蛇》等作品表现出了一种先锋性、魔幻性的审美风格。可贵的是,刘玉栋没有延续,而是从生命体验出发创作了《给马兰姑姑押车》《葬马头》《我们分到了土地》等一系列飘逸灵动而又意味深长的乡土文学精品,获得广泛赞誉。李骏虎的文学创作历程也有过这样一个从模仿先锋文学到转向乡土大地写作的审美嬗变历程。东紫早期作品的先锋性精神气质特别强烈,《饥荒年间的肉》显现出类似余华和莫言的先锋魔幻精神气质,后来转向“病态问题型”写作依稀可见某种先锋的魅影。能够始终坚持先锋精神理念、持续进行先锋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是李浩和范玮。李浩在《将军的部队》中通过一个讲述人的口,叙述了一个独特将军及其部队: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是的,“那些原本白色的,现在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就是将军的部队。”小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无比沉重的故事,压迫着读者的神经,近于窒息。在李浩的故事里,始终有一个巨大的“父亲”形象的存在,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延续了这一主题。山东作家范玮是一位有着自觉先锋艺术追求的作家,其作品《刺青》《孟村的故事》等显现出惊人的才华,遗憾的是作品创作数量不多。 2012年“铁葫芦丛书”的《中间代》小说作品集横空出世,向读者展现了一批新崛起的“70后”中间代的后先锋文学作品的精神风采。苗炜的《星期天早上的远足》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关于“后先锋”精神气质的奇幻故事:“我发现时间真是一片混沌,我无法理清季阳这些年的生活轨迹,有些事前后颠倒,有些事真假参半”,“我说服自己,季阳没有骗我,她只不过把她的想象跟我分享,如果她需要一个人充当她的观众,好让她亦真亦假的表演更好的进行下去,我倒不在乎被她选中当这个观众”。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设置的叙事迷宫不仅把作者自己绕进去了,就是读者也陷入了迷茫,到底这位主人公的“远足”是真是假,乃至“季阳”这个人是真是假都让读者生疑。或许,故事已经走出了是真是假的问题,已经出离人世间的尘嚣,现实的真假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心灵中的精神存在问题。这在无意之间已经溢出了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那种或血腥或魔幻的精神特质,而走向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亦真亦幻的、幻真并存的后先锋精神意蕴。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阿丁的《你进化得太快了》,小说讲述了一对恋人决意脱离现代人的生活轨道,重回与大自然万物一体的原始人生活的故事,“我的脑子已经顺应了自然,甚至可以说,我的脑组织我的脑神经都不再是人类的脑组织脑神经,而是一棵随风摆动的树,有风吹过的时候就顺势而动,当风停止也随之静止。没错,现在我流血了,我仍然有痛觉,但这已经不是人类的痛觉,而是植物的痛觉,动物的痛觉,你见过一株被砍伐被割断的植物哭喊吗?你见过一只断了腿的狼哭哭啼啼吗?没有。它们只是适应,适应一切自然发动的兵燹,在漫长的让人绝望的逆来顺受中无声无息地调养,无声无息地进化。”小说在看似荒诞无比的叙述中,细致真切地描述出了男主人公回归大自然的“退化”历程, 同时点出了一个无比沉重的生态主题,“我再也没见过比你们人类更可笑的生物了。就这样你们还敢宣称自己是高等生物,你们还敢说直立行走是非智能生物迈向智能生物的伟大标志?笑话,真他妈是个笑话。你们藐视自然,你们砍伐林木,你们更改河道,你们用大坝让洄游的鱼断子绝孙,你们用水泥一样的脑袋铺设水泥的道路,覆盖小草的生长,填充昆虫的洞穴,你们让其他的生物绝望,总有一天,最终绝望的一定是你自己”。从李浩、苗炜和阿丁的作品,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在新世纪在叙述主题、叙述方式、叙述内容等方面的变迁,即已经从“60后”一代作家的“先锋文学”发展演变为“70后”一代作家的“后先锋文学”。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30年的审美嬗变,既有来自“60后”一代作家自身的先锋文学创作的自我演化、转型和创新,又有着来自“70后”一代新作家对前辈先锋文学的模仿学习、借鉴和突围,已经从冷酷、血腥、魔幻,逐渐走向了日常与现实缝隙之处的裂痕性、破碎性、后现代性的后先锋写作。而在这30年间,不变的是永恒的“先锋精神”,即求新、求变的异质性精神维度的追寻。从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带给我们一种永恒的“异”,“常”中之 “异”。正所谓,永远的先锋,永远的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