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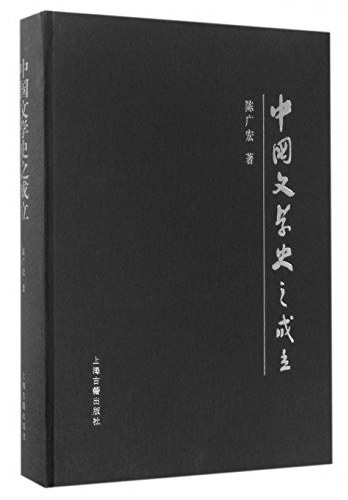
《中国文学史之成立》,陈广宏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98.00元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书写活动逐渐兴起,一百多年来在文学教育、文学研究以及整理文化遗产、铸造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学界对此已有反思,即为“文学史学”的展开——可粗略地分为“文学史理论”及“文学史学史”两个方面的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展开“重写文学史”大讨论,人们才比较深入地思考文学史书写活动的本质和意义,进入“文学史理论”的探索。相对而言,“文学史学史”的研究起步更晚,直至21世纪才有直接以此为题的专著出版,如任天石《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董乃斌《中国文学史学史》等。此外,如戴燕《文学史的权力》、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重要专著,或着眼于权力,或偏重形态,或回归现场,详加考论重要的文学史家及文学史著,各自从不同视角精彩地勾勒了中国百年文学史书写的起承转合。可以说,尽管这一领域似乎仍有很大的学术空白可供填采,但如果仅仅只是拾遗补缺,势必难以独树一帜,必须扩大视域才能有所创获。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之成立》,即堪称该领域扛鼎之作。
通读该著,最突出的感受即中国文学史书写考察的地理尺度大幅延展。中国文学史之由来,一是有中西文化交流,二是有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日本中介,故欲深入研究,当同时考察近代西方和明治日本。这虽是老生常谈,但此前却无深入、全面的专著,陈著将这一领域推向新的高度,实在可喜。在这样的视野下,书中提出不少新颖的观点,弥合不少矛盾的现象。同时,该著考察文学史的成立,不只着眼于体例、结构、书法、史观等叙事层面的问题,还扩大学术方法的视野,使全书带有概念史研究的色彩,指出“文学史”是一种知识体系,是西方文化近代转型的产物,是近现代西方思维框架的组成部分,是“文学”民族化和审美化的结合。陈著内感应着“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外绾结着现代学术制度的空间传播,呈现出极为宏大的格局和整然彰著的架构。
二
不少著作出于逻辑需要,或为了观照体系的完整性,往往会牺牲某些局部的原创性;反过来,另一些著作却是散钱失串,缺少整体架构,读来令人目迷五色,不知其指归。陈著则同时兼顾了“大判断”和“小结裹”。正文三编九章,或考掘相对稀见之史料,如据新发现的斋藤木文学史讲义立论,据“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相关文件勾连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上海与欧洲汉学界的联系;或考论如赤门文士、太田善男等学人,他们或许算不上学术史上的明星,却无疑是中国文学史学史中的重要人物;或考释曾毅编著文学史这一被人遗忘的学术公案。可以说,每一篇都不是点到即止的泛泛之论,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在每章的专题之外,作者以长达65页的序章和共计18页的三篇概说,将散钱归索,形成一整饬的架构。至于中国文学史成立过程的翔实信息,则由书后所附《中国文学史著作编年简表(1854—1949)》呈现,简表与正文之间,犹如太史公《史记》创立十表与纪传互见,保证了史实的完整性,又进一步支撑了唯陈言之务去的原创性,令全书有峻洁之美。
跟随陈著的架构,中国文学史之成立过程彰然可见。第一阶段是文学史书写从近代西方到明治日本的传播,可谓是中国文学史的“史前史”,即第一编《明治日本:新旧汉学之间》的主要内容。以大学分科为标志的现代学术制度之建立、以赤门文士为代表的泰纳文学史观的引入、以狩野直喜为代表的中国小说戏曲史研究的发端,正是明治日本学者中国文学史书写活动的三个标志性事件。陈著借助日本学者中国文学史著由粗转精的显性表现,挖掘出日本汉学由古向今转型的隐性因素,展示了实证主义思想与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普及和狩野直喜完成新汉学向现代学科转型的过程。可以说,没有这个“史前史”,就无法精准把握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第二阶段是晚清中国对明治日本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移植,即第二编《清末民初:新知的移植与调适》的主要内容。本编三章分别将林传甲置于“明治日本学者的文典及修辞学——西方古典语文学”的脉络中,将黄人置于“日本明治二十年以来的文学论——英国19世纪文学观转型”的脉络中,将曾毅置于“新汉学者的文学史模式——法国泰纳的文学史模式”的脉络中,都是学界未曾展开的,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早期中国文学史著的影响源:从外在学科构架到核心观念,从具体的观念、理论再到相对完整的文学史体系。
第三阶段是民国时期文学史体系的本土化实践,即第三编《胡适之后:文学史建构的多维拓进》的主要内容。“五四”以来,在胡适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进入新的阶段。“纯文学史”和“俗文学史”的兴起,皆彰显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新动向,作者特别指出这两种文学史书写的背后,仍有日本学者的影响。全书最后一章专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至此中国文学史体系完成本土化。
三
上面抽取中国文学史成立的框架,不免掩盖了作者精彩的思辨,尤其是细节的考证,可以说上述整个大框架皆建立在大量外语与中文文献融汇及严谨的考证之上。比如我曾认为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是明治新学科体制的产物,因为末松氏另有《希腊古代理学一斑》,而“文学”“理学”正是明治新学制中的两大学科,故题中“文学”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而非“‘古文’学”。而陈著特意指出末松氏《支那古文学略史》实是其在英国的演讲,所著乃学习欧洲历史编纂法的产物(第70页)。正是“英国”这个关键信息,将末松此著放回欧洲的学术场域来理解,避免不必要的联想。这样的例子很多,粗看起来无关宏旨,实则考据精细而能见其大。而有些启人深思的段落,几乎能引出一篇专题论文,甚至作为硕博士论文的题目。
如书中考察“文学”概念的形成,这个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文章、文辞及文学等概念有交叉有分别,极易引起混淆,一不注意就会循环论证。有人认为孔门四科的“文学”,宋人注作“文章博学”,故已包含了literature之义;也有人认为至迟在《世说新语》的“文学”中即有此含义。至于晚明以来传教士的译词,或用“文学”对译rhetoric,高一志用来对译philosophy,林乐知用来对译education,高丕第则用来指“语言文字之学”,在具体语境中并不易判断是否literature的译义。陈著对此有大量的辨析考据,认为“国别文学概念的出现,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文学史观念得以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作为跨语际的转换,像东京大学那种国别文学学术体制的形成,正可看作是新概念在制度上的临界”(第39页)。这个判断为“文学”概念史的研究制定了一个标准,可以防止拼命拉长中国“文学”(literature)概念史的冲动,为文学史、学术史、概念史的研究都提供了一个参考和界限。
再如,书中指出古文运动以来,“文章”一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亦已指出:“周濂溪称文以载道,所以显文章之大用。而彦和则论文原于道,所以探制作之本原。”陈著并进而追问其背后思维结构的演变,认为自《周易》以来,“文”是自然之道这种“神理”的呈现,基于对此宇宙之自然构成法则的认识,注重语言文字形文、声文等组织构造,是中世文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古文运动以来,“道”已转为伦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伦常秩序,因而文学观的重心,由关注文学如何表现的形构论,向文学表现什么的价值论的范式转换。故最终将文道关系作了明确的划分,很好地阐释了中古与唐宋文学演变问题,也阐释了“文章”与“文学”(literature)的区别。
此外,如引用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译本时,随手指出文中两个外文书名的疏漏及其通行中译书名(第5页)等细节,更在在显示作者的严谨与功力,仿佛散落四方的珍珠,每每令人于不经意处收获惊喜。
总括而言,陈著以45万字之篇幅,揭示出“文学史”这一近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来龙去脉、基本结构、价值基质,集中探究这一知识体系向东亚传播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途径,展示其中过滤、改造、解构、重塑等种种经验,架构俨然而陈言务去,考证精细而能见其大,洵为充实而有光辉的探索。
“充实而有光辉”之语出自《孟子》,清人章学诚曾移用作学术著作的标准,近人严耕望在其《史学三书》中也提出以此为史学论著的标准。充实,就是要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光辉,是比较高的境界,一要有见解有识力,二要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这两个词其实是杨联陞称誉严耕望本人的评语,只不过严氏在书中隐去不说而已。我觉得这句话也不妨移来评价陈广宏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