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体”于笔尖的精神创痛——田耳小说的底层精神书写
|
底层的关注与描绘其来有自,自新文学诞生伊始,当时所提倡的“平民的文学”,正是今天所谓“底层文学”的先声。田耳小说里对人的精神世界各个层面的描绘,尤其是对底层人们各种精神创痛的探索,为这类文学开辟了新的路向,他的创作,未来值得期待的还有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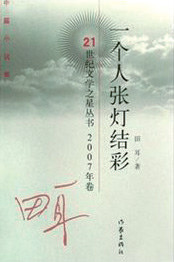
去年,上海的《青年报》曾经对作家田耳做过一次访谈,名为《现实的茧太厚,想破茧而出越来越难》。在访谈里,他谈到十几年以前,当他还在故乡湘西凤凰老家县城,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做的是和文学与小说创作无关的事。他谈到:“如果你在一个小县城生活,没有工作,想以写作成为作家,不混出来,你就是笑柄,混出来,你就是作家。”这种感觉,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的确不能算是多么美好。而对于愿意从事写作,希望以此为终生职业的写作者来说,内心的焦虑与痛苦也是可以想见。好在田耳并没有被“现实的厚茧”束缚住,他最终还是“破茧而出”,而刺破这重厚茧的依然是他手中的笔,凭借《一个人张灯结彩》这个优秀中篇,他在2007年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成为鲁迅文学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这个奖项的获得,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对其创作技艺的奖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虚构的那个文学世界的赞赏与肯定。然而,奖项的结果,从世俗眼光看,可能带来的是更多的实质性的物质与生活处境的改变。这种改变延伸到前方,给作家在现实社会中虚构自己的王国提供了世俗的合法性。也使得作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使用自己周边的生活,一笔一画地建构起他所理想的文学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多年的小城生活,对他的创作来说,是一笔不错的财富。
在田耳看来,他生活了许多年的小县城,那里的人们总是不相信身边的人,只肯相信一无所知的远方。远方对于人们总是有种蛊惑人心的力量,而当如果真的有个曾经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成为那个一无所知的远方的一部分,他们日后的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将为这个“远方的人”所占据。而在他们身边生活过的作家则与之相反,他们并非对远方没有兴趣,只是他们更愿意浸淫在身边的人与事之中,为自己的小说王国添砖加瓦,他们也以此与生活在他们身边的芸芸众生区别开来。而在我看来,田耳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
田耳的创作,一开始就较多地着眼于他所生活的湘西家乡。提到湘西,人们更多地是将其与《边城》,与沈从文联系起来。似乎湘西给予人们的刻板印象就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淳朴和宁静。但在田耳眼中,他看到更多的是曾经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底层乡邻,他们局促在自己那一方天地中,他们的生存与死亡、欲望与满足、孤独与挣扎,都被他用略显犀利的笔端,挑开呈现在外面世界的眼前。而且这种田耳周边的生活,在他的笔下驾轻就熟。他也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外衣将其包装得或悦目赏心,或五彩斑斓,从而让他的小说的可读性极强。
田耳的中短篇小说,对于底层的关注始终如一,而且对底层的“灰色”生存境况的挖掘,也是他所擅长的描绘方式。获鲁奖的《一个人张灯结彩》里,警察老黄是个足迹专家,当警察当到50多岁,还是个足痕专家,却未能混上一官半职。他从一个分局调到这个分局,之后在一个理发店认识了一个手艺不错的哑巴女,又在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哑女的哥哥。由哑女又牵出钢渣和皮绊两个罪犯。钢渣和哑巴女发生了肉体关系后,相互间在内心也找到了依赖,但钢渣却又阴差阳错地和皮绊抢劫并杀害了哑女的哥哥。最后,老黄破了这个案子。 这篇披上了侦探外衣的中篇小说,其情节性和可读性很强。不过,如果除去侦探外衣,我们可以发现的是,这篇小说所写到的底层生活,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底层有很大的不同。以往我们所认为的“底层文学”,可能希望看到的是更多底层困苦生活的展示。然而,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田耳展示给我们的是人性中更多的挣扎和无奈,以及那份浸透在每个人心底,透彻心扉的孤独感。小说里的几个人物虽然都是生活在钢城的一个城市里,每个人都很难从他人身上获得温暖。老黄早年丧妻,惟一的女儿又不在身边,在业务上是一把好手,但其实他并未能有与自己可以倾心交流的对象,只能不时地去小于的理发店借理发之机适当放松,使自己的孤寂暂时得到缓解。哑女小于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小女孩的父亲不知所踪,他们自己经营一家理发店,却没有料到和一个潜逃的罪犯钢渣发生了关系,其孤苦无助的心也仿佛是找到了慰藉,这种关系好像是她的救命稻草一样,她只有死死地抓住不放,才能排解内心无尽的荒凉。那个答应回来找她的钢渣,在阴差阳错之间杀了小于的哥哥,而钢渣最终又被老黄擒获。小说最后的结尾,是年三十的夜里,小于在理发店门口亲手挂起一串灯笼,在等待那个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人。
可以说,这部田耳的成名作,是一篇另类的“底层作品”:我们在这篇小说中看到的不是一般底层人物生存的艰难,是他们那种发自本能的,无所依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可能不会如文人雅士所描绘的那般细腻精致,但质感朴拙同样也可以让人感动。可以说,田耳用这样的一篇小说,写出了“底层的孤独”,这种孤独使得我们在审视这些人的时候,获得了一种情感共鸣——毕竟人的情感具有天然共通性。
田耳在《一个人张灯结彩》里为我们展示了城市底层的孤独后,并不是一味循着这条创作道路重复自己。在另一个中篇《金刚四拿》里,他将目光投向乡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样貌的“底层”:这部获得2016年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提名奖的作品,用一种类似于荒诞和戏谑的笔法,重新思考了在乡村和城市的二元格局下,农村青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如何选择自处,以及这些青年在返乡之后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怎么被乡村社会再次承认,以便取得精神上的获得感。
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缘起的时候,田耳曾经感叹如今的乡村,“在乡下有一种现象,就是人老了,常常连抬棺材的青壮年都凑不齐了”,“我就曾见过有的人家,因为找不够抬棺材的人,就直接叫拖拉机拉走的。死去的人虽然看不到这一幕,但这让活着的人看了倍感凄凉。” 也正是基于作家对于如今中国乡村景象的敏锐观察和深切体认,田耳在《金刚四拿》里以“我”——残疾人——田拐的视角,塑造了罗家垭打狗坳进城务工后返乡的青年罗四拿。小说中的罗四拿与其父罗代本的矛盾冲突,既是天然的父子之间的代际冲突,也是某种意义的时代表征: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结果,要求城市必须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充实到城市各行各业当中去,而这些劳动力的来源只能是中国人数众多的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然而,作为曾经的农村支柱的青壮年农民兄弟,他们的离开,使得他们身后的广阔的乡村逐步呈现出“空心化”的态势,而乡村“人死无人抬”的情况也绝非个例。
《金刚四拿》里的罗四拿正是在上面所提及的背景下返回罗家垭打狗坳的,即使是经过多年的城里打工生活,他也并没有能够融入城市,成为一个“城里人”,反而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他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外乡人”。这种两难的处境,可以说在近些年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一困境,田耳在小说中为四拿找到了“八大金刚抬棺”,这种中国乡村葬礼上的仪式,通过他为大爹葬礼寻找“金刚”一事,为他赢得了乡邻的尊重和认可,重新在家乡获得地位——成为村长助理。这种认可,也对四拿精神上所急需的获得感给予了满足——有尊严的生活,恐怕是任何人都需要的。可以说,在《金刚四拿》里,田耳再次从底层的精神生活入手,将他们的精神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有尊严的生活和获得感的满足同样有普遍性的意义。
如果说田耳在《金刚四拿》里还可以以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调来回应四拿面临的困境,那么在他近期的中篇小说《附体》里,当他将目光投向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下岗失独家庭的时候,其笔触无疑是相当沉重的。小说让家庆以一个外人的身份介入表哥表嫂的生活后,他看到的是一个因失去独生子而濒临破碎的家庭真面目。在这个家庭里,痛苦弥漫在每个人的头顶,如挥之不去的乌云,压迫着每个人,性情懦弱善良的表哥,不仅要承受丧子之痛,还要面对同样经历丧子之痛而性情古怪的强势表嫂。家庆和林黎怀以及小李他们一起生活在表哥家里,虽然可以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但是一个人的痛苦却不能与其他人分享,人与人的沟通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尤其处于痛苦中的人们更是这样。表嫂似乎在家庆的身上看到了她早夭的儿子海程的影子,她几乎是强制性地把亡子海程的影子投射到家庆身上,家庆即使顺从了表哥的意愿,表面上扮演了海程的角色,可是这对他来说也是痛苦的——他的存在减轻了表哥表嫂的痛苦,那么他的痛苦又有谁可以体会。痛苦是人类共有的感情,不过落实到确切的每个人身上,很难说谁能体会到或者说愿意体会到他人的痛苦——每个人的痛苦有时候并不能通约。这篇小说结尾的时候,家庆终于还是没有坚持到最后,他离开了表哥家。表哥和表嫂也无法将痛苦生活延续下去,他们离了婚,并且又各自重新婚育。田耳在小说中没有让这种绝望且令人窒息的痛苦无限生长,他斩断了它,也为我们保留了希望的火种,毕竟痛苦本身没有意义,展示它也还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生活下去。
如果我们拉长一个时间段来看,对底层的关注与描绘其来有自,自新文学诞生伊始,当时所提倡的“平民的文学”,正是今天所谓“底层文学”的先声。田耳小说里对人的精神世界各个层面的描绘,尤其是对底层人们各种精神创痛的探索,为这类文学开辟了新的路向,他的创作,未来值得期待的还有很多。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