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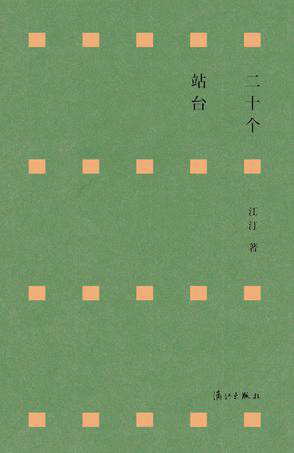
清晨挤在糟糟乱乱的人流和公交中,望着窗外北京早春盛开的玉兰和丁香,是一种绝美的对称。我喜欢江汀诗中的一句“带着自己全身的苍白,穿过北京黑暗的颈部”。对应于这里的现实生活,黑暗和苍白已经不是简单的反义,它们实际是一种相融和互为表里。当我默念着这句,心里也生发出另外一个词——灰蒙,它是北京涂抹在人们视网膜之上的色彩,我因它而得以重新阅读理解同时代人的写作。一种本能的体验在告诉我,我们都应该把自己凝固在此时此刻,此时此地。灰蒙带给人的不仅仅是疏离感,而是一种更大的团结。灰蒙不是退避,而是预兆。
在江汀的作品中,始终萦绕着两种生活经验的断裂和互融,很具有代表性。童年时的乡村生活与成年后的城市体验,他的很多作品都表现这两个不同居住地情感的摩擦和碰撞。似乎这种情愫早早地存在于诗人的精神内核里,并在多年的诗歌探索中渐渐发展成了明显的生存主题,一面是乌托邦式的田园共同体,一面是光陆流离破碎的现代城市之镜。两者在诗人的意识和潜意识里相互挤压、交锋、争夺。仔细翻阅诗集《来自邻人的光》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克制,连绵诗句背后的暗流,这是江汀最初写作的基础原点,进而渐渐铺展成其强大的内驱力。在一篇谈论自己诗歌生涯的文章中,他说:“最初,对我来说,写诗是一种私人性的自我救赎。后来,渐渐变成了一种敞开的日光下的见习。我的那些个人体验,已经直接地写在诗歌里,它们对我极其重要。”(《大写的处境》)
“乡愁的眼睛凝视漆黑的天花板”
对于“80后”这一代有乡村生活经验的青年来说,我们生长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背景下,和同龄人书写乡村体验的诗歌极为不同,在江汀那里,乡村(更多的时候是家乡这个词)是一个先在的、非空间存在的乌托邦设定,而不是具体的、充满个人体验的真实住址。然而正因为此,江汀的写作才显得尤为珍贵和与众不同,如果说每个诗人都是理想的乌托邦中的小小公民,那么江汀这种鲜明的立场表明从一开始,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境遇里,他坚定地走了一条最不好走的、回望的路。这种目光似乎可以对应于俄尔普斯回望的目光,家乡仿若身后那位美丽动人的欧律狄刻。在散文《文雅的歌尔德蒙》中,他说:“虽然我在诗艺上受惠于曼德尔斯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但我来自于一个叶赛宁的世界。我的乡村经验,如海子所说,‘今天的花椒树,使我健康,富足,拥有一生。’”
家乡是“归宿”,庇护所。家乡是力量,可以“阻止世界的本原从那里堕落”,家乡是需要被“思念”的,如此“我们才能显现出来。”家乡是“见过预兆”的神圣之地,童年的同义词是“幸福生活”,然而已经回不去了,是“不去提及”的事物。诗句充满了深深眷恋和哀伤哀悼的语气。家乡的属性在诗人那里的表达是“对我而言,家乡——是时间性的存在。家乡不在空间里,而在时间里(《星期一纪事》)”。江汀诗歌中童年的乡村生活是抽象的,诗人的目光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救赎色彩,然而也存在思想的矛盾之处,他希望家乡是一个永远停留的存在,并坚决捍卫这种立场:
“俄罗斯女诗人娜·苔菲有一首诗,先是描述了故乡的岛屿,描写了景色和一扇美丽的门,最后总结:‘我从来都打不开这扇大门!’远离故乡的女诗人表现的是乡愁和无力,而我站在她身后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但我从来都不打开这扇大门!’真相,就是在月光之下走过花椒树。像那些消失在历史上的兴致勃勃的预言家们那样,有一天,我也会骑着小煤桶消失在南方。”(《预言》)
拒绝打开家乡面目的真相,因为诗人对探访真相的态度是怀疑的,它不过是“月光之下走过的花椒树”。不愿做一个具体境遇里的人,而是要做一个预言家,家乡在江汀那里犹如一个魔法花园,在阿甘本看来,能够坚守住魔法花园乐趣的,只有处在游戏中的纯真的孩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是人类纯真的代表和守护者。
“城市在封闭,运河上有一片绿色的云”
诗集《来自邻人的光》中,从《他在公共汽车的人堆里》开始,诗歌的背景开始转移到了城市,意象也开始从乡村的风景变化成城市里的风物,出现了公共汽车,亮果厂,西直门,候车厅等词汇,当城市的意象开始出现在江汀的诗歌中时,其中的乡愁色彩更加浓厚了,情感也从最初淡淡的忧伤发展成了忧郁(如果把忧郁看做是在精神上比忧伤色调更浓郁的话)。有时对家乡直接的情感表达是怀念,并且和城市相互之间的对照和对比是明显的,甚至在一首直接命名为《家乡》的诗歌中,出现了哀悼。
和前一阶段的诗歌相比,如今对家乡的情感升华到了崇高的位置上,诗人说:“说到底,家乡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有一次,在书堆里我找到了一段文字:‘诺斯替……让他回归到他的光明的故乡中去……’之后,我继续读着那本书,困倦之时,我沉沉地睡去。那一次我又做梦了,我梦到自己的书桌在漂浮,没有前,没有后,没有上,没有下,没有肯定,没有否定。我的结论是——让我紧紧抱住自己的梦境,抱住它,抱住它在家乡生儿育女。”(《星期一纪事》)
然而那“光明的故乡”毕竟是一场“梦境”,终于在某个时刻,它和“徒劳”站在了一起。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的形象从来不是自足的,更像是一种衬托,矛盾之中表达的是一种对遗失家乡的惋惜,并且在词汇上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和对立,与“家乡”一词在意义上互文的词有童年、田野、老人、夏天、绿色。相应地,围绕“城市”一词聚集起来的表达有寒冷、苍白、黑暗、冬季。诗人并不避讳象征的诗歌技艺手法,与对前者所抱有的崇高感不同,词语色彩暗淡,用后者目光眺望的世界,是无望的,在一首以《西直门》命名的诗歌中,起句的表达就是这样:“我曾感到很深的悲哀。十点钟,店铺关门,街上开始变黑……我两次在这里做同一件事。世界像是一个黑暗的小房间。”
从“发光的童年”到“发光的塔”
还是那句话,在江汀的作品中,始终萦绕着两种生活经验的断裂和互融,而连接两者的桥梁就是“光”意象。在《光的寓言》中,江汀描述了他对前辈诗人孙磊的相遇和相识,在未曾谋面之前,它是使心灵朝向同一方向相互靠近的原因。“事实上,我自己也是同样与‘光’有缘分的写作者……我知道自己是孙磊的一位回应者。”除了他对孙磊的倾心赞美之外,他的诗歌还另有一个为他独有、别有深意的意象,那就是“雾”。
雾气堆积在地铁入口
像受伤的动物在蜷缩
车厢里,人们的脸如此之近
他们随时能够辨认对方
——《悲伤》
呼吸伴随电梯缆绳的摩擦声
忧虑跟着我回到这一层
雾气进入了走廊,像墨汁被稀释。
——《我熟悉这个小区的老人》
将有一个人,如赴约一般到来
提着童年的灯笼,在田野的雾气里
捕捉敏锐的死亡。
——《家乡》
光与雾,日与夜,城市与乡村,异地与家乡……迷雾,大雾,就是天空给予同时代人的灰蒙之感。而江汀追寻的光,已经悄然地面向了一种广阔,如诗集名从中截取的那句话,“他开始观察来自邻人的光。”
(《二十个站台》, 江汀著,漓江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