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语
东君是从先锋小说出道的。而且可贵的是,东君是至今依然罕见地还保持着先锋实验热情的“70后”作家。他的《树巢》是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退潮之后一个重要的,却没有被批评界充分重视的先锋文本。
从文类上,东君现在的这篇文字似乎应该算一个创作谈——是东君小说实践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和一些作家将自己的写作神秘化不同,东君坦然地裸露自己“一次”小说写作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坦然承认如何从海明威的《杀人者》、博尔赫斯的《等待》转换到自己的一篇小说《群蝇乱舞》。虽然是一篇工作手记,但最后谈论的却是短篇小说的文体本性和本质。且看小说家言。

海明威与博尔赫斯都不属于那种“物质主义”作家,他们不会在文本空间里放进太多已知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有效地把“物质”转换成“能量”。一部好的短篇小说所产生的能量,也许连作者本人都无法预料。这种能量会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持续地释放,一部分来自作品的内部,一部分来自读者的内心。读者会把自身储备的能量放进作品里面;而作品的能量也可以进入读者的内心。
短篇小说之美,不在于把一个故事完整地讲出来,而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呈现它的“不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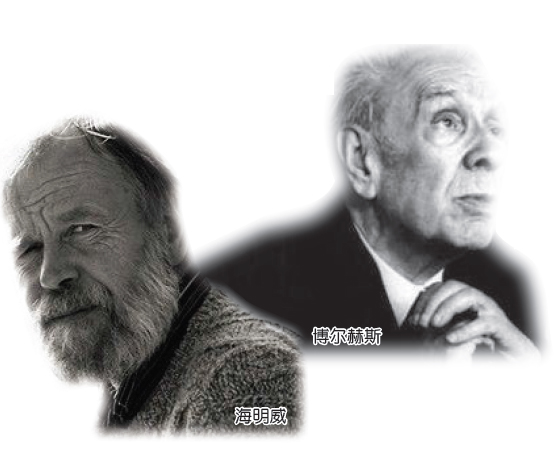
海明威 博尔赫斯
有一种短篇小说可以让人站着一口气读完;有一种短篇小说非要我们坐下来慢慢读(必要的话,可以斜躺着,采取卧读的姿势,以便让身心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还有一种短篇小说,当我们坐着阅读时,突然会产生一种站起来的冲动。很多年前,我阅读海明威的几个重要短篇小说时就有过这样一种阅读体验。
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我读罢海明威的《杀人者》,突然感觉这篇小说仿佛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我一下子像是被这股能量激荡起来。整整一天,我就没有再读别的小说了。第二天,我想读一点别的什么,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读起那篇《杀人者》,因为我觉得这篇小说中有一种悄然释放的能量正在吸引我。
那个拳击手究竟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博尔赫斯的《等待》里去了。我把《杀人者》读了一遍之后又去读《等待》。《杀人者》里面一种类似于量子讯息的东西就源源不断地出现了。《杀人者》中的重量级拳击手奥利·安德烈森和《等待》中的维拉里为什么要静静地等待着一颗子弹的来临?海威明和博尔赫斯都没有直接说明,但在一些细节中却透露了信息:从《杀人者》两个伙计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大略知道,那个安德烈森很可能“在芝加哥搅上了什么事”,而且据说是“出卖了什么人”;而在《等待》中,作者什么都没有说明,只是提到了一本书——但丁的《神曲》,还提到了书中的一个并不光彩的人物乌戈利诺,如果不读《神曲·地狱篇》我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个中世纪意大利比萨伯爵曾经在一场战争中出卖过自己人。也就是说,这两篇小说讲述的都是一个人因为出卖了别人而遭到追杀的故事。
我原本以为,只有我发现了《杀人者》与《等待》之间那种似乎源于经验同化所呈现的相似特点。后来我才注意到,马原在一次文学课中谈论奥康纳的短篇小说时,也顺带提到过这两篇小说。遗憾的是他只是一句带过,没有再作深谈。
在《杀人者》的结尾部分,尼克找到了那个正和衣躺在床上的重量级拳击手安德烈森,向他报告,有两个人要致他于死地。但安德烈森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作者在多处描述了一个相同的细节:“奥烈·安德烈森望着墙壁,什么也不说”;“‘我不想知道他们是啥个样子,’奥利·安德烈森说。他望着墙壁。‘谢谢你来告诉我这番情况’”;“奥利·安德烈森翻过身去,面对着墙壁”;“他望着墙壁。‘现在没有什么法子了’”;“尼克出去了。他关门时,看到奥利·安德烈森和衣躺在床上,面对着墙壁”。
在博尔赫斯的《等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细节:当仇人终于找上门来,博尔赫斯这样写道:“他做了个手势,让他们稍候,然后朝墙壁翻过身,仿佛想重新入睡。”
博尔赫斯对这个翻身的动作发出了一连串疑问,而海明威却没有片言只语解释安德烈森为何总是面对墙壁。
我父亲曾给我讲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年前,他去看望一位卧病在床的老拳师,很奇怪,老人家听到外头有人来了,也不管是谁,就转过身去,面朝墙壁。我父亲与他家人聊天时,那位老拳师一直背对大家,偶或应答一声。出来后,病人家属向我父亲解释说,老人家这一阵子情绪波动很大,懒言少气,谁都不愿意见。只要有人来看望,他就采取背对的睡姿。我父亲后来对同行者说,老人家恐怕时日不多了。事实证明,我父亲的判断是没错的,没过几天,老拳师就撒手归西了。父亲说,老拳师面对的,不是墙壁,而是死亡。
因此,在我看来,那位重量级拳击手奥利·安德烈森和维拉里所面对的,不也正是死亡?
是的,死亡的阴影一直潜伏在冰冷的文字间。《杀人者》里面收起的那支“锯掉了枪筒的散弹枪”,终于在《等待》中发出了声音。但博尔赫斯没有动用血腥的词汇描述这个场景,他只是淡然地写道:枪声抹掉了他。
尽管两部小说看起来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但我们不能就此妄下论断认为:《杀人者》可以归入博尔赫斯名下,而《等待》也可以视为海明威的作品。不是这样的。它们之间除了叙述风格不一样,结构也截然不同。就像《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从开头部分看更像是出自博尔赫斯的手笔,但我们只要耐着性子读上一部分,海明威的浓烈气息就出来了。而《玫瑰色街角的汉子》虽然有着海明威式的硬汉风格,但它仍然是以博尔赫斯的方式呈现。
把《杀人者》与《等待》放在一起,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杀人者》的结构是开放型的,里面隐藏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读完结局,我们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而《等待》就像一个封闭的圆,这个“圆”是完整而自足的,但里面同样有着可供想象的“隐匿的材料”。与海明威不同的是,博尔赫斯喜欢在捉摸不定的叙述中一步步逼近一个完整而又耐人寻味的结局:如果不能用匕首来解决问题,他就毫不手软地动用枪。他有不少短篇小说的结局跟《等待》类似:“苏亚雷斯带着几近轻蔑的神情开了枪”(《釜底游鱼》);“他倒退几步。接着,非常小心地瞄准,扣下扳机”(《死亡与罗盘》);《秘密奇迹》则是以一个不确定的数字和一连串确定无疑的数字构成了结局:“……他发出一声疯狂的呐喊,转动着脸;行刑队用四倍的子弹,将他击倒。哈罗米尔·拉迪死于3月29日9点03分”。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对博尔赫斯与海明威的作品进行比较阅读,说到底不是为了“求同”,而是从“大同”中发现“小异”。如果以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书法作喻,那么《杀人者》与《等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就像那种锐角造型、张力外倾的字,而后者就像那种钝角造型、张力内倾的字。这只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所获致的一种大体的感受。
很显然,海明威与博尔赫斯都不属于那种“物质主义”作家,他们不会在文本空间里放进太多已知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有效地把“物质”转换成“能量”。一部好的短篇小说所产生的能量,也许连作者本人都无法预料——事实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创作与再创作之间的关系——这种能量会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持续地释放,一部分来自作品的内部,一部分来自读者的内心。读者会把自身储备的能量放进作品里面;而作品的能量也可以进入读者的内心。
海明威的《杀人者》和博尔赫斯的《等待》后来就这样构成了我写作《群蝇乱舞》的灵感源头。那一年是1999年,我完成了几个中篇之后,想操练一下短篇,因为没有文体自觉意识,我写作《群蝇乱舞》时依旧带着一种近乎盲目的惯性,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到三分之二处,我就开始犯难,接下来我不知道该以怎样一种有悖常理的方式打破逻辑发展的情节。因此,我就把《杀人者》和《等待》重读一遍,但我还是没能把那一套从海明威或博尔赫斯身上学来的手法直接塞进自己的作品——“物质”与“能量”的转换并没有如我所想的那样简单。结果,这篇小说就像是带着自身的意志脱离了我的掌控,自行抻长了。成稿后一看,篇幅已接近于一个中篇。之后,我写了几个大致可以称之为“短篇小说”的东西,渐渐地,也就被一部分人承认了。
话说回来,把短篇小说写得越来越像短篇小说,未必是一件好事。这活儿难弄,我一开始就明白,但我也明白一点:短篇小说之美,不在于把一个故事完整地讲出来,而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呈现它的“不完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