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说,在好莱坞电影里,全世界被轰炸次数最多的城市是纽约。纽约是“美国梦”,纽约也是恶之花。这是一个极度分裂的“双面之城”。文学杂志《格兰塔》前主编约翰·弗里曼邀请了28位在纽约生活的作家写下他们的纽约故事,结集为这本《双城故事》,该书中文版由浦睿文化出版。通过这本“纽约折叠”,我们可以窥视到今天每个大城市每天都在生产着自己的“双城故事”,也可能甚至是三城、四城故事。
弗里曼最近一周来到上海旅行,澎湃新闻记者与他聊了聊纽约和文学。

约翰·弗里曼
现实不是现成的,是等着我们去触碰的
澎湃新闻:这本书都是写纽约的,为什么题目却叫《双城故事》呢?
弗里曼:我的感受是,在过去的五年里,纽约已经变得太不平等了。从经济的层面来说,面对面住着的人,可能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里。这条街上的房子可能上百万美元一套,但房子旁边每天徘徊着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共同分享的空间,彼此没有联系,两个世界互相冲突。这种冲突开始定义何为纽约。
澎湃新闻:你说的其实全球化的大城市都是这样,也不只有纽约是这样。那你觉得纽约这个城市有什么独特的、所谓纽约城市精神吗?
弗里曼:纽约一直是一个肮脏的、嘈杂的、多元杂居的、全天候运转的城市,它的破碎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随着金融市场权力巩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纽约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二三十年前,你可以花二十万美元在纽约买一栋公寓。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随着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纽约背叛了这样的精神,它不再是一个大熔炉。尤其是因为金融产业的发展,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把生活成本提高到了大部分人都望其项背、无法承担的程度。我知道在这儿(上海),生活成本也很高。但不一样的是,纽约是一个更老的城市,现在这种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不是从来都是如此的。
澎湃新闻:说到纽约,就一定会联系到美国梦,你个人相信美国梦吗?
弗里曼:是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写过很有趣的书叫《异类》(Outliers),他讲的就是我们用一些天赋异禀的异类来代表“美国梦”这个迷思。很多美国人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找一份工薪阶层的工作,供小孩子上了大学,追寻美国梦。但这些人是异类,还有很多人在受苦、失败。美国梦只有在人们相信的时候,它才有效。但现在他们需要美国梦,因为这个国家不再照顾穷人,从一个福利国家转向了另外一面。美国梦很漂亮,如果人们来到美国,没有性别、种族的歧视,但现在这个国家非常残忍。
澎湃新闻: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作品里,也有对于美国梦的质疑,那跟当下的美国梦的破灭有什么区别?
弗里曼:很有意思,你提到《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写作的年代和今天有着同样的不平等。《了不起的盖茨比》讲的是大萧条前夕,那时社会保障所有人。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巨大的到处可见的财富,它有意思的地方是展现了你可以追求巨大的财富,但不追寻美国梦。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梦不只是伦理的公共概念,它也是一个文学概念。电影往往喜欢成功,但在文学故事和小说往往对失败更感兴趣。但从伦理道德意义上来说,失败并不那么有趣。你需要人们成功,支撑起家庭,有体面的工作,有体面的薪水等等。但我觉得,好莱坞电影、电视剧、媒体似乎主宰了我们对于纽约的想象,《欲望都市》等片子里,你看到的是好像一场财富文化的狂欢,好像每个人都住大house,年薪上百万。
但如果你真的生活在纽约,如果你不属于1%的那个阶层,你会和1%以外的阶层有很多接触、互动。如果在纽约,即便这里是大银行,大商场,你会看到周围聚集着无家可归的人。你会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你的生活很可能变成另一个样子。在纽约,每个晚上,都有6万无家可归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请作家们来写纽约,我知道作家们也关心这些。文学不应该只反应这个城市光明美好的那一面。
澎湃新闻:这也是你在序言里说作家们也可以用他们的想象力和经验,为从本质上努力改良城市助一臂之力。
弗里曼:是的,我认为现实不是现成的,是等着我们去触碰的。现实也是我们建构出来的。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要想在纽约心安理得地活着,你就得装作好像你看不到那些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他们不存在。我觉得作家没必要写出大团圆的结局,他们用他们的写作让我们承认这些人的存在,这就可以了。人们看到的越多,就越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澎湃新闻:你现在是文学网站Lit hub的主编,钱从哪里来?
弗里曼:一个叫格罗夫的小型独立出版公司,专门出贝克特、亨利·米勒、哈罗德·品特、阎连科等人的作品。出版人觉得美国的文学文化正在遭遇困境,因为报纸的广告没了,都去投给网络了,所以很多报纸的书评板块都被砍掉了,然后就有了这个网站。两年时间,现在有一个月50多万的浏览量,可能是最成功的英语文学网站之一。我还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叫Freedman’s,两年一期,有点像《格兰塔》。
澎湃新闻:美国人不太读世界其它地区作家的作品,这不是我的偏见吧?
弗里曼:完全正确。在美国,没人读莫言的作品,也没有人读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我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小团体,他们会把阿乙等中国年轻小说家的作品翻成英文。我觉得翻译是一个疯子干的活,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压力非常大,也没什么钱,也没什么名气。我知道,在日本,有一种摇滚明星一样有名的翻译家,但反正美国没有。我是干文学的,我知道这些翻译家,但其他就没有人认识他们了。
你说得特别对,我们应该鼓励美国人拓宽他们的阅读视野。除了那些畅销书,别的书卖掉2000册就算成功了。所以这个数字挺让人泄气的。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像哈金、李翊云这样的母语是中文但在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作家?
弗里曼: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我在《格兰塔》都发表过他们俩的小说,我也给很多他们的作品写过书评。哈金很有意思,他很晚才开始学英文,然后开始学习用英文写小说,《等待》是非常漂亮的小说。我觉得美国人往往喜欢读那些离开了母国,然后在美国生活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而不是还生活在母国的作家的作品,比如通过这些作家的作品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往往会读李翊云的作品,而不是余华的作品,尽管余华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对美国人来说,哈金、李翊云变成了中国人的代表,这本身不是他们的错。就好像裘帕·拉希莉,她突然就变成了十几亿印度人的代表,但她其实没有在印度长居过,她住在美国,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于文学的误用,我们给这些作家施加了太多的压力。
澎湃新闻:你怎么评价他们的英文呢?因为很多西方人会说他们写的英文很简单。
弗里曼:我觉得英文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一直被那些母语非英语的人激活。像杰克·凯鲁亚克,5岁才开始说英语,索尔·贝娄,他一开始说的是法语。我喜欢哈金、李翊云的英文那种钝感、粗糙的感觉,时间久了,他们的英语顺一点儿了,更光滑一点了,他们不是故意的,但他们就是这么写了。从他们的英语中,你读到的声音,语调,这种变形和转化是很让人兴奋的。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一个波斯尼亚裔作家,他会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意象放在一起,因为他对于自己成长的语言中的陈词滥调不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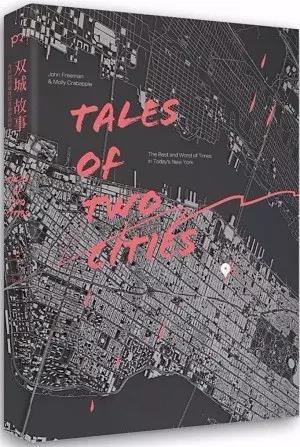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