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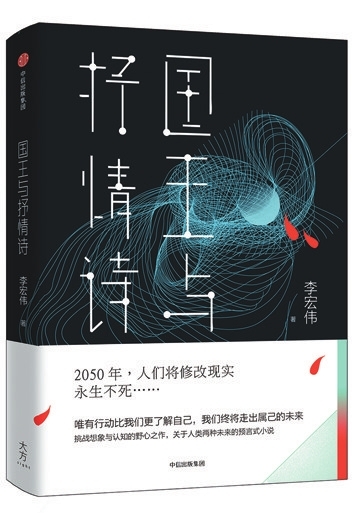
《国王与抒情诗》,李宏伟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39.00元
我视自己为“现实作家”,我认为自己的写作关乎现实,甚至只关乎现实。现实刺激我、召唤我,我必须回应它、廓清它。
“国王”和“抒情诗”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连李宏伟本人也琢磨不透。他只知道,这两个词语间的张力让自己心心念念,留存越久,越要去想象:在秩序井然、讲求理性的国王世界,感性勃发、自由舒展的抒情诗是否还能够存在,如果能,将以什么面目。
不知多少年之后,“国王与抒情诗”的种子,才逐渐找到它的土壤,在可以生长的空间里生成小说的轮廓,并在李宏伟的写作中逐渐清晰。
在小说中,李宏伟选出“思、聊、物、唱、谜”等42个字作为标题。在他看来,每一个字都代表了这个世界不可变更、移动和不可替换,这些小标题是一次次发现,同时也拓展了小说走向纵深的可能性。或许还有更佳的备选,但一旦选定,便成了最合适的,无法更改。
李宏伟的职业是编辑,所学专业是哲学,同时他还是诗人、是译者。“不同的身份意味着我们拿出自己的某一部分来应对世界,与此同时,这种应对也让我们对自己的那一部分有所观照、发展。一个人在应用不同身份时,如何展现与收放他的秉性、禀赋,在不同场合中,他怎么缓解那种身份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将他挤压到何种程度,这些是我更感兴趣的,”李宏伟说,观察与反观确实丰富了写作。“至少,它让我明白自己的写作也可以从内里构成多重身份。”
中华读书报:在结构上,《国王与抒情诗》分为《本事》和《提纲》两部,在作品体例上也有很大区别。你是怎么考虑的?此前你的《哈瓦那的超级市场》里就有三层结构;新作中又有长诗《鞑靼骑士》镶嵌其中。
李宏伟:到目前为止,我着手一部小说时,不会列出详细提纲,事先演练小说的层次、节奏,因为写才会真正发明一部小说的骨肉血。但我习惯在着手前把小说的空间明朗,想明白它可以往哪几个方向发展,需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初稿完成后,再根据小说已经得到的空间,来修改、完善。
我对自己的小说有个基本的空间要求:够。不是要写足,把所有的地方填满,让读者顺畅地往下读,而是把这个小说本身应该有的空间写够,拓展到符合小说本身的要求。小说的结构,包括所谓的技巧,都是其空间的外显。具体到《国王与抒情诗》,它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有《本事》《提纲》(原来叫《材料》)两部,是一种竖的乃至垂直的空间,第二部是铺展的基础性物质,第一部是这基础性物质诸多可能中实现的一种,《鞑靼骑士》则是实现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准备小说的单行本时,我总感到这部小说的“不够”,竖的空间过于单调,于是又补充了“附录”,一是让小说突破了2050年这一封闭时间,二是让《本事》《提纲》的相对位置移动,关系产生变化,有了相互的投射、映照。这样改定后,心里才踏实一些。
中华读书报:作品开篇写到:“20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意外去世……”你如何定位《国王与抒情诗》?《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得京东奖时(首届京东杯“锐”作者征文大赛中篇小说组一等奖),颁奖词里评价你写的是科幻小说,当时你并不同意。为什么?
李宏伟:科幻小说是我现在很感兴趣,也想花精力了解更多、阅读更多的类型,我对很多科幻小说与科幻作家都心怀敬意,京东颁奖时,我不同意《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是科幻小说,主要是认为它的“科幻小说含量”不够,不足以放到我敬重的那些作品序列里去。《国王与抒情诗》,我不反对别人说它是“科幻小说”,但我自己不把它当作“科幻小说”,这不是出于傲慢类似考虑,而是想表达我的关切。
尽管定义或者标签常常不由作家本人决定,也常常偏离他的意愿,但一个作家清楚表达自己的关切总是应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视自己为“现实作家”,我认为自己的写作关乎现实,甚至只关乎现实。现实刺激我、召唤我,我必须回应它、廓清它,《国王与抒情诗》是我看到的现实的胚芽或庞大身影,我尽力将它辨认清楚,并指认给愿意的人看。如果有人认为,这部小说里的现实并不那么“现实”,我会提请他注意威廉·吉布森那句被重复了很多遍的话,“未来早已到来,只是尚未普及”——未被普及的未来正是我们的现实。
中华读书报:标题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你希望在作品中向读者传达什么,可否简而概之?
李宏伟:第一部《本事》的每一节标题都是该节内出现的字,加上它的解释,这些解释完全来自中国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和最大众化的字典《新华字典》。每一个字和它的解释构成一个词条,全部45节的词条放在一起就是一个词汇表,内容有实有虚,离我们的生活有远有近。第二部《提纲》一定意义上就是第一部里面提到的《面向死亡的十二次抒情》,和当代中国诗人的非正常死亡方式有关,标题或者指向具体诗人的生命要素,或者指向某一种死亡的关键部分。如果读者读完这个小说,尤其是在标题上得到一点启发,愿意去列一个他们自己的词汇表,去想一想自己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表述方式,那我将感到由这部小说而来的某种合力。
中华读书报:青年评论家杨庆祥认为,你的全部作品都在处理一个重要的现代主题,即主体精神的统一性问题。“在诗歌中,他以一种密集的意象和知识来呈现统一性内部的不可弥合的毛细血管;而在小说中,他借助形象——个体的形象和世界的形象来呈现一种异质性……更重精神内景而非日常琐碎,他更热爱复杂的综合而非简单的故事陈述,”因而你很少被归为70后作家的典型成员。你认同吗?确实,大家在谈论70后作家的时候,你似乎是疏离于这个圈子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李宏伟:谢谢庆祥的评论,他所说的正是我想通过写作实现的,但我还在路上,前路漫长。代际是当下文学评论与生产的主要方式,一个作家是否被划入到一个代际中,除了他无可更改的出生年份外,还有包括出道早晚、出版方包装方式等诸多偶然的因素。我对被称为“70后作家”的群体没有完整、全面的阅读,因此无法断定这个群体有哪些可以清晰总结的特点,更没法对照这些特点自我判断。我可以说的是,单就我读到的1970年至1979年出生的小说家,比如阿乙、张楚、徐则臣、李浩、弋舟、陈集益、东君、石一枫、黄孝阳、田耳等人,他们每个人都特点鲜明,无法用一个词语归纳合并。另外,作为1978年生人,我对“70后作家”这个概念毫无兴趣,但我对前面提到的这些人以及其他我关注的同龄人,一直有一份亲切,他们的写作也提醒我,这世界有我惯常目光忽视的东西在闪耀、生长。
中华读书报:《并蒂爱情》里面的两个人身体长在了一起,《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写的是世界末日的故事,《国王与抒情诗》写的是2050年……为何会有这么强烈的虚构意识?
李宏伟:就时空而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身体只能存在于此时此地。我们在此时此地面对和处理的一切,构成了每个人切身的现实,即使是我们的思虑也通常有现实的触发点或者出发点。如何在当下,返身观看自己的现实?意识乃至意识中的身体,和自己的现实是什么样的距离?每个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答案、独到的体验。当我被现实的某一点触动,又无法在面对面的情况下看清楚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会尝试着往远处退或者把这一点放大,这固然会让我看到的进而呈现出来的有“失真”,有着浓烈的一望而知的虚构色彩,却也能让触动自己的“这一点”突出来,更容易被他人看到,更有力地传递那份触动。比如《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一开始让我心惊肉跳的是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多少年后将有多少男人只能单身到老的新闻报道,但我真正理解了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在通过小说给它找到了纯男性构成的匮乏社会之后。
中华读书报:你对自己的创作,有无明确的规划?
李宏伟: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对置身的现实有深层次的把握,能够拓展我对时代的精神状况的认识,并且将我的把握、认识如水波一样,借助涌动的力量,扩散、传递开去,如果可能,最终汇入到人类精神的波纹图中,成为一环也好,一截也罢,或者成为其中隐在、湮没的成分,总之,能让我在某一天停止写作的时候,不会对自己曾置身的现实感到羞愧,不会羞于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希望自己能够同时在退得足够远的地方、离得足够近的地方,来凝视、处理我面对的现实,我的写作规划也大体是沿着这样两个方向拟定,前者如中篇集《假时间聚会》与《国王与抒情诗》,后者如《平行蚀》,就算最终它们并没有均衡发展,但对作为“这一个”的我来说,却是必须的。我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在某个时候,脱离这样的规划,放开我的现实,彻彻底底地疯起来、狂放一次,拿出一部让自己也大吃一惊、始料未及的作品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