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史无前例的改变,写作者需要敏感地观察和把握它们。”把汉语当做沟通人们心灵之桥的写作者们,身处这巨变的时代,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故事,又将呈现怎样的面貌?本期报纸我们采访了九位写作疆域各不相同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聆听他们关于写作、关于心灵的声音。这几日我们会陆续推送给读者们。
《北鸢》是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南北书”之“北篇”,历时七年,是继上一部《朱雀》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文笔的华美清雅,内在情怀对传统文化的薪火相承,以及现代语境中对民国历史独具韵味的演绎,让业内专家和读者颇感惊艳。
学者陈思和为《北鸢》作序:“虽是一部以家族史为基础的长篇小说,但虚构意义仍然大于史实的钩沉。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又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也许这不仅仅是他的兴趣,读者们都会有兴趣知道,作为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青年作家,葛亮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文化底蕴、审美取向,让他选择这样一种小说形式与语言,叙写他的中国故事,写出一部致敬《红楼梦》的当代小说。

新作《北鸢》
“格物”是引领我进入历史情境的因由
Q
陈思和教授在序言中指出,《北鸢》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史。你在自序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本小说关乎民国,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你怎样让自己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去直面民国的历史?
葛亮:很感谢陈思和老师对《北鸢》的精准导读。我曾经与前辈作家有过对话。在当时我更倾向于前辈书写历史建基于亲历经验,而吾辈更多依赖于想象。“想象”为年轻一代赢得了更多历史书写的空间。但在《北鸢》的写作过程中,我的想法出现了调整。我越来越要求将自己置于“在场者”的地位。我为这部小说进行大量格物工作,如果缺乏有关那个时代的细节,所有的想象都是无本之木。其实“格物”对我而言,意义远不止勾勒场景,落实细节本身。它是引领我进入历史情境的因由。借由这些历史的砖石,我搭建的是一个“在场者”观照下的模拟现场,以此去穿透我,作为作者与历史间的重重隔膜。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并不困难,相反是十分愉快的。
Q
你沿着丰富的细节,重返历史的现场。历史、岁月,人物、命运渐渐地有了温度和质感。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葛亮:是的,的确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因为这种查考具有相当的延伸性,比方一场“祭孔大典”的场景,你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典制本身。与此相关的春丁秋丁、府县两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辞格式,祭服的具体样式,这些细节是环环相扣,由此及彼的。换言之,落实的过程,也是不断发现的过程,并在其间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这种建构系统的意识,也和我受到的学术训练有关。所谓格物,并非只是埋在故纸堆里作案头功夫,我也很乐意通过访问的形式去触摸历史,比较有温度。所以,如何“让读者重回现场”,对我而言,前提是,我已经是“在场者”。这种感觉很微妙,处理虚构与真实,原无一定之规,而我则按照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进行。
Q
民国是中国现代史中真实的部分,你以小说的方式进入民国,《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上个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岁月中的世道人心。生活在一个全媒体,全球化的时代,已经隐没在历史大河中的民国,上世纪20至40年代中的人和事,是你生命中的重要情结吗?你的现实生活与你虚构的小说世界有什么联系?
葛亮:我对那个时代的感情,来源非常具体。就是我的家族与父祖辈的经历。我的祖父是一名艺术史学者,外公则出身商贾家庭。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造就了我认知民国这个时代的不同面向。特别在写作《北鸢》的过程中,祖父生前的几位挚友,如王世襄,范用等陆续辞世凋零,我感觉到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这或许是我表达它的动力。
《北鸢》中,有相当比例的情节是源于真实。为了写这部小说,我曾经去加拿大探访祖父的同窗,切身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个体与历史间的砥砺。同时,父祖辈的经验本身对我是无形的滋养,特别是知识结构的建构方面。比如我祖父对于中西艺术与绘画的见解,我外公作为戏曲票友对于京剧与昆曲的体认,都融入了小说中的细节。有关传统的薪火承继,这也是一条路径吧。

Q
现代的身份,全球化的角色,古典的心,你觉得对你这样的概括准确吗?前两者是时代赋予你的,而唯有古典的心是你的一种选择。你对古典的心是如何理解的,影响着你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
葛亮:其实每个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都负载着现代与传统的辩证。我想古典的心,多少是对传统的依恋吧,包括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审美,甚至人情。从文化续接的角度,我儿时的阅读经验提供了某些帮助,这和父辈的引导有关,看了不少笔记体的小说,《阅微》《耳新》之类。培养了我对古典文字传统的敏感与语感。
因为生活于当下,我对于中国的讲述,呈表传统,更多会考虑到现代的语境。所谓“常”与“变”的关联,这是在沈从文先生的《长河》中已经提出,但未得到解决的问题。现代性的价值,需要放置在中国经验中加以检验。虽然新古典主义本身是个舶来的概念,但对于传统的吸收、消化、反刍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品类的过程,对于东西方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当下时代的变动不居,构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试验场,我很感兴趣在这个“场”里中国的角色与位置。在《北鸢》中,除了传统而封闭的襄城外,我同时写了民国最为时髦的一南一北的两座城市,天津与上海。在文化谱系上,它们为襄城所钦羡与模仿,同时也和后者产生对话。在天津内部又有新旧的分野,在意大利和英国租界区,成为前清遗老遗少的避居之地。而上海的“隔都”,则成为犹太人的诺亚方舟。中国在民国时期所呈现出的空间的复杂性,让我十分着迷。其次,我也感兴趣中国与西方文化相互的谛视。所以,《朱雀》从一个苏格兰长大的华人青年的视角切入,对古城南京的探视。而美国的间谍泰勒,以中古五音制成曲谱发送情报,则是当时关乎中西的文化想象使然。
我写中国的每一个当下,都希望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
Q
这些构成了你小说的空间与格局。为了写好天津和上海,你专程去过上海和天津吗?
葛亮:是的。上海因为和南京很近,我自小非常熟悉。对天津的了解,不少是我外公和祖辈们对我讲述的经历。为了写小说,除了案头功夫,专程去天津数次,都是为了做相应的实地考察,直观的感受和认识,与抽象的格物还是不太一样。前者更有温度,好像亲自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是血缘和地缘上双重的亲近感。所以,小说有不少细节都是很日常的。天津对我而言,又和故乡南京有叠合的一面。历史沉淀丰厚,城市格局又相当的日常,是过日子的城市,这一点特别符合小说的气性。
书出版后,围绕小说内容,做了一次“与《北鸢》行怀旧之旅”的直播活动。我们首先去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拜访了冯老师,听他亲自为我们讲述老天津的风物。这些年,他对于传统建筑的保护作出卓著贡献,令人感念钦佩。随后,循着我外公幼时的成长轨迹,我们探寻了天津的一些历史遗迹,比如他曾就读的耀华中学、意大利租界区、督办衙门的原址。这一程下来,感觉《北鸢》这部小说与我个人之间的联络,更为饱满和丰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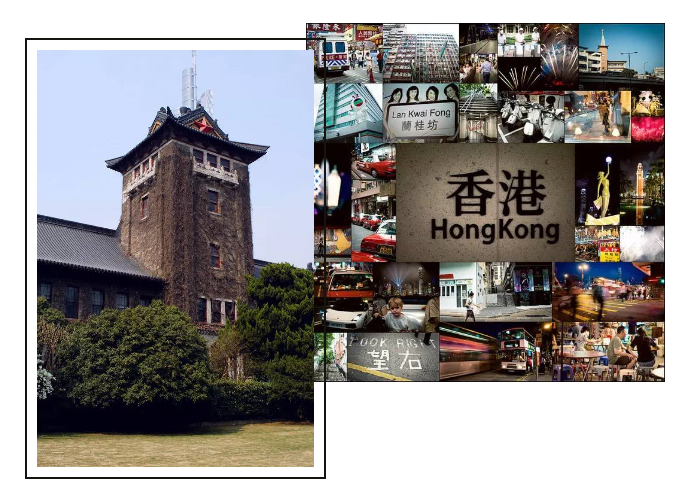
南京与香港,家城与磁场
Q
你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几年了?香港和南京这两个城市,对你思考审视历史和体验认识现实,有着怎样的影响?你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吗?
葛亮:我在大学任教近十年。南京与香港对我的历史体验而言,各有意义。我曾将其概括为南京是我写作的温床,而香港是我写作的磁场。南京作为我的家城,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如吴敬梓先生所说“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但落实到民间,就是感觉很舒服,很适合生活。而这种舒服,会影响文字表达的欲望,因为生活方式本身已是立场与态度的表达。
Q
在南京,你经常会去哪里?金陵是不是让你感到历史就在斜阳余晖掠过街角、建筑的时候,在日常的市声中,静静地流动着?
葛亮:在南京,我常去的地方,一个是夫子庙,与儿时记忆不同,现在逐渐商业化了;一个是南京博物院,前身是中央博物院。有丰富的藏品。尤其是明清瓷器,每次去,满目如见故人。南京的确是个历史俯拾皆是的城市,自小身处其中,习以为常。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祖父执教过的院校,我有一份独特的感情。百年老校,虽处闹市,却宁静沉郁,是旧日的好。在里面学习,久而久之也是一种心智沉淀吧。每次走进校园,看到被藤萝包覆的北大楼,心里就格外踏实。
来到香港后,这座城市的气质与南京全然不同,节奏的匆促,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冲击还是蛮大的。促使我躬身返照,去重新审视南京。也构成了我写作的起点。写作之初,在台湾出版《谜鸦》时,我曾被称为“学院派”作家。虽然现在这个称谓已不重要,但是学院的训练,还是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某些养分。比如对于文本逻辑感和格局感的构成,比如从田野考察的角度,对实证与“格物”的重视,大约都和我的学术身份相关。

Q
历史不是简单的时间排序,而是类似于有机的生长。你今后的创作还是面向历史的中国吗,还是会书写当下的中国经验?历史的中国,是你讲述中国故事擅长的题材?这是你以现在的眼光打量历史,去发现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联系。
葛亮:其实我写中国的每一个当下,都希望是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的。因为对于具有历史感的国族来说,每一个当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时空网络中的某个坐标,必然有其发展的起点与渊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感兴趣这种在结果基础上体会渐变的过程。所以,我的不少小说都是现实对历史的逆推。其间,你会感受到历史的意外,以及不规整之处。这是作为小说作者可以发挥的空间,你通过虚构去丰满与梳理这种达至意外的逻辑,同时表达这种逻辑中所含有的“常情”的力量。这便是我认为的历史的强大,这是吸引人的。
Q
现实和历史不是割裂的,现实就是历史的有机生长。你写《北鸢》历时七年,犹如重回历史情境,与笔下的人物共处了七年,内心一定有很多感慨吧,在回望历史,思索历史的过程中,是不是感受了自己的成长?你的下一部作品准备写什么题材?
葛亮:小说写作本身对我而言是种内心的沉淀之道,成长一定是有的。触摸与呈现历史的过程,也是建构自身的旅程。和笔下的人物将心比心,休戚与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也随之而饱满与成熟了。下一部长篇小说,仍然是关于中国的历史,会延展得更久远些,同时会放置到相对更宽阔的语境中考察,探讨中西方文化传统在接触之初的彼此间的交错、钦羡、撞击与融汇。
Q
作为教师和学者,你一定了解和领会不少现代小说的技巧,作为一个作家,你是不是对《红楼梦》情有独钟?或者说《红楼梦》对你的文学观和写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葛亮:我对《红楼梦》很熟悉,是我阅读经验中的重要部分。我很钦佩曹雪芹先生的一点是“博学于文”。但我更重视的是他对于“民间”的态度。《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小说达至文人化的高度标尺。它是雅的,但对俗的东西也融合得很好。中国小说的源流本身就是俗文学,所谓“稗说”,传奇,话本、拟话本都是为了喜闻乐见。其中有着来自庙堂之外的、野生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红楼梦》里保留了这些东西,雅俗共冶一炉,构成了审美的新气象。曹先生的《废艺斋集稿》已经散佚了,里面多涉及民间艺术。风筝是其中一种,所谓“比之书画无其雅,方之器物无其用”,但恰恰是这种“无用之用”,相当的迷人。它代表着一种审视历史的角度,自由而不拘一格。有很多逸出成见的所在,是我在写作上认同与重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