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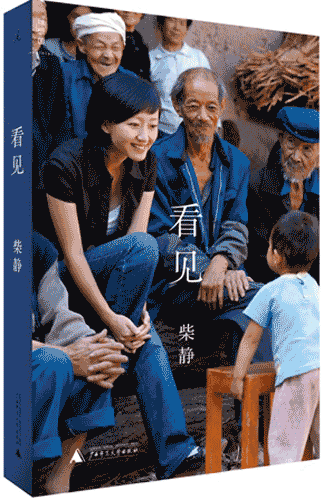
《看见》,柴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问:“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责任编辑:admin) |